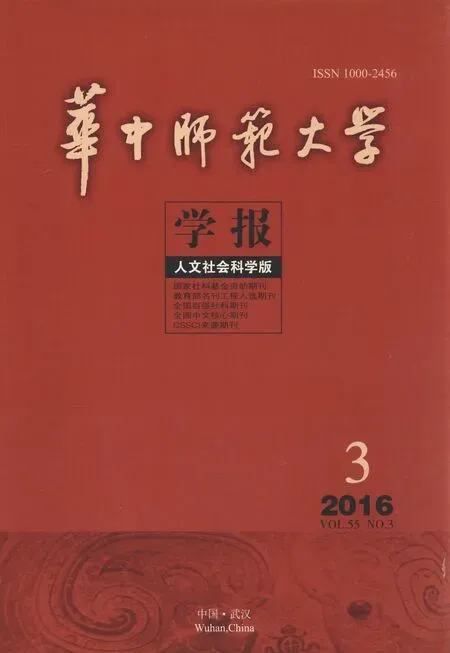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辛德勇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辛德勇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前此我撰著《制造汉武帝》,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读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本文就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文章首先指出,在西汉时期,只要不以天子为祝诅对象,巫蛊并不违法;《汉书》客观记载了从太子据宫中掘得桐木偶人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武帝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感悟”,不过是意识到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更换太子的意图,是促成巫蛊之变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仅汉武帝,甚至直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朝廷,一直认定太子据犯有对天子行用巫蛊的罪过。
西汉; 汉武帝; 卫太子; 巫蛊之祸; 江充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即心存审慎者,亦不过表述为其事或许如此而已。前此我撰写《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此文后单行出版一小册子,题作《制造汉武帝》),其中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人感觉难以接受,纷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表看法。其中虽然也有学术论文,但更多的只是一种议论,以为拙说不能成立。
很多历史问题,因史料记载不够明晰,学者们基于各自的主观原因而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来很难彼此认同。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在这里详细讲述一下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令这些朋友更具体、同时也更为切实地了解我的想法。至于了解之后,是否愿意接受,仍不过各信其是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当代学者中,有很多人,做过乍看起来好像很深入的探讨,例如劳幹、田余庆、蒲慕州,等等。但我读后,感觉这些论述,似乎都与《汉书》等基本史料的记载,存在很大的隔阂,甚至明显的抵牾,好像总是作者自己想得太多了一些。因学识所限,一时我还难以领会这些高论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确切联系。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这里就暂不涉及他们着力探讨的那些史料中隐而不显的问题。
一、论证的前提
近人吕思勉,在所著《秦汉史》中,对巫蛊之祸始末,做过比较细致的梳理,多信而质实。本文所论,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这一基础。当时所谓“巫蛊”,如吕氏所说:“蛊之道多端,武帝时期所谓巫蛊者,则为祝诅及埋偶人。”①这是本文立论的一项基本前提。
论及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当时,人们行用巫蛊之术,只要不以汉家天子为祝诅对象,一般并不违法。
溯其缘起,在秦代,就连朝廷,甚至都设有专门施行这种法术的“秘祝”之官,“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唐人张守节对此解释说:“谓有灾祥,辄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恶于众官及百姓也。”②如此赤裸裸地以民为壑,堂而皇之地引祸水而下流,而且一直沿袭到汉文帝十三年夏,始废除这种做法③,犹可见此等巫术盛行的程度。民间普遍合理合法地施行,自在情理之中。
在废除此法之前的汉文帝二年三月,孝文皇帝刘恒,发布了一道涉及巫蛊的重要诏令: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④
诏书中“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这句话,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原本连读为“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语义不明,而看裴骃《史记集解》和张守节《史记索隐》所做旧注,则愈加糊涂不清⑤。
通观上下文义,知汉文帝乃云为“通治道”而欲除去“诽谤”和“妖言”两罪(《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将文帝此举概括为“除诽谤律”⑥),而作为这两项罪名具体针对的罪行,汉文帝列举的“妖言”之罪是“民或祝诅上”,亦即直接诅咒当今皇帝,故“吏以为大逆”。如此严重的行径,竟然能够得到汉文帝的宽宥,本来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皇帝在已经与民“相约结”亦即应允民众的情况下,随后复又“相谩”,也就是朝廷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蒙骗民众。因而,并不是任何一种诅咒皇帝的“妖言”,都可以从宽发落,免除其罪责。台湾学者蒲慕州,曾以为汉文帝此诏是取消了“祝诅上”为“大逆”亦即处以死罪的律条⑦,误解殊甚。这一事例向我们提示,当时在特殊情况下,即使是直接祝诅今上,也是可以免受惩罚的。那么,民间百姓之间,行用巫蛊之术,更不会轻易获罪。

对此,需要适当予以说明的是,东汉时人郑玄,在注释《周礼》“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这一文句时,引述汉代律文注云:




二、太子据巫蛊事件的经过
事关太子据的所谓“巫蛊之祸”,其具体经过,在《汉书·戾太子传》中有比较清楚的记载: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
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
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徳,徳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宫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眀,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徳言。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记述,随着问题的展开,下文还会有所征引。不过,通过上引《戾太子传》的内容,已经可以了解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
按照《戾太子传》的记载,太子据被牵连到“巫蛊之祸”当中,首先是由于江充率人进入“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这种“桐木人”,也就是施展巫术时替代所诅咒对象的人偶。关于这一事件,首先,《戾太子传》文中“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这只是一种客观的记录。同样的记录,尚别见于《汉书·江充传》:
会阳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孙贺子太仆敬声为巫蛊事,连及阳石、诸邑公主,贺父子皆坐诛。……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读文中“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这句话,与《戾太子传》的行文,几乎一模一样,简单,明了,这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情节存在。
像《汉书》这样严谨的历史著作,其最基本、也是最为首要的功能,当然是如实记述史事。在有关巫蛊之案侦办与被告双方人物的传记里,都决然不见江充暗设计谋来诬陷太子据埋设桐木偶人以行蛊术的记载,清楚显示出这是一件在太子宫内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并非无中生有。
再来看东窗事发之后,《戾太子传》所记太子少傅石德的态度。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惧为师傅并诛”。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若是不明就里,或是此事还存在太子自施巫蛊之外其他的可能,石德怎么会一下子想到自己会与太子据一并遭到诛戮?若是太子据在召唤他前来商议时就明确告诉他,此事出自江充栽赃陷害,他又何必再讲“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亦即已有确切物证证明太子据暗施蛊术这种废话?显而易见,惊慌之中,太子据并没有向这位少傅讲出诸如江充设计陷害之类的开脱词语。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危急关头,石德一下子就想到了从困境中挣脱出来的办法,以询问的口气说道:“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眀”——这个桐木偶人,究竟是司职搜查之巫自己安放的呢?还是此前确实就在宫里,这是你自己怎么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这是以一种委婉的形式,给太子据指明一条逃脱惩处的路径:也就是反咬一口,说是江充预埋人偶陷害太子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据也并没有向石德申明自己的无辜,事情的真相,实已昭然若揭。



三、江充之奸



尽管今所见《三辅旧事》的佚文,显示其纪事内容大多尚较为平实,但毕竟只是杂记琐事,其记述重大史事的可信性,远不能与《汉书》这样的“正史”相比。即以这一条记载而言,观其“充晓医术,因言其事”云云,即与《汉书》的记载存在巨大差异,且绝不可信据。因知江充预埋桐人于太子宫中的说法,也同样不足偏信。
关于江充预埋桐人于太子宫中,在唐代初年撰著的《礼记正义》当中,在疏释《礼记·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语及郑玄注之“左道若巫蛊及俗禁”时,还有这样一段叙述:

观其所述“后王将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诛充”云云,与《汉书》太子或将被废的记载决然抵牾,即可知这段记述不仅不是出自《汉书》,而且显然属于所谓齐东野老之谈,就历史纪事的意义而言,本没有任何史料价值。





考虑到这一因素,也就愈加容易理解,太子据派人捉拿江充以至韩说、章赣、苏文诸人,若是不能逼使其就范,一致屈认江充埋置偶人陷害,就只能杀人灭口,使之死无对证,然后再寄希望于汉武帝病体衰弱不支或是业已身亡,冒险一搏,夺取帝位。太子据图谋杀死江充、韩说等所有负责侦查巫蛊的官员,已经表明在行用巫蛊一事上,他绝不像现在很多人所认为,或是所热切期望的那样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四、汉武帝的“感悟”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从壶关三老等人上奏的内容及其缘起谈起。史载太子据在长安城中兵败逃亡之后: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曰: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
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寃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
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鈇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首先,如此惊天动地的重大事变,京城里满朝文武官员谁都闭口不谈,各地方官员同样缄默不语,却是由远在今山西长治太行山东南边缘地带的微末小吏“壶关三老令狐茂”出面上书,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像令狐茂这样的人,当然无法直接与闻深宫秘事,身后一定另有地位较高的人物作后台。问题是不管是其背后指使人,还是令狐茂这位站在前台的壶关三老,假若确实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或是切实了解到江充故意给太子据栽赃的行为,本应该直截了当地指明这一邪恶阴谋。这既能够直接把性命危殆的太子据解脱出来,又足以使汉武帝的盛怒涣然冰释,老皇帝和小太子,马上就能尽释前嫌,和好如初。然而,壶关三老令狐茂的说辞,却是迂曲回绕,讲了好长一大段话,还是不清不楚,只是触动汉武帝内心深处暗自有所“感悟”而已。这样的“感悟”,更像是一种拿不到台面上清楚叙说的“心照不宣”。
具体来看壶关三老令狐茂的上书,笔锋竟首先指向汉武帝本人,而不是直接出面整治太子据的江充,这更显示出江充并没有犯下诸如诬陷太子据这样严重的罪过。令狐茂上书第一自然段的话,是在讲述太子据起兵事件的核心原因。——首先是“父不父则子不子”,亦即汉武帝有过在先;又“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也就是太子据做出的引发所谓“巫蛊之祸”的行为,实际也算不上不孝,只是汉武帝没有明察整个事件的真实性质而已。
在上面引文所划分的第二自然段,是壶关三老令狐茂为太子据所做的辩白。在这里,同样没有直接正面指斥江充弄虚作假,刻意欺骗汉武帝,而假如江充确实造假坑人,这本来应该是其指陈的核心内容,不能不直接言明。除了泛泛而谈江氏等“造饰奸诈,群邪错谬”之外,其实写的内容,重在提醒汉武帝,对待太子据与江充二人,一定要判明内外的界限,做到亲疏有别:即太子据是汉家嫡嗣,而江充只是闾阎之隶,明此,也就不必做智者不为之事,来“深过太子”。假如壶关三老令狐茂能够把“造饰奸诈,群邪错谬”这句话坐实为江充使人埋设施行巫蛊使用的桐木偶人,一语戳破其鬼蜮伎俩即可,何必还要以内外亲疏这么迂远的套话来疏解汉武帝对太子据的愤怒?
令狐茂上书的最后一段,是讲他此番上书是出自对朝廷的忠心,并再次劝告汉武帝切勿听信谗言,而应宽恕太子。
从总体上把握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的内容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令狐氏所说“造饰奸诈,群邪错谬”究竟指的是什么?看前引《汉书》之《江充传》和《戾太子传》,可知江充看到汉武帝年老体衰,害怕武帝晏驾后遭到自己得罪过的太子据报复。当公孙贺父子行巫蛊事被朱安世揭发之后,汉武帝决意“穷治其事”,亦即予以严厉惩治,牵连所及,甚至包括阳石、诸邑两公主等亦未能宽免。江充从汉武帝对待此事的态度上,为自己找到了一线生机:“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亦即期望整治那些对汉武帝行用巫蛊的人,从而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太子据因怨望而施行巫蛊的证据。

汉武帝这一任命,正中江充下怀,给了他直接下手的机会。——如同当年报复害死其父兄并差一点儿杀掉自己的赵太子丹一样,他可以通过举发太子据的巫蛊行为来彻底除掉对方。
那么,江充又何以会预知太子据必定会在宫中施行巫蛊以祝诅汉武帝呢?关于这一点,江充倒未必具有十全的把握。不过,因为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做法,所以太子据这样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江氏别无他法,只能借此求其一逞。




江充的目标,是太子据。但直接冲着太子查将过去,报复的用心,过于明显,而且在太子宫中到底能不能查到巫蛊的证据,也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万一一无所获,恐怕会给他引来更为直接、也更大的麻烦。特别是如上所述,当时的朝野官员,大多数人对此都漠然视之,不愿深追清查。若是贸然侦办太子,一旦失手,周遭人这种普遍的敌视态度,会使其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但在另一方面,其他官员之所以都不愿侦办,江充又恰恰敢于放手查拿,并且预期会有所收获,都是由于施行这种巫蛊法术,在当时本是一种从上到下普遍流行的行为。


形象地说,当事人是在祝诅隔壁的老王,还是未央宫中的汉家天子,这需要在作法时通过具体的祝语来表述。因此,其所行巫蛊,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属于正当的行为抑或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实际很难界定,巫蛊之事自然随之愈为通行。不管具体怎样施行法术,江充在短时期内,就抓获如此众多的疑犯,这已经充分说明民间行用巫蛊之术的普遍程度与巫蛊之术的兴盛景况。基于这一背景,似乎不难想象,在汉武帝末年民怨几近沸腾的情况下,总会有一部分人会以巫蛊诅咒武帝刘彻速死;若再加以酷刑逼供,自然会有更多的人被屈打成招。
结合前后发生的史事,可以判断,江充指使人动用酷刑,逼使具有相关巫蛊活动迹象的人,承认是在针对汉武帝作法,凸显这种活动的广度和强度,显现事态的严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加重汉武帝对巫蛊行为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揪出这些小人物之后,汉武帝的病情,并没有缓解,这自然会把汉武帝的注意力,引向地位更高、与其更为亲近,从而造成更强巫蛊效果的人身上。——实际上,是要把究治巫蛊这一举措引向太子据那边。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去,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汉武帝因壶关三老等上书到底“感悟”了些什么,以及《汉书·戾太子传》所记“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这话究竟该怎样理解。
如前所述,壶关三老令狐茂开门见山,提出太子据一案发生的前提,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这实际上是讲汉武帝因后宫私爱而想要无故废黜刘据的太子地位,这是太子据后来“子亦不子”的根本原因,亦即前文所说汉武帝行事有过在先,太子据行用巫蛊既事出有因,同时这也是当时很通行的一种很一般的社会习惯做法,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严厉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辨明内外亲疏的区别,看破江充所谓“奸诈”用心。——我想,这应该就是汉武帝从令狐茂上书中所能得到的主要“感悟”。



题侯张富昌,以山阳卒,与李寿共得卫大子,侯巨鹿〔谓食邑巨鹿〕。邘侯李寿,以新安令史,得卫大子,侯河内〔谓食邑河内〕。师古曰:“邘,音于。”《百官表》亦作邘侯。又《武五子传》诏曰:“其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韦昭曰:“邘在河内。”孟康曰:“题,县名也。”晋灼曰:“地理志无也。《功臣表》食邑巨鹿。”师古曰:“晋说是也。”《汉纪·孝武纪》题侯作踶侯,邘侯作抱侯。

所论“踶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足证李寿和张富昌之受封为侯,都是汉武帝所谓“感悟”的一种表现形式。
五、汉廷对太子据施行巫蛊事的认定



这就更是自我作古,强以清人之曲意而加诸西京之帝君。




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田千秋在升任丞相之始,目睹汉武帝为太子据之案,牵连诛杀惩罚人员过多,群下为之恐惧不安,为“宽广上意,尉(慰)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徳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而汉武帝却答复说:
朕之不徳,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案“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即汉人司法术语“案验”之具体操作。汉武帝说道,直到现在他还受到巫蛊的困扰,谈不上什么寿不寿的。当初江充入宫搜查巫蛊,各相关部门并没有举报他的图谋。现在你田千秋作为丞相,亲自在兰台挖掘偶人来验证,看到巫蛊之事是确实存在的。——这些话等于是说江充虽然另有图谋,醉翁之意本不在酒,但太子据行用巫蛊,实亦确有其事。
至于《汉书·戾太子传》等处记载汉武帝在连连接到壶关三老令狐茂和高寝令田千秋的上书之后,因“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进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云云,对比上述各项实质性内容,便不难看出,不过是一种自我装点的门面事,用以遮掩其为父不父、为君不君而逼使太子据施行巫蛊并最终引发兵变的尴尬行径。
2016年3月10日晚记
注释
①⑨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五章第十一节《巫蛊之祸》,第146-149页,第147页。
②《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卷二八《封禅书》并唐张守节《正义》,第1656-1657页。
③④《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541页,第537页。
⑤案关于《史记》这段文字的标点,别详拙文《中华书局新印纸皮简装本〈史记〉补斠》,待刊。
⑥《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335页。

⑧《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六《武帝纪》并唐颜师古注,第203页。
⑩案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乙帙《秦汉》之第四一九条“禁巫祠道中”条(第820-821页)对此有更为具体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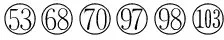





















责任编辑梅莉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ursing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the Crown Prince of the Emperor Wu in the Han Dynasty
Xin Dey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Under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Wu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crown prince Liu Ju (刘据) was accused of conducting cursing activities and compelled to start a palace coup, but he ended up in a total failure and committed suicide. The later researches, however, defended Liu Ju against the cursing activities by saying that it was a political frame-up by Jiang Chong (江充) and Liu Ju was innoce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Liu Ju was not as innocent as some of the researchers assumed. Firstl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s long as the object of the cursing was not the emperor, the cursing activities were not considered as crimes. Secondly,HanShutruthfully recorded the process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cursing dolls in the crown prince’s palace. Jiang Chong just took advantage of the fear inside the Emperor Wu in order to get rid of Liu Ju. The Emperor Wu’s intention to change the crown prince was the trigger for this severe palace coup.
the Emperor Wu; crown prince Wei; the cursing activities
2016-03-11
国家哲学社会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地图绘制”(13&ZD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