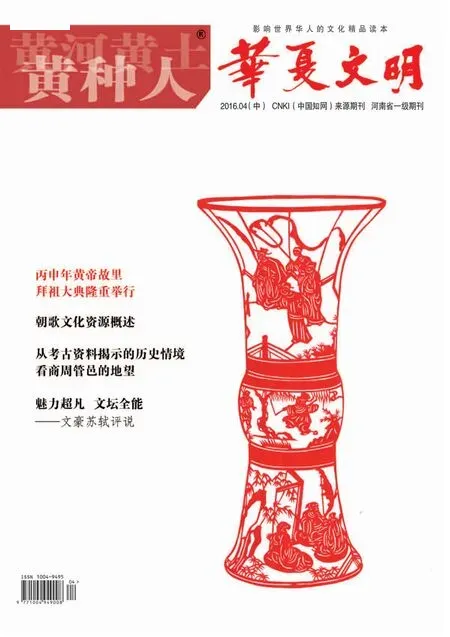陶寺文化的兴起及相关问题
□赵江运
陶寺文化的兴起及相关问题
□赵江运
陶寺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主要分布于晋南临汾盆地、以陶寺遗址命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陶寺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发现以来[1],随着遗址的不断发现以及资料的不断公布,相关的研究文章也层出不穷,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地扩充。然而,检索过去发表的相关论文,研究者主要集中于对其文化性质的讨论[2]、分期与地域类型的划分[3]、族属的认定[4]、聚落形态的研究[5]、社会发展水平的探讨及其总体面貌的综合研究[6]等方面,少有对其兴起原因的讨论。此外,从考古发现来看,陶寺遗址在陶寺文化早期时,突然出现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城内建筑设施以及城外墓地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复杂化水平远远高于该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之时。陶寺古城,如此疾风骤雨般的兴起显然有别于史前城址 “由小型聚落到中型聚落再到大型聚落最终发展为城址”的一般发展模式。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着谈一谈陶寺文化兴起的原因,以期进一步完善陶寺文化的研究体系,进而以此个案研究为例,谈谈史前城址起源的模式问题。诸多不足之处,还望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陶寺早期文化的界定
欲要探讨陶寺文化兴起的原因,首先要对其早期阶段遗存进行界定。而对陶寺文化早期遗存的界定是建立在陶寺文化分期的基础之上的。关于陶寺文化的分期,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期说”[7]和“三期说”[8]两种意见。“两期说”,由于提出的时间较早,所依靠的材料有限,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其虽然建立在对器物的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然而却没有经过定量分析,对其的定性也就存在问题了。而“三期说”,既充分考虑到陶寺以及其他遗址的文化面貌,同时又注意到其文化内部的阶段性演变,可以说,基本符合现有考古材料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何驽先生更是从文化因素分析入手,全面地比较了陶寺早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的异同,从而得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并结合其他文化因素而独立发展的一个新文化”[9],这一较为合理的结论。故而,本文关于陶寺早期文化的界定采用“三期说”的观点,即以陶寺遗址78ⅡH4、T401⑤、H439、83~84ⅢH379、H381、99ⅡH414[10]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关于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参考诸家观点及碳14测年,笔者以为2500BC~2000BC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
陶寺文化早期,在遗址的东北部已经建立起了一座面积达56万平方米的夯土城。城内有面积约6.7万平方米的宫殿区、1.7万平方米的贵族居住区以及分布有大量窖穴的仓储区[11]。此外,小城东南还发现有大片墓地,其中大多数属于早期,墓葬情况反映出较高的等级分化(图一)[12]。这反映出陶寺文化在其诞生之时,即已具有都邑文化的特征,成为整个晋南临汾盆地的中心。因此,笔者对陶寺文化兴起原因的探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陶寺遗址而言的。以下,笔者将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个方面来解析陶寺文化的兴起。
二、陶寺文化兴起的自然条件
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陶寺文化聚落群,位于晋西南临汾盆地浍河与汾河下游的交汇区,其北接吕梁山,西临黄河,南望峨眉岭,东倚太岳山和中条山,为一较为封闭的区域。盆地中部又以塔儿山为界,分为临汾和运城两个小盆地,陶寺遗址就位于塔儿山的北脊(图二)。

图一 陶寺早期小城布局示意图
根据环境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知,在陶寺文化时期,该地区处于暖温带林区,气候温暖湿润,是史前时期生活的理想之地[13]。适宜的自然条件为陶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临汾盆地周围的塔儿山、峨眉岭、中条山、太岳山和吕梁山为陶寺居民提供了制作石器的原料。在襄汾大崮堆山[14]还发现有采石场,其使用年代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因其仅距陶寺遗址6公里远,周围亦缺少大型聚落,且当地发现的石斧、石锛、石铲、特磬以及厨刀的毛坯与陶寺遗址发现的同类器高度相似,说明这里当有一段时间是为陶寺都邑服务的。
(2)根据孔昭宸等人对陶寺遗址出土孢粉和植硅石的分析,当地植被中存在大量的乔本科树木,而丰富的林业资源为大型建筑的建造以及日常的炊煮取暖提供了保障[15]。
(3)陶寺文化遗址多位于黄土台塬之山,既有一定的规模,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洪作用。黄土台塬相对平坦,满足建立城址的条件。但陶寺遗址位于塔儿山的北脊,受山谷风的影响以及地形雨的作用,很可能当时存在一定的山洪灾害。陶寺文化早期即已修建城墙,很可能考虑到了防洪的需要。
(4)根据对陶寺遗址中土壤的采样与浮选分析,发现有大量的炭化植物种子,其中以粟、黍类为主,还发现有很少的稻类种子[16]。这反映出当地的生态农业模式以旱地粟种植为主,这也符合当地多平坦台塬、有一定降水但不是很多的自然条件。
(5)汾河、浍河以及滏阳河等河流流经晋南盆地,这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日常生活以及陶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图二 晋南地形图
适中的地理位置、类型多样的地貌特征、适宜的气候条件以及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陶寺居民优越的生存环境。陶寺文化以粟作为主要的农作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为大规模人口集聚一地提供了物质保证。然而,优越的自然条件仅仅是陶寺文化兴起的充分条件,这并不能解释为何晋南临汾盆地自仰韶时代大暖期以来,气候条件都适宜人类居住的情况下,直到陶寺文化时期才发展为都邑聚落。因此,我们还得去深究文化发展背后人所起的作用,而这也是最关键的。
三、陶寺文化兴起的人文因素
临汾盆地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 “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文化”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一支考古学文化的兴起固然离不开当地先前文化连续发展所奠定的文化基础,然而陶寺文化都邑聚落“空降式”的出现表明,仅仅认为文化自然发展而形成的解释是行不通的,我们还需要寻找新的解释途径。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在陶寺文化的周围分布有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杏花村文化、老虎山文化与后岗二期文化,除了后岗二期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关系还不太明朗之外,其他皆或多或少有所互动与交流。而陶寺文化由于居于中心位置,能够引进与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这主要反映在陶器的不同形制上。而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的相互融合也就使文化的多样性更加突出,从而使得陶寺社会的运转机制更加灵活,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做出适时的调整,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下,笔者将用文化因素分析法来讨论陶寺早期文化中所见的周围同时期文化的因素。
陶寺文化遗址目前已发现256处,其中发现有早期遗存的就有72处[17],而已发表有资料的仅有陶寺、丁村[18]、曲舌头[19]、柴寺、侯村[20]等几处遗址。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陶寺文化早期的陶器主要有釜灶、斝、扁壶、矮足鼎、折腹盆、深腹盆、折肩罐、深腹罐、直壁缸、钵、碗、豆、甑、杯等。除去釜灶、扁壶等几种陶寺文化典型的器物外,其他器类多带有周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从以下具体器形来看:
折腹盆:陶寺遗址中的折腹盆与王湾三期文化王湾遗址的折腹盆极其相似,而折腹盆系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因此陶寺遗址的折腹盆的出现当是王湾三期文化影响的结果。
双腹豆、宽沿豆:陶寺遗址出土的双腹豆、宽沿豆在当地没有文化传统,在周邻文化中也不常见,而在屈家岭文化中则有较多的发现。又因为屈家岭文化晚期时存在北渐的趋向,其通过豫西南或豫南地区北上,进而影响到黄河流域。[21]在大河村五期文化(如大河村遗址和谷水河遗址均有发现)中存在大量的屈家岭文化因素,晋南地区也有发现(天马—曲村赵南遗址)。因此晋南地区的双腹豆与宽沿豆当是屈家岭文化北渐的结果。
深腹罐:陶寺文化早期的深腹罐的特征主要是侈口、束颈、溜肩,这与关中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常见的小口折肩罐的形制非常相似,两者当有一定的渊源。
斝:陶寺文化早期中的陶斝可以分为两种,即釜形斝和罐形斝。前者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多有发现,且从早到晚发展演变较为清晰,应是本地产物,而后者似乎是受到关中地区的罐形斝的影响才产生的,特别是单耳罐形斝更能看到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影子。
觚形器:陶寺遗址出土的觚形器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斜腹杯的形制极为相似,其制作工艺应当或多或少借鉴了来自南方的文化传统。
厨刀:陶寺遗址出土的厨刀,其形制非常独特,在周邻文化中没有发现。何驽先生提到陶寺文化的“V”字形厨刀的形制当来源于良渚文化老和山遗址出土的三角形犁形器,只是其功能有了本质的改变[22]。但是,囿于实物资料发现较少,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还不足。故而,笔者还是倾向于厨刀当为本地独立制造出来的。

图三
此外,陶寺早期文化中发现不少器物带有双鋬形装饰,而双鋬形装饰器在晋中杏花村文化中极为常见,而晋中晋南都处于汾河河谷地带,往来较为方便,因此陶寺文化中出现杏花村文化的因素也是合情合理。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陶寺文化早期中存在许多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因素,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陶寺文化的社会性质。陶寺文化中,外来文化的因素既可能是外来文化对其的传播,也可能是陶寺居民通过和平的交往或暴力的战争的方式带回来的。在此,笔者无意于探讨究竟是哪一种文化在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强调文化交流在文化的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以上,主要谈论的是陶寺文化兴起的外因,而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下面笔者试以陶寺文化政体内部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来看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从陶寺早期墓地发掘的700余座墓葬的情况来看,可以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其中大墓仅9座,中型墓80余座、小型墓600余座,呈现“金字塔式”的结构,等级分化非常明显。早期大墓除有木质葬具外,随葬品十分丰富,多达二百件,如M3015随葬各种器物178件,其中包括鼍鼓、特磬、异形器、玉钺、玉瑗、石镞(111件)、彩绘陶器、日常实用陶器和猪骨架等(图四)[23]。
显然,大型墓墓主身份显赫,当是陶寺早期都邑的统治者。而墓葬中,既有随葬象征军权的玉石钺、石镞,又有随葬较多的石、陶、木质礼器,如石磬、蟠龙纹陶盘、陶鼓、木仓形器等,显示出王权与军权的高度集中。这反映出陶寺社会的政体走的是“集权化”的道路,而这种集权化的社会往往能够集中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与生产活动。陶寺早期小城面积已达到56万平方米,中期大城更是达到280万平方米,这么大的工程显然不是单一聚落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当是地区内多个聚落的共同成果。这种高度集权的社会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在其早期阶段由于具有能够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以及加强区域内聚落之间联系的优势,故而能够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陶寺文化“都邑式聚落”的出现,显然与其选择集权化的发展模式有关。联系到陶寺文化中期时,出现大规模的礼制建筑以及更加注重礼制,陶寺文化似乎走上了与“良渚文化”相同的道路。陶寺古城在晚期虽然仍被使用,但是大型宫殿建筑被毁表明其政治中心的地位的降低。
总之,一支考古学文化的兴起既依托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也受其制约,特别是在史前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时期,这种制约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们主观能动性的提高,人文因素在考古学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陶寺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社会的复杂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自然条件的制约作用已趋于次要地位,人们可以通过彼此的交流以及长远距离的贸易来弥补自然条件的不足。这种不同地区文化之间频繁的交流与互动对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陶寺文化虽处于较为封闭的临汾盆地,但其北方的杏花村文化和老虎山文化、西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以及南方的王湾三期文化对其皆有辐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陶寺的精英阶层选择了一条能够短时间内促进社会发展的道路,晋南地区最终成为四方汇集之地,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
四、陶寺古城的兴起对史前城址起源的一点启示
关于史前城址起源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倾向于“战争说”和“防洪说”。虽然城址的功能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经济与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是伴随着城址发展而来的,是逐渐演化出来的。
从陶寺早期小城城内的建筑布局、功能分区和城外墓地高度等级化的情况来看,陶寺小城出现时,即已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取向,“卫君”“别贵贱”的政治功能已具备。此外,陶寺城址的防御性功能也较为突出。通过宏观的聚落分析,以及陶寺早期文化中晋中地区杏花村文化的因素所见甚少,似乎表明两者之间更多的是对抗。从地理条件来看,晋中、晋南同处汾河河谷地区,当时杏花村居民的南下不存在交通方面的困难。此外,南下的动力可以通过气候方面的信息来说明。龙山时代晚期,晋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气候较为干冷、生态条件趋于恶劣,岱海地区的老虎山居民不得不南下扩张以寻找更合适的生存环境。而晋中地区的杏花村居民迫于老虎山居民南下的压力,一方面进行抵御,另一方面不得不向南方和东方迁移 (如在后岗二期文化中就发现有杏花村文化的双鋬鬲),这就直接威胁到陶寺文化。此外,陶寺城址东、南、北面皆有山峦环抱,南方更有黄河相隔,其所受的威胁明显小于北方,陶寺早期小城的营建考虑更多的是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
至于陶寺早期小城的兴建是否与防御洪水有关,目前还不能找到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但从城址修建于黄土台塬之上,应当是考虑到了防洪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陶寺城址的营建主要是出于防御外敌的考虑,是战争所导致的结果,其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

图四 陶寺遗址墓葬M3015平面图
五、结语
陶寺文化作为一支新兴的考古学文化,在其早期时即已呈现出都邑聚落的特性,中期大城的面积更是达到280万平方米。社会发展之迅速、水平之高在同时期黄河流域较为罕见。通过对陶寺文化兴起原因的探讨,人们认识到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以及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一个文化的兴亡至关重要。陶寺文化盛极而衰的教训似乎影响到了王湾三期文化。目前,王湾三期文化的墓葬材料仍然很少,这或许反映出王湾三期文化的精英阶层更加重视现实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生产,而不是营建死后繁华的世界。龙山时代晚期后段,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已转移到王湾三期文化所统治的嵩山周围地区,王城岗、古城寨以及新砦等古城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
注释:
[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南五县古代人类文化遗址初步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09期。
[2]徐殿魁:《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02期。张岱海:《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3]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时代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03期。董琦:《陶寺遗存与陶寺文化》,《华夏考古》1998年01期。
[4]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 06 期。张德光:《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文物季刊》1989年01期。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06期。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文物世界》2001年01期。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与帝喾之都考》,《考古与文物》2007年01期。张国硕:《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考古》2010 年 06 期。
[5]高江涛:《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中原文物》2007年03期。许顺湛:《临汾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10年03期。
[6]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曹艳朋:《陶寺文化研究》,郑州大学,2009。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高江涛:《中国文明与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13。苏家寅:《史前社会复杂化理论与陶寺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罗新、田建文:《陶寺文化再研究》,《中原文物》1991年02期。宋建忠:《山西龙山时代考古遗存的类型与分期》,《文物季刊》1993年 02期。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
[8]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时代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03期。
[9][22]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文物出版社,2004。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Ⅱ区居住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03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03期。
[12][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01期。
[13][15]孔昭宸、杜乃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 02 期。
[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襄汾县大崮堆山石器制造场遗址1988—1989年的发掘》,《考古》2014年08期。
[16]赵志军,何驽:《陶寺城址2002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006年 05期。
[17]曹艳朋:《陶寺文化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10期。
[19]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襄汾县丁村曲舌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04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989年06期。
[21]孟原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华夏考古》2011年03期。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