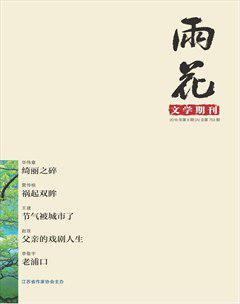末庄老A
王泉水
老A是最后一个搬离末庄的。他不是钉子户,老早就签定了拆迁协议,之所以迟迟不搬,实实在在是舍不得这片热土。
他太熟悉这里了,哪块土地上庄稼长得壮实,哪块土地上结得瓜果香甜……全在他心里搁着。
现在的末庄,面目全非,一片狼藉。实际上末庄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地名——末名山庄,不久的将来,这里是富人居住的地方。
“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的农家舍院推倒了;农业学大寨时开挖的,滋润周边四个乡的水库填平了;村里最肥沃最丰收的土地掺进砂子、碎石,浇上了混凝土……老A痛惜得心都颤抖起来。一路坎坷,一路沧桑,哺育了世世代代黎庶百姓的土地,就这么没了?!
拆迁,在局外人看来,不啻是天上掉馅饼,而且是掉天大的馅饼。事实也是,那些日子,末庄像过年似的,处处喜气洋洋,人人兴高采烈。一笔不菲的补偿款,一处满意的安置房,一个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生活环境,一桩让儿孙“跃出农门”享受幸福的愿望……随着拆迁,一件一件地变成现实。
乔迁新居的时候,老A快乐得像个孩子。他在电梯操作键上摁来摁去,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不为别的,就为坐坐电梯。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也让他咧着嘴儿开心地直说“好”,过去茅房,不管怎么弄,总有漏网的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让人无可奈何……
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像硬币的正面与反面。
新鲜劲过去以后,老A觉得,虽然是大户型居室,但比起农家小院,还是逼仄得慌。对门邻居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哪像在末庄,捧着饭碗可以到处串门儿,到哪,都能把筷子随意地伸向人家的饭桌。
有一天,老A见邻居回来了,就站在过道口等着,准备搭讪一下。他堆着笑脸招呼道:“你好!”邻居面无表情,生硬地问:“有事?”他没料到邻居这样对答,有点尴尬,慌乱中结结巴巴地说:“没……没事……”邻居听了一脸诧异,不再吱声。他思谋说点什么,还未来得及想出词儿,邻居已经开锁进屋,又随手“嗒”的一声关上了门,留给他的是冷冰冰的、厚实实的防盗门的钢板面儿。
还有,开门七件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要掏钱。掏钱倒也罢了,买回来的常常是假冒伪劣商品,掺什么三聚氰胺、苏丹红……能吃吗?哪像在末庄,菜是自家地里长的,随吃随采,绿色,环保;粮是自家地里种的,随吃随碾,无污染,无公害……
还有,在末庄,他是老把式,农活儿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土地听他的,庄稼听他的,乡里乡亲们也听他的。他说施肥,大伙儿跟着施肥,他说浇水,大伙儿跟着浇水……现在,他是什么?他会什么?不懂技术,也看不了图纸;不擅于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也不精通商战上的套路与韬略。离开土地,光荣地成为城里人的他,边缘化了……
老A怀念起末庄的日子。
那时候,无论多少落寞、惆怅,无论何种苦闷、烦恼,只要到田埂边坐上一坐,听听庄稼拔节生长的声音,看看深耕土地泥浪翻滚的俏模样儿,便什么都随风飘散了,便什么都遗忘在九霄云外了……
还有,末庄的大槐树,树身数围,荫蔽数亩。乡亲们都喜欢聚集在树下。姑娘、媳妇们做针线,忙手中活儿;男人们抽烟,喝茶,天南海北地闲聊;孩子们追逐、吵闹、嬉戏……天边,夕阳如火,晚霞似锦,暮归的老牛“喔呜喔呜”唱着,远处有牧童的短笛吹响……
那晚,闷闷不乐的老A,喝了几杯酒,酣然睡去,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还是孩提时代,父母亲在田里干活,他在田边玩耍,父亲教他:“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蓝天白云之下,他跟着一句一句地学,稚嫩的童音在广阔天地里清脆地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