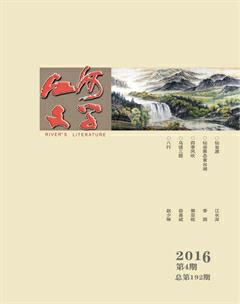江长深·仙翁渡
天街的北面是天台山,南面是天河,天街的街道虽然成天字形,但挤在这山与河之间狭长的地带上,远远看去显得很杂乱。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特殊的交通条件,天街南北交通受挫,出进主要靠横贯东西的古驿道。
天街人曾经有人想在天台山上凿一条栈道,打通南北的通道。风水先生袁祖明的父亲袁荫明听后,如同自家祖坟被人撬翻,一跳八丈。他拿着罗盘针站在天街口,对天街的老少爷们训话就像训斥自己做错事的孩子。他说:“天台山是天街的龙脉,就如同你们的骨骼精髓。天街自古以来之所以能够荣满朝廷显赫乡野,就是这条龙脉在奔涌着。如果在龙脉上修一条道,千百人走来踏去,龙脉就会枯竭,且不说富贵荣华难保,天灾人祸将是家常便饭。”主持修路的头人听了,吓得直伸舌头,觉得自己犯了天街的大忌,惶惶然在天台寺烧了三炉高香,诉说了自己的过失,请求先人宽恕,才把修路的念头放下。
也有人提出在天河上架一座桥。方案提出后,天街的响应者却很少,原因之一是南面多荒蛮之地,不通州府,无商货集散,缺乏沟通的基本条件;二是天河水患无穷,破坏性大,在天河上建桥,工程大、困难多,耗资也不是小数目,没有人敢挑这担子;三是天街上游十多里处有一官桥,曰银子桥,天街人南行虽然不是很方便,但不是没有出处。因此,修桥的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天街人要过天河,急有仙翁渡,缓有银子桥,各得其所。
早先的时候,天河上并没有渡。天街的人要过天河得逆着天河向东走十多里,过银子桥。十多年前的夏天,天河两岸普降暴雨,山峦飞瀑,田野汪洋,夫子镇一片泽国,人们举步维艰,困在家里望水兴叹。天街对面的天河,浊浪排空,湍急的河水狂泄不止,河水搅着上游冲刷下来的家具、禽畜和瓜果藤蔓,横无际涯,直卷而下。风浪中忽有一条小木船像快速飞驶的梭标直冲下来,在天河潭的急弯处如鲤鱼跳龙门,小木船飞到了河边的岩石上。这惊心动魄的瞬间留在了天街人的记忆里:又一曲人间悲剧在天河的大洪水中发生了。
几天几夜的洪水过后,被雨水淋湿心灵的天街人终于走出潮湿发霉的房子,勤劳的庄稼人开始打整被洪水浸损的庄稼,被洪水冲毁的田畴。有闲阶层漫步天河岸边,陶醉于灿烂的阳光下,晾晒被霉雨阴沉酥软的心情。咆哮了几天几夜的天河像厮杀溃败后疲惫不堪的狮子,安静下来。水经过几天几夜的沉淀已经变蓝,被河水刷白的沙滩映着骄阳的秀色熠熠生辉,白鹭翻飞着,在蓝天碧水之间织出纷繁的美丽。天街人在河堤上走着、看着,忽然有人发现天河上一个白发老翁驾一叶方舟穿梭在碧波之中。小舟如梭织绿水,老翁如画笑东风,天水人舟俱为一体,成为天河独特的风景——这就是洪水留给天河的礼物,这就是后来被天街人所称的天河上的仙翁和他的仙翁渡。
仙翁是天街人对驾船者的爱称,问他的真名叫什么,他朗朗一笑,答曰:“摆渡人”;问他来自何处,他用竹桨指着天河上游说:“我家就在天河之上,我是从上游漂下来的,天街渡口是我的归宿”;问他年龄,他答是花甲已过,不近古稀。人们见他闪烁其词不说详情,也就不好再问,封他以“仙翁”,封渡口为“仙翁渡”,权当是上天对天街的馈赠。
天河有了渡船,天街人出门方便许多。人们到南方去,不再弯银子桥的十多里路程,站在岸边喊一声:“仙翁,过河。”他立马回过一声唱和:
客官一喏我即来,
满河清水两边开;
今日有缘同此渡,
倾城富贵到客怀。
一曲唱罢,船就飞到了求渡者的面前。
叫渡船者为“仙翁”,绝非天街人空口奉承,而是实至名归。仙翁自有仙翁的容颜,仙翁自有仙翁的风骨。仙翁须眉白发,双目有神,突兀的宽额深埋着智慧,沐浴着河风的面颊和双臂、双腿如铜浇铁铸,苍劲有力。他驾船的技术娴熟,竹篙拨击水面,如蜻蜓点水,无论水流多急,小船如履平地。坐他驾驶的小船过天河,白云头上飘,绿水脚下淌,船歌耳边绕,真是一种享受。
仙翁以渡船为生,收费也很随意,手中宽绰,多给一点他不拒;一时手短为不来,不给钱他也渡。大户和生意人家给银子铜板行,庄户人捎些米面油菜也未尝不可。天街的人非常喜欢他,有了新鲜的东西忘不了送他一份,节假日过渡走亲戚,有什么好吃的也得给他留着。仙翁很快融入了天街的大环境中。
过了一些时日,天街人发现仙翁渡船遵循一个非常严格的规矩:只渡人不载物。无论白天黑夜,无论老少男女,再多人过河仙翁也不厌其烦地渡,如果你负荷着财物,他就让你弯天河上游的银子桥。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先说船小载不起。如果你继续追问:“你把人和物分开,分两次渡河不行吗?只要过渡人出钱。”仙翁见含糊不得,就露出不屑的表情答道:“世间的人和物,都各行其道。天有天道,人有人道,物有物道,模糊不得。我来此摆渡,是与人方便,而不是与物方便。方便之人方便过,是我摆渡的本分。恋物者图的不是方便,不方便就不应该行方便之道。”
天街是文化沃土,数百之众有贫富之分,绝无贤愚之别。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九流三教,都能知晓书理。仙翁渡主的这番宏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家喻户晓了。初次听时,大家还浑浑噩噩,不以为然,慢慢品味,也能品出一些味道。他们再到仙翁渡口审视仙翁,觉得仙翁看似平常最是倔,人格修养上了一个档次。仙翁虽做的是粗杂活路,却非行走在人间烟火中的等闲之辈。他们都自觉遵守仙翁的规矩,人过渡,有了货物过河就弯银子桥。
太极县县衙庄汝玉是天街人。有一日,他骑着高头大马回天街为自己的父亲祝寿。按照以往的惯例,他是要走银子桥官桥的。行前由于公务缠绕,耽误了时间,他担心影响寿宴,心里着急。随从说:“天河设有一个仙翁渡,我们改乘船回去,还来得及。”庄汝玉说:“仙翁渡我听家父说过,渡船的老头规矩多不好说话,我们还是赶紧走银子桥。”随从辩说:“你既是太极县的父母官,又在天街长大,再不好说话这点面子他能不给?无非是多给点船费就是了。”庄汝玉看时间不早,就依了随从,抱着侥幸的心理,走小路过天河渡。
主仆二人到了天河渡口,随从吆喝着要过渡。仙翁听见喊声,青篙点过,从岩石后闪出,船如利剑划开水面。仙翁在船上唱道:
客官过河我撑船,
我与客官不一般。
今生一次同舟过,
写就来生一世缘。
歌罢船到,大喝一声:“客官要过河么?”
随从答道:“是明知故问怎的,不过河站在这里当河神?我可要告诉你了,这是太极县知县、天街庄老太爷的公子庄县爷,要过天河去给庄老太爷祝寿。”
仙翁站立船头,白发轻飘,两耳临风,并没听进什么。他见随从右手牵着马,左手扶着县衙向船上走来,仙翁道了一声:“慢!”青竿一点,小船离岸五尺。庄知县主仆二人不解,两双怒目扫来,如芒似刺。仙翁赔了一个不是,解释说:“客官有所不知,仙翁渡为的是过往行人的方便,设渡之初就立有规矩,只渡人不载物,更不能人马同载。客官请走银子桥吧。”
随从恼了,指着仙翁发问:“只渡人不载物,这算哪家定的规矩?在太极县境内,什么规矩都由我家老爷说了算。你把船开过来,渡我们过去,少不了你的银子;耽误了我家老爷祝寿的大事,跟我到县衙问罪。”
仙翁也不急躁,立在船头,平和地笑着说道:“这位客官,县爷回家为太爷祝寿,事在急中,就不要浪费时日,你快快扶县爷骑马上路吧。至于草民立的一些规矩,县爷要治罪,还不是信手拈来,何必去县衙。”
随从铁青着脸,又要说什么,被庄汝玉止住了。他传过话说:“既是摆渡的规矩,我们不过也罢。只是我想问个明白,人与物千丝万缕相连,人离不开物,物少不了人,你一个摆渡之人,为何要分得如此清楚明白?”
仙翁朗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理论过多次了,天街是家喻户晓。县爷如若仅是好奇,不问也罢;要想深究下去,赶回家问问你家老爷吧。”话完,再拨青篙,小舟如叶,划过碧波,回到河中。
随从在岸边手舞足蹈:“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仙翁道:“我等你们再来天河,但不要牵马。”
仙翁渡成为天河一景。天街人得了空闲,就到天河岸边,有人过渡时看仙翁摆渡,没人过渡的时候,就陪伴仙翁在水中划船。仙翁有一手绝妙的划船技艺,小船在他的脚下就像一头灵活的小鹿,他手中的那一竿青竹,就如同驯鹿的鞭儿,指挥着“小鹿”在水中温顺地划行。他们也试图与仙翁谈论一些家事国事,仙翁回答这些问题时有意搪塞,笑说:“家事知今不知古,国事知古不知今。”如若有人继续追问下去,他就大谈他独自一人的好处,如何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何前不忧先人后不思来者;或者大谈三皇五帝,唐太宗杀兄继位,隋炀帝弑父篡权,等等。说得听者一脸雾水,只得丢下此题论及其它。
有一天夜里,仙翁在河边的草棚里歇息,听见河边有人急喊渡船。他翻身起来,边穿衣边向船边走。对于夜晚渡船的人,仙翁特别留意。他知道不是紧急事谁愿深更半夜到河边渡口来。摆渡之人,白天摆渡没什么,只有到了晚上,给人方便才到了实处。
仙翁来到河边,解开缆绳,才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劲。岸边的天街已经轰动起来,灯笼火把照亮了半边天,他们一边呼喊着“抓贼啊,抓贼啊”,一边向渡口这边跑来。而站在船边的两个人,一人背着一个布口袋,十分慌张。仙翁一看心里就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正是被天街追赶的贼。他们想背着偷来的东西,逃过河去。
仙翁十分镇定。他立在船头,青篙戏水,其声如歌:“客官,仙翁渡的规矩,人物两分,人不问身份,有求必应,物不分贵贱,与渡无缘。客官若要走人,就请上船,如果是人物全走,请走银子桥。”
贼人也没回话。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人从腰间抽出一把小刀抵着他的胸口说:“少废话,你是要规矩还是要性命?送我们过河一切好商量,否则,你这渡也就摆到头了。”
抵在胸前的那把刀,仙翁看都没看一眼。他平静地说:“别说凶狠话,兄弟。把东西留下,你们俩要过河,我送你。不管你是什么人,做过什么,来到渡口,就是我的客官。摆渡之人,送客是我的本分。”
俩贼人不听劝说,一人提东西上船,一人拿着刀逼仙翁上船。仙翁仍然平和,面对着刀口,说话的语气如同在茶馆与朋友交谈。他说:“兄弟,你我上了船,我就能把你们送到对岸么?你急了拿刀逼我,你看我是贪生畏死的人么?还是听信我的一句话,先保全性命吧。与人的性命相比,什么样的东西还能珍贵?什么样的东西不能抛弃哩?”
灯笼火把越来越近,喊声越来越近,河岸上可以看见奔跑的人影。俩贼人没办法,将两个布口袋甩上岸来,愤愤地说:“别啰嗦,今天就依你,送我们过河。”
仙翁说:“兄弟,别不高兴,你这样做就对了,弃了外来财,避开杀身祸,值!”话毕,仙翁轻起一篙,小船如箭,向对岸飞去。
仙翁的小船从河对面开回来,天街的人有些愤怒,埋怨他不应将贼子放走。仙翁说:“歉意歉意,宽宥坏人,是我的罪过。”他立于天街人面前,深深鞠躬,一边请求给自己治罪,一边又为贼人开脱,他说:“盗物为贼,人家既已把东西留在天街,光身离去,虽有贼行但无贼实,悔过之心可鉴。仁者当宽待有悔心之人,给人一条生路,胜造十级浮屠。”
天街人虽然愤怒,但见仙翁不仅俯首请罪,而且所言不无道理,也就宽过了他。
仙翁以仁者之心放过了贼子,可贼子并没有放过他。一个月以后的一天黄昏,仙翁正要罢桨歇息,南河岸上急走下两个人,他们也不招呼,黑着脸走到船边。仙翁以为两人有急事渡河,忙问道:“客官要过渡吗?”两人不回他的话,跳上船头,一边站立一个,问:“你认识我们吗?”仙翁定睛一看,知是那晚过河的贼人,心里微微一笑,我仙翁苍蝇飞过能识公母,况两个与我有过几回合的贼子,但为了不给他们难堪,笑笑说:“客官虽尊,但都为渡口的匆匆过客。仙翁渡虽小,每天也有百儿八十的,我怎能一一记得清楚?客官为缘分而来,相识与否已不重要了。”
两贼人轻轻一笑,说:“我们没兴趣听你讲这些。既然你如此健忘,那就让你长点记性吧。”话毕拳到,正中仙翁右眼。仙翁觉得眼前一黑,在船头晃了晃,也不容仙翁解释,又有一拳打来,击中左眼。仙翁站立不住,落入水中。两个贼人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挥舞着撑船的竹篙迎着他的头部猛击。仙翁在水中挣扎一会,便不省人事。
仙翁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河边的草棚内,旁边坐着的是天街药房的掌柜张承良。张承良见他醒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总算醒过来了。”
仙翁醒来,马上就记起了河中发生的一切,他问:“张先生,是你把我从河中救起来的?”
张承良拿来一杯开水,扶他起身喝下,说:“是的。也算是好人命不该绝。我从太平谷行医回来,本打算走银子桥的,看看天色已晚,就改乘船回天街,走到渡口一看,只见船不见人,我以为你回棚歇息了,站在河边喊了一会儿,不见人应。我怀疑出事,走到船边一看,果然出事!你已经躺在河水里,不省人事,摸摸脉门,还有一口气。我就把你背上船。如果我晚来一步,你就没命了。”
仙翁看了看棚外晾晒的衣服,又看了看棚内的一些药罐和水盆,感激地说:“张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张承良说:“这就是仙翁见外了。救死扶伤是我医者的职责,就如同你渡人过河一样,本分之事,何谢之有?伤口我已经处理过了,都是些外伤,好好调养几天,就会好起来。”
仙翁点了点头,说:“因我处事不周,拖累于你,实在过意不去。”
张承良说:“人命关天,哪有不救之理。在天街别说遇上我,任何人也都责无旁贷。”他停了停,望了望天河和天街,又将目光缩回,停留在仙翁的脸上,若有所思地说,“我就是有一点不明白,你在天街无亲无故,无财无产,也没沾谁惹谁,谁的心那么狠毒,起心加害于你?”
仙翁犹豫一阵说:“你记得那天我送过河去的两个贼人吗?偷了天街的东西,被我放跑了,还劝天街人同情他们。”他叹了一口气,自责道,“宽宥孬人,也算是一种因果报应吧。”
张承良说:“那帮贼子,以德报怨,真是蛇蝎心肠,太狠毒了。这一篙下去,差点要了你的命。”
仙翁见张承良紧盯着自己头部不放,猛然地想起了什么,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大吃一惊:“张先生,我,我,我的头……”
张承良也想起了什么,他急忙从床前抓起一个白发发套,看了看,说:“是不是这?”
仙翁一把抢过,就要往头上戴,边戴边说:“你,你怎么,随便动别人的东西?”
“慢!”张承良止住了,说:“你的头上有伤,我刚缝过针,发套不能戴。”
仙翁手里抓着发套,非常痛苦地说:“你,发套,你怎么能把我的头、头、头……”语无伦次一阵后,他忽然长叹一声,“哎,这就是,就是命,天命难违!”
张承良见仙翁如此痛苦,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对不起,我一定是触到了你的伤心处了。其实,我不是故意的,当时你的头部流血,创伤很大,我想给你缝合伤口,没想到会是这样,这这,如何是好。”
听了张承良的回话,仙翁的情绪马上镇定下来,他觉得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张先生,忙着解释说:“张先生别自责,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这么多年,天街人对我这么好,可我一直隐瞒着,年纪轻轻以老者自居,充什么仙翁,这以后,该怎么面对天街,面对世人?”仙翁说着,说着,眼眶里的泪水如珠落下。
张承良行医多年,极其善解人意。他见仙翁落泪,就劝他:“人各有秘密,只要不影响他人,保守这些秘密也不能算错。不瞒你说,第一次在渡口见到你,我就怀疑你的年龄,这次给你号脉的时候,也证实了我的猜测。但猜测归猜测,求证归求证,我是一个不随便走进别人秘密的人,更不会为别人隐匿的秘密去求证,这是我行医的原则。这次,要不是给你的伤口缝针,无意间打开了你的发套,走进了你的秘密,我宁可让我的猜测变为空穴来风,也决不会去作无谓的求证。”
听了张承良的一段真心表白,仙翁深受感动,他伸出手轻轻地握了握张承良,说:“谢谢你,张先生,谢谢你的理解。但,但是,我欺骗了天街,天街的人都能有你一样的见识一样的胸怀?不把我当骗子?”
“这个我就不能担保了。”张承良见仙翁露出了无奈的表情,沉思了好一会儿后才说:“不过,如果天街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如果你觉得还有继续保守秘密的需要,我一定把这个秘密继续保守下去。你能相信我吗?”
仙翁深深地点了点头,说:“我并不想保守这个秘密,但是现在我又不能不保守这个秘密。公开这个秘密,需要时间,也许一天两天,也许一年两年,也许……”说到此处,仙翁停了停,绝望地说,“也许,这个秘密我要带进坟墓,今生今世也不可能公开了。”
张承良觉得仙翁的话题太悲凉,太沉重,为了宽慰他,张承良说:“不管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你愿意,我就会像保守自己的秘密一样保守你的秘密。”
“我相信你的人品,也相信你的承诺。”仙翁思索一阵后想起一个问题,他问张承良:“我有点不明白,你既然知道我的假象,也知道我藏有秘密,怎么不问声为什么?这是任何人嘴边的话题。”仙翁盯着张承良的目光,他觉得张承良深不可测。
张承良淡淡一笑,回答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是医生,懂得病人掩饰伤疤的无奈和揭开伤疤的痛苦。人活在世上,谁都不愿意有伤疤,有了伤疤,谁也不愿意挑破伤疤。我怎么会那么无聊,去挑破别人的伤疤,窥视别人的痛苦?”
张承良的话至情至理,恰如金玉之声,仙翁一听,失声痛哭起来。那哭声似六月的雪、晴空的雷,惊天动地,静静的天河被感动了,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像是与他一起悲怜,一起呼号。
张承良的心在剧烈地颤抖,他不知该如何劝慰这颗受伤的心灵,让他回到从前的状态。仙翁哭了一阵,挣扎着爬了一会,支起上肢,突然匍匐在张承良面前,说:“贵人啦,我今天遭此大难,纵有十条性命也绝了,幸亏遇上贵人,才得以残活。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
张承良扶住他:“别这样,别这样。出了这间草棚,你还是仙翁,摆你的仙翁渡;我仍是医生,采药看病人。今天发生的事,我当没见过没听说。”说完,收拾好自己的药箱,交代仙翁,“我给你留的这几副草药,疗效很好,敷几天伤好如初。头上的那处伤口,缝合了几针,抽线得等几天,出门戴假发,小点心。本来打算让你到我家里住几天,现在看来没有必要。自己好生照料吧。我走了。”
仙翁挣扎着要送他,被他止住了。
第二天早晨,仙翁渡口风平如昨。
仙翁和他的小舟准时准点出现在天河上,依然是目光深邃、脸如铁铸,依然声音洪亮、白发飘飘。那丈二竹篙在他手中如驯鹿的鞭子,把小舟驯得自由如梭。张承良到太平谷去看昨天的病人,成了仙翁新一天的第一个过渡人。张承良寒喧几句后,坐在船上,双手抱着药箱,目光紧盯着船头,看河水撞击的水花,不再发话。仙翁有些不好意思,找了一个话题说:“太平谷远么?你大概什么时间能回来?”张承良收回系在船头的目光,看了看仙翁撑船的身姿,回说:“不远,上岸以后很快就到。今天你不必等我,太平谷看完病后,我要上太平山采些草药,还是过渡的老规矩,回来时走银子桥。”仙翁笑了:“如果回来太晚,你背的那些药材,我就当没看见。”张承良回说:“你不遵守过去的承诺了吗?”仙翁不好意思地说:“你当别论。”张承良黑了一下脸,说:“你不要还在昨天的阴影里,就当昨天的事没发生,该咋样还是咋样。”仙翁大喜,放声一喏,唱道:
客官过渡我撑船,
我与客官不一般。
风雨人生君莫笑,
来生有幸报今缘。
唱罢,两人相互对望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笑了。
到了秋天,天河两岸金黄的稻子收割了,成片成片的棉花地里雪白雪白的棉花归了仓,忙碌的人群不见了。成群的白鹭在蓝天绿水中自由自在地飞翔,肥沃的土地在丽日蓝天之下延伸,就像刚刚分娩过后的贵妇人一样温馨和安逸,忙碌的天街进入了丰收后的休憩期。每年到了这个时期,仙翁渡也该清闲下来,除了三五个由南岸嫁到天街的小媳妇背着孩子回南岸的娘家省亲,仙翁渡也少见其它过渡客人。但今年的秋天似有些不同,除了那些省亲的小媳妇以外,来天街的人比过去多,仙翁记得有些是熟悉的面孔,有些还陌生。开始仙翁并没有留意,送他们过河也就算了。有一天,一个教书模样的中年人上了他的渡船,很随意地问了问天河渡的情况,然后向他问起天街的一些往事。仙翁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知道的他答了一些,不知道的就摇头不答。中年人也很平和,对天街的历史掌故知道不少,称天街人杰地灵,为国之罕见。他说:“这次来天街是作些考察,打算著一本《天街秘考》,以飨世人。老者长期在此行渡,自然知道不少。”仙翁说:“我不是天街人,知道的也很有限,你还是去天街向那些老者了解吧。”“啊!”中年人怔了怔,说:“难怪。看你一头白发,在此摆渡也有不少时日吧?”仙翁心里有了一丝震懔,他略略思考了一会,回说:“一晃有十几年了。”中年人说:“一个外乡人,在此风餐露宿十几年,真不容易。这也是《天街秘考》的极好素材。改天我们抽点时间好好谈谈?”仙翁觉得中年人的目光有些清冷神秘,不敢深谈,看看船已靠岸,就附和着说:“行啊,在天河摆了十几年渡,没想到会成为你书中的人物要流芳千古了。”仙翁自笑,目送中年人去了天街,看看天色已晚,就抛锚停渡。
第二天清晨,张承良去南岸治病,走到天河渡前,发现渡口集聚了许多人。他不知发生了什么,走近一看,见是庄汝玉和一些官兵。他马上想起了仙翁的那头假发和那次欲说还休的秘密,他知道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他壮着胆子走到渡口,发现小船和仙翁不见了。他不知是高兴还是失落,表情有些生硬。庄汝玉走过来问他:“那家伙可能会逃到什么地方呢?”张承良反问道:“他在此渡船十几年,犯了什么事吗?”一个教书模样的中年人走过来,看了一眼张承良,淡淡一笑说:“都说天街地灵人杰,却让一个朝廷要犯在此生活了几十年,传出去实在让人笑落大牙。听说你还给他把过脉,看过病?就没有看出点蛛丝马迹?”
张承良记起来了,就是这个人,今年秋天经常在天街一带活动。张承良在乡间行医时多次遇到过他,说是写什么《天街秘考》,来天街一带搜集素材。他还跟这个人讲过白鸽庄的故事呢,没想到他不是什么作家,而是朝廷的探子。张承良有了受骗的感觉,觉得这个人太阴险,心里本来就有些反感,见他盛气凌人的样子,心火已烧到眉前,他生生地回了一句:“一个朝廷要犯,十多年逍遥法外,责任能在天街?一个行医看病的乡间医生能够破案,朝廷养那么多捕头干什么?”
庄汝玉了解张承良的脾气,担心他俩发生争执,忙过来调停。他对张承良说:“这是巡捕房的洪捕头,具体负责这桩大案,十多年来洪捕头苦没少吃,路没少跑,最近在天街作了广泛的调查,昨天才有些眉目,没想到他晚上跑了。”
虽然看不惯洪捕头的那一副嘴脸,但把仙翁与朝廷要犯连在一起,他还是有些不相信,他问庄汝玉说:“仙翁犯的是什么罪呢?在天河渡口,我们觉得他特好的。”
庄汝玉说:“洪捕头跟我说时,我也有些不相信。他实在伪装得太像了,欺骗天街十几年。你们不知道吧,他的父亲是掌管京城漕运的一品大员,利用职务之便,在江南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人为地制造了江南百年不遇的饥荒,使美丽的江南盗贼四起,饿殍遍野。朝廷文武百官深恶痛绝,皇上下令抄斩满门。行刑的那天,天空突然猛降暴雨,刑场一时混乱,他的父亲和家人都行刑了,只有他一个人乘机跑脱。洪捕头十几年一直在找他,全国都跑到了,没想到他隐姓埋名,乔装打扮,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啊!”张承良夸张地“啊”了一句,表示自己已明白。
仙翁跑了,仙翁渡没有了,天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河水空流,水波不惊。过惯了仙翁渡的天街人很是不方便,他们想念仙翁,埋怨庄汝玉多事,让洪捕头在天街抓人。他们说,一个贪官的儿子,埋头在此摆渡十几年,死罪也该赎活了,还要抓人家,罪过,罪过。还有人提议,以天街的名义联名写一封书信给当今皇上,十年风雨,迎来送往,实属不易,不管仙翁死没死,免了他的死罪吧。死了,让他来世清白;没死,让他恢复本来面目,活得轻松一些。
张承良接到天街人联名信笺时,心忽然放飞出去,飞到了天河渡口,他想起了仙翁曾经讲给他的一个谜语:
想当年绿叶婆娑,
到而今青少黄多。
自从随君后,
受到多少折磨,
多少风波。
到而今
休提起
提起了泪洒江河!
当时,看到仙翁手握竹杆,须髯飘拂,白发临风,立在方舟之上,张承良很快猜到了物。仙翁听了,轻轻一笑,未置可否。如今想起来,他只答对一半,仙翁要告诉他的是人而不是物。
休提起,提起了泪洒江河。谜语后的两句话让张承良心灵颤抖不已,他主意已决:人随风远,祸福皆自由他吧。
张承良没有在联名信笺上签名,他不想提起仙翁泪洒江河的往事。
联名信最终还是送到了县衙,庄汝玉看了也没后话。几个月后他回天街,提议在仙翁渡口处建一座石拱桥。
据说建桥的资金原本由太极县衙出,后来建桥者在南北两边选定的桥墩处挖出了两坛金银,建桥的资金一下子就凑齐了。
桥建起来了,天街人仍沿袭过去的叫法,叫过桥为过渡,桥也不叫桥,而叫仙翁渡。
责任编辑: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