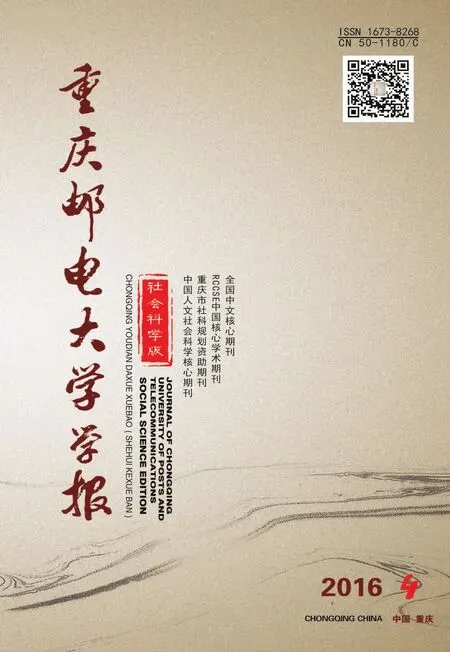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
王伯承,倪嘉颢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
王伯承,倪嘉颢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考察人口流动问题,就是坚持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观察现实,是研究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人口学、经济学分别从人口迁移、劳动力配置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人口流动问题,却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农民工回流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户籍制度障碍、政府的政策效应、城镇和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是农民工回流的外部社会原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健康状况、技能和家庭事件等是农民工回流的个体原因,农民工回流即是这两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个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回流是农民工自主性的一种体现。虽然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区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但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以及农民工对现实的考量才是回流产生的根本原因。主动回流与被动回流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如何将这种农民工回流的能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智力,需要制度扶持和政策引导。
关键词:农民工回流;个体选择;户籍制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人民公社的解体、票证制度的废除、高等学校恢复统考招生制度,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开通,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农民可以到城镇务工、经商,大批农民从农业和农村向非农业和城市流动,社会成员可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所以社会流动率明显提高了,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从社会平等和社会融合的理念出发,解决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的城市户籍身份,实现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无疑是应该的,也是最理想的。不同的学科,特别是人口学、经济学都从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出发对此进行了阐释,但是这些观点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假设,即农民工都愿意放弃农村户籍、选择城市户籍,进而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定。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农民工人口迁移并非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的单向位移,农民工重新返回农村的反向迁移现象也持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农民工回流问题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农民工回流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出发,坚持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关照现实,进而对农民工回流的现象进行系统的解析。
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考察当代农民工回流的理论工具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农民工回流现象
坚持唯物史观,就是坚持用生产力的观点来看待农民工回流问题,观察到其中蕴含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对于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人口流动现象,恩格斯写道:“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要,工人工资提高了,因此农民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1]而现在却产生了回流的现象,这种规律性表现为:大批农民工回流,是因为城市产业的更新换代,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结构由体力劳动型向知识型、技术型转变,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和技术更新需要的低水平体力劳动者被迫回到农村。此外,从现代社会城市化的角度看,有些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顺利地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而市民化的失败者则被迫重返乡里。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时期,城市化水平要与其物质基础或经济承载力相适应。在城市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承载力尚未达到容纳足够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时,过度接纳农民工就有可能造成贫民窟和影响社区治安、城市和谐稳定的情况;部分农民工的回流,实现了农村作为社会稳定蓄水池的功效。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农民工回流是我国转型期和经济社会发展特殊阶段的一种外在表征。
(二)用辩证唯物主义考察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农民工的流出和回流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层面。农民工的流出,体现的是城市地区工业生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而农民工的回流却反映了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同样对劳动力有旺盛的需求。社会发展合力论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2],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合力的思想启示我们: 在历史合力的构成中,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都发挥着不同作用,在具体而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在中国,劳动力迁移是一个可逆的过程,不论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还是从城市回流到乡村,毋宁说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双向的互动,是一个流出与回流相互博弈的过程,并且它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致力于完善的最终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观察资本主义时,也看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对农民素质提升的积极作用[3]。在城市务工的经历不仅带来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也带来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县域经济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并逐步形成了现代生活的物质条件。农民工返乡后,虽然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经历了现代化的塑造和洗礼;不管是返乡自主创业还是从事其他行业,返乡农民工都成为了乡村建设中的新鲜血液。最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其政策启示是: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在政策的设计上必须要保证回乡农民工再就业和创业的积极性。
二、相关的理论研究视域及其批判
人口流动和劳动力配置不仅是人口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同时又与社会经济系统密切关联,因而农民工问题一直是人口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来探究人口流动现象,为研究农民工回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视角出发,这些理论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一)人口学的视角及其批判
人口学主要是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对农民工回流活动进行考察。最早从人口学视野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是英国学者雷文斯坦(E.G.Ravenstein),他曾总结出迁移的七大定律:第一,大多数的迁移是以短距离迁移为主;第二,迁移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先是就近流动,再往更远的地方流动,且迁移者会随着距离的延长而减少;第三,每一个迁移流都会带来作为补偿的一个逆迁移流;第四,做长距离迁移的人通常是由于对大的商业和工业中心有喜好才前往;第五,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容易迁移;第六,从性别上看,女性比男性更有迁移的动机;第七,主要的迁移动机是经济因素[4]。雷文斯坦对人口迁移的观点被认为是“推-拉”理论的起源。E·S·李在雷文斯坦迁移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四方面因素:第一,与迁出地相关的因素;第二,与迁入地相关的因素;第三,介入障碍;第四,迁移者的个人因素。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相关的因素包括就业机会的评估、生活条件、生活成本、基础设施的可利用程度、歧视性待遇的存在等等。介入障碍是指从一地迁往另一地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包括两地之间的距离、信息的获取能力等等。个人因素有两方面:一是迁移者个人与家庭的因素,二是指迁移者本身的智力与认知程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首先是要坚持唯物史观,就是坚持用生产力的观点来看待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问题,观察到其中蕴含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亦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规定的经济承载能力,否则就会发生回流现象。可见,人口学人口迁移现象的描述多体现为一种“推-拉”理论的探讨,它总结了可能影响劳动力做出迁移决策的因素,但没有深入探究各方因素及其变化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程度,它只是阐述了迁移的可能性,而缺乏其必然性的分析。
(二)经济学的视角及其批判
经济学主要是从劳动力配置的视角对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分析。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建立了首个人口流动模式,即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型。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两个部门,一个是汇聚大量资本、具有较高劳动生产效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另一个是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5]。由于两个部门在经济收入上存在着差异,会吸引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资本家利润的不断增加,资本家会进一步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发展态势会一直持续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为止。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迈克尔·保罗·托达罗(Michael Paul Todaro)指出农村劳动力是否进入城市是由城乡实际工资收入的差距和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概率所共同决定的。农村劳动力之所以大量涌入城市,是因为他们认为城市收入远高于农村收入[6]。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是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客观现实:首先,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刘易斯模型及其追随者忽略了农业生产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会增强的特点;其次,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也不是无止境的,即使农村劳动力被城市吸纳,也往往只能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缺乏稳定性,受市场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大,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可能被迫回流;最后,也有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期间不断积累专业技术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人脉资源,选择主动回流创业以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收入。
三、社会因素与个体因素:农民工回流的双重约制
(一)农民工回流的社会因素
农民工的回流首先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包括政府的政策效应、城市的融入度、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经济形势的变化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壁垒被打破,广大农民获得了自由进入城市工作的权利和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村户籍居民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里,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差别或潜在的不公平,甚至还有排斥和歧视,这些差别阻碍着农民工实现自己在城市社会中的追求和抱负,而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被归因到户籍制度上[7]。因此,寻求户籍制度的保障来消除差别和改变在城市中的境遇,是农民工的社会理性选择,差别越大,获得城市户籍的欲望越强[8]。严格的户籍制度、严苛的就业制度、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域的歧视都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最终获得城市户籍的巨大障碍,因而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典型的非户籍人口之间的迁移流动。这一特征会对农民工的回流起到推力作用。国家对于三农问题十分关注,从2004年至2015年连续12年颁布了以“三农”为核心的中央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回升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密集出台,产生了缩短在家务农和外出打工的经济收益差距、拉动外出劳动力返乡重新回归土地的局面,地方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的支持,也大大增加了农民工回流的可能性,打破了务农者老龄化的尴尬形势,使农村重新焕发了活力。同时,各地基层政府鼓励兴办企业,积极使农村的创业环境更稳定、更优化,对在外积累了一定财力、人脉又有创业想法的农民工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加之这些农民工对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易于掌握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形成了农民工回流创业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可以保证其较高的成功率和预期的回报。近年来,高素质农民工选择主动回流创业的比例在不断上升[9]。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左右农民工的心理变化,对促使农民工或主动或被动的回流产生重大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经济效益受到重创,就业岗位不断减少,城市容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削弱,农民工外出就业出现了明显的困难性,大量只拥有简单技能的农民工被迫失业,出现了一轮农民工回流的大潮。同样,随着全国范围内招商引资如火如荼的开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少企业由城市转移到乡镇,大大增加了乡镇的就业机会,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加之城市收入高预期的破灭,对外出劳动力主动回流具有显著的影响。
(二)农民工回流的个体因素
农民工回流的个体因素即农民工个人状况和家庭事件因素。农民工个人状况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健康状况、技能等等;家庭事件包括结婚生育、赡养老人、子女上学等等。
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中,年龄的影响十分显著。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回流的数量会不断增多,其原因主要是年龄越大,上有父母要照料、下有子女需要学习生活照顾的压力会更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在不断下降,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不得不选择回流。同时,这也体现了劳动力供求年龄结构的不匹配,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往往更高,中老年人因无法适应产业升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所以最容易产生回流。在以知识经济主导的全球背景之下,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也决定了他们是否回流。缺乏一技之长的低学历农民工在城镇很难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很多农民工干的都是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由于工作环境差、安全措施不到位以及缺乏正规管理等多方面原因,农民工因工伤病的比例不断升高,受制于劳动能力的下降、伤病的折磨,农民工被迫选择回流。相反,受教育年限越长、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希望留在城市,回流意愿相对较弱。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对进城务工的收入预期要高过其他农民,因此他们更愿意放弃土地进城定居。有较高学历或有一门技艺的外出者也很少有回流的想法,而多数处于城市最底层从事工作量最大、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差的体力劳动的农民工会考虑回流。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比重达到41%,周工作超过44小时的高达84.7%。就在这样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之下,与城镇工人相比较还受到“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由于这些工种无需技术含量,所以可替代性很高,农民工还要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农民工工作场所的环境非常恶劣,遭受着粉尘、噪音等污染,还存在着机械故障风险,但给予的保护条件极差,2013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占28.5%,参加医疗保险的仅为17.6%,农民工的职业安全隐患多,人身安全风险大。即便如此,农民工还会面临着被克扣、拖欠工资的风险。这一类处于劣势的农民工很容易催生回流的意愿。此外,囿于城市高额的教育费用,多数外出农民工会有回流意愿,为了使得孩子在有限的家庭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出于陪伴子女的需要,他们也会选择回流。女性农民工较之于男性更容易产生回流意愿,未举家迁移的已婚农民工,特别是已婚女性有着最为强烈的回流意愿。
一般来说,迁移者的流动主要是为了追求比原住地更高的比较经济效益。依此逻辑,农民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越高,越容易实现永久性迁移;而那些收入不高的农民工对自己能否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得到发展相对信心不足,所以他们不敢轻易放弃土地选择永久性迁移。因此,是否选择回流主要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只要在城市打工的比较收益高过农村,他们就会永久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下去。但是,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低又缺乏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会被迫选择回流。基于我国特有的土地政策,土地成为农民工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因而家中耕地面积越多的农民,回流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此种种,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不一而足,总体呈现的是一种在宏观社会背景下出于自身经济状况和现实考量而导致的个体选择。
四、农民工回流产生的影响
(一)城市与乡村的博弈
农民工的回流作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配置的空间转移,对城乡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城市而言,一方面,有助于减缓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因为大量农民工进城导致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人口承载能力超限,给城市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社会治安问题等,因而农民工的回流可以缓解城市容量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民工回流适应了城市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对劳动力素质的需要,城市低水平富余劳动力的退出以及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涌入,进而推动了城市地区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对乡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各种生产要素的回归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引入,为乡村社区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契机,特别是农民工在回流的同时也把资金、技术、管理和新观念带回了乡村。就经济效应而言,农民工带回的资金无论是用来消费还是投资,都有助于缓解农村资本的不足,农民工的回乡创业有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就文化效应来说,农民工在城市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各方面的思想都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他们俨然成为我国乡村文化进化过程中重要的传播者,除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外,回流的农民工更有意愿参与乡村事务的民主化管理,这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革新注入新鲜血液,也起到了加快推进农村民主化管理的作用。
(二)主动回流与被动回流的区隔
主动回流和被动回流的农民工对流出地的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主动回流的农民工多数是在城镇打工期间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技术资本和人脉资本,具备相当的经营管理能力、敏锐的市场洞悉力、有着较为成熟的规划蓝图以及锐意进取的竞争与风险意识。他们怀揣着衣锦还乡的心态,有着强烈的回乡开辟一片属于自己事业的求胜欲。所以,主动回流的农民工在从业上有着明显不同于以往“农民”的职业身份转变。一方面,主动回流的农民工即便回乡从事农业生产,也是属于新型农民的范畴。他们有意专注于蔬果、水产养殖、花卉树木等的规模化经营,并朝着家庭农场的目标发展。他们受益于国家、政府的补贴优惠政策,充分利用当地的职业培训体系,加之通过科技运用和农业机械化普及,全面提高经营效率、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经济效益,积极推动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智力与技术支持,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主动回流的农民工涉足工业和服务业的更多,他们创业的领域也更加多样化,涉及水利水电、服装加工、建筑建材、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等,促进各行业百花齐放,不仅为流入地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为当地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10],实现农村创业引发就业的“多米诺效应”,有利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虽然主动回流的农民工给乡村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然而主动回流者一般都是经济富足者,为了让故里乡亲知道自己在外打拼取得的成功,他们往往盖起了小洋房,开起了小轿车,用起了名牌货。通过各种消费让人注意到自己的行为,以获得他人的羡慕与嫉妒;同时也向人证明自己的支付能力,以获得他人对自身财富、名誉和身份地位的认可。这种炫耀性消费对农村传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产生巨大冲击,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
被动回流的农民工多是由于家庭事件因素或在外工作不顺而回乡[11]。不同于主动回流者,被动回流者在经济收入和从业上均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其一,在经济收入上,这部分回流农民工的心态往往无法摆正,他们非常矛盾:一方面,依旧希望外出打工、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现实的状况羁绊住他们外出的脚步或是他们在城市获得的经济收益有限,使其不得不返回原住地。他们的回归会直接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外出劳动力向留守亲人的汇款金额下降。而且,回流后的他们会倍感迷茫,不愿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而高收入的工作又无法胜任,长此以往,他们会沦落为无业农民,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治安的稳定。其二,在从业上,被动回流者一般是城市打拼的失败者,回流后他们大多是从事农业生产或原来的工作。然而对于家庭来说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减轻留守老人的耕作压力,另一方面使得留守儿童可以得到较为完整的家庭教育。
五、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我国农民工回流的应对策略
基于农民工回流问题影响因素的分析,农民工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做一种“候鸟式”的流动,主要是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基于自身经济状况和现实的考量的个体选择和制度后果。虽然稳步积累农民工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获得城市地区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增加农民工获得非农工作的机会和非农工作的稳定性,然而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市产业结构的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社会新常态的特殊发展阶段,农民工的回流有利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城市社区的和谐稳定的健康发展。但对于广大乡村地区发展和乡村社会的稳定确是一项新的命题。城市富余劳动力的回流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新的契机。从政府层面出发,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拓宽政策信息传播渠道,发挥中间桥梁的作用,为群众完整呈现各行业信息表;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职工的教育、职业技术和创业培训体系,提高群众的职业能力。从企业出发,可以注重改善企业的工作环境、住宿环境和休闲娱乐环境,而外出农民工自身也应摆正心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理智看待回流抉择。
第一,政府层面可以拓宽信息传播渠道,确保政策传达链条畅通。一方面,政府应发挥中间桥梁作用,整合企业招聘信息,为本地群众整合全面的应聘信息,积极建立农村劳动力供求信息平台,充分利用外出农民工回乡的集中时间段举办大型的人员招聘会。针对企业急缺型人才,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人才回流机制、人才引进政策,努力为企业面临的人才短缺现象做出回应。另一方面,转变职能,提升服务理念,不断拓宽信息的传播渠道,利用政府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向在外农民工推送信息,确保信息链终端的群众都能接收到。有条件的村委会将各类最新的政策法规、资讯信息全天候地实时在LED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放。在召开村委会会议、村民会议时,着重宣传最新政策动态,用尽可能多的渠道让群众知晓与其息息相关的惠农政策和创业扶持政策。
第二,加强对回流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回流农民工一般受教育程度偏低,而且技能水平不高。所以,加强对回流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对实现他们的再就业就显得特别关键。政府部门要及时掌握农民工返乡动态,组织并制定各种短期、中期、长期培训计划;推动企业和农民工积极投入到农民工技术培训当中;根据返乡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和企业用工需求的变化,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培训。特别是围绕县域经济下的特色产业,开展系统培训,帮助返乡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
第三,改善企业的工作环境、住宿环境和休闲娱乐环境。大都市具有生活方式现代化、工资待遇高、生活娱乐设施健全、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等特点。所以,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觉得回到家乡就不适应了,进而降低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这个角度看,除了薪资之外,乡镇企业工作环境、住宿环境和休闲娱乐环境的改善和提高对解决农民工回流问题不啻为一个重要方面[12]。特别是对很多年轻的农民工来说,农村的生活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他们与农村的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都越来越远。面对这种现状,需要加强农民工群体的价值观教育,远离盲目从众、远离虚荣攀比,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理智看待家乡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相较于大城市的现代化,小城镇呈现的是温馨——生活工作在家乡,可以常伴家人左右,生活环境亲切熟悉,幸福指数高。
六、结 语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考察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就是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系统辩证地看待现实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个体化并不像西欧那样借助于市场力量,而是首先通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度安排的推动,例如城市的单位制度、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导致个体脱离了家庭、家族和地方社区,并且能够以国家公民的身份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中去。在从农民身份向城市居民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太多的阻碍因素,割舍不了的乡土情结、如影随形的偏见与歧视等等,太多的内外因素交织促使农民工做出回流的选择。所以,在社会个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回流亦是农民工自主性的一种体现。虽然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区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但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以及农民工对现实的考量才是回流产生的根本原因。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是要结合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工业化水平决定了农民工“亦城亦乡”的两栖生活状态。然而,无论是主动回流,还是被动回流,农民工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城市文明的熏陶与感化。农民工回流对农村地区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如何将这种能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智力,需要制度扶持和政策引导,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民工的主体性作用,进而推动乡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96.
[2]郝欢.恩格斯社会发展合力论的理论价值[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3-16.
[3]李红梅.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考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J].求索,2013(8):241-243.
[4]RAVENSTEIN E. The Birth of the People and the Laws of Migration[J].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1876(3):173-233.
[5]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0.
[6]蔡禾,王进.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6):86-113.
[7]吴如彬.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18.
[8]张辉金,萧洪恩.农民工回流现象的深层思考[J].农村经济,2006(8):102-104.
[9]张桂蓉.人口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129.
[10] 蔡宜旦.助推“返乡创业潮”的政策思考——浙江省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调查研究[J].青年探索,2010(4):59-64.
[11] 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1(4):64-76.
[12] 马良,黄益飞.居住模式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 6.
(编辑:蔡秀娟)
DOI:10.3969/j.issn.1673- 8268.2016.04.002
*收稿日期:2015- 08- 07修回日期:2015- 09-23
作者简介:王伯承(1988-),男,河南商城人,编辑,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应用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8268(2016)04- 0007- 07
The Problem of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Viewed by Marxist Methodology
WANG Bocheng, NI Jiahao
(SchoolofSocialandPublicAdministration,East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200237,China)
Abstract:Using Marx’s methodology to investigate population mobility is to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observe real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tool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migrant workers’ flowing back. Demographic studies focus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while economic studies in labor force allocation perspective, but there are obvious limitations. Age,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status, gender, health status, skills and family events are intrinsic causes for the returning of migrant workers, while the obstacles to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government’s policy effect, urban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conditions, wage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are external social cause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flowing back.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from the two kinds of causes intertwined. Migrant workers’ flowing back is a kind of embodiment of autonom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Despit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is a symptom of the binary regional segment to a large extent caused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consideration of reality in the cit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special stage is the root cause why migrant workers have chosen to return. The effect of active and passive return to rural community is different. How to transform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energy into power and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needs supporting system and policy guide.
Keywords:migrant workers’ flowing back; individual choic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