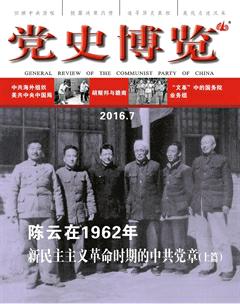陈云在1962年
孙京
1962年,对于陈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之前四年,由于与毛泽东存在一些认识分歧,他不断受到批评。1962年上半年,陈云在国民经济调整恢复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四年,他一直养病闲居,直到“文革”爆发。
矛盾心态: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表现令人琢磨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7118人出席会议,此会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参加者包括中央、中央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干部参加的人数和层级,均为党史上首次。这是在国民经济最紧迫、最关键时期召开的会议,对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会期间没有讲话的唯一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196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7人。除了陈云,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都在大会或小组讨论会上发了言。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刘少奇代表中央做报告。周恩来、朱德分别在福建组、山东组的讨论会上发言。林彪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方针。邓小平在大会上讲了党的建设等问题。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是唯一一位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显著地位人所共知,“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内理财的能手,是建国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新中国成立伊始,陈云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领导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稳定物价以及制定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称之为“能”“多谋善断”。1957年后,虽然陈云受到了批评,但毛泽东始终十分重视陈云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意见。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7月11日晚,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称赞陈云:“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当总指挥好。”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更是毫不掩饰他对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欣赏。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
基于此,毛泽东特意想请陈云讲话,但被陈云婉拒了。毛泽东说: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
为什么陈云没有在大会上讲话?学者迟爱萍认为,一是不说违心话、顾全大局、维护中央的团结和权威,是陈云一贯的作风,也是他突出的政治品格;二是大家思想认识还不完全统一,还处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通气、出怨气的阶段;三是大家还处在统一认识的过程中,作风向来沉稳的陈云,选择不讲话是明智的。学者张素华则认为陈云不讲话的原因是:一是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二是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三是心有余悸。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更能说清楚,陈云曾在1988年5月21日的一次谈话中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大会之后做了重要讲话的最高经济工作负责人
实际上,陈云在会前做了十分详实的调查研究。自1960年9月至七千人大会前,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陈云进行了5次调研,累计时间近1年,足迹遍布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京等8个省、市,涉及农业、化肥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等多个领域,调研对象覆盖省、专区、县、生产大队等不同层次,为了掌握真实情况,他特别到自己熟悉的家乡、早期搞工运的青浦调查。
陈云也没有等到半年后讲话,而是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就讲话了。
1962年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
2月8日上午,陈云出席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这次,他讲了话,没有谈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就采取什么方法获取比较正确的认识谈了意见,题目是《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他谈的“交换、比较、反复”思想方法正是自己一生始终遵循的信条。他高度肯定七千人大会,认为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陈云认为本次大会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认为这是共产党无敌于天下最关键的一条。
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多次发言。在讨论中,陈云就财政平衡、市场平衡、工农业恢复速度、精减职工、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等问题谈了意见。这些意见不仅全面,而且操作性强,尤其是各种数字非常具体。比如减少行政管理费、文教等事业费5亿元;国家给农民开的退赔期票7亿元,推迟3年归还;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等等。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做任何讲话,但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在上午、下午两个会上,他都做了重要讲话。一前一后的鲜明对比,表明了陈云当时的矛盾心态。这表明,陈云不是无话可讲,而是在选择讲话的时机和范围。“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他深知自己讲话的分量,因此选择了在大家意见相对比较统一、范围较小的场合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体现了陈云一贯的坚强党性。
2月8日的讲话,表明陈云认为党内的政治生活空气已经发生了明显改观,可以做到畅所欲言了。
开怀畅谈:从西楼会议到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由于七千人大会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会议对财政经济方面困难的估计仍不够充分。会后,“陈云对财政经济工作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受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高度重视”。这个会后的一系列主张,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指的是2月8日的重要讲话。
西楼会议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史称“西楼会议”。毛泽东因在外地视察没有出席,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西楼会议发现了一些在七千人大会时没有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使中央认识到必须下更大的决心来进行调整。
2月23日,刘少奇让陈云发言。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做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其实,自1957年以来,中共中央在经济工作中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对形势如何判断和估计上,一切随之而来的措施、争论乃至党内斗争也都源于此。陈云从农业减产、通货膨胀、钞票向农村转移、投机倒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方面谈了经济困难的表现。针对困难,陈云提出了6条措施:把1963年至1972年的10年经济规划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继续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陈云直率地说明时局的困难,充分显示了陈云不和稀泥、讲真话的风骨。
“陈云的讲话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很大震动。”刘少奇也因此改变了对形势的判断,认为当时处于非常时期。为了使陈云的讲话在中央决策部门广为人知,刘少奇建议陈云到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讲他的认识。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提议国务院全体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
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全体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他一共讲了5点困难,但认为农业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是基本原因,其他困难(通货膨胀、投机倒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是从这两点派生出来的。如何克服困难、采取的办法,还是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6点框架,但内容大大丰富、具体、深入了。比如,十年规划中恢复要5年;把减少城市人口作为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对制止通货膨胀、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和农业增产都提出了具体办法;认为计划机关的注意力要放在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陈云在报告中还特别强调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陈云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薄一波回忆,“特别是陈云同志的报告,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赞扬”。
毛泽东也同意陈云的讲话。3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出,“中央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讲话要在省一级传达、讨论,并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立即行动起来。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次,各省级负责人对形势的判断迅速统一到了陈云的讲话上来,而且纷纷要求扩大传达范围。4月26日,中央决定将陈云等讲话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陈云的讲话,经中央批发,成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各地产生重大影响。
中央财经小组会议
在西楼会议重新评估形势的同时,在组织机构方面,中央决定恢复财经小组。刘少奇、周恩来一致主张由陈云担任组长,但陈云一再推让。后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同意由陈云任组长。毛泽东也同意这项提议。1962年4月19日,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中央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由陈云担任,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成员。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具有了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但对比这个机构与前两个机构的人员组成,会发现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规格更高了。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员分别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员是陈云、薄一波、马寅初、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邓子恢、邓小平、李维汉、李先念等。新成立的小组两名副组长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而且周恩来也第一次成了小组的成员。不仅如此,机构还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这个机构随之成为了当时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主张对1962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陈云讲了7个方面的问题,继续重申、丰富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同时着重讲了1962年年度计划调整和综合平衡问题。他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最关键的是实行综合平衡原则。怎样实行综合平衡原则,根据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解决从什么时候开始搞和从长线还是短线开始搞两个问题。他指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
薛暮桥认为这个讲话和2月26日在国务院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对“纠正‘大跃进以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使我国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会议,陈云是在心脏病复发、医生要他长期休养的情况下抱病参加的。会后,他就到南方疗养了。
编辑印发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
陈云去南方疗养了,但国民经济的调整一直按照陈云的经济思想进行着。一向善于从理论高度思考问题的刘少奇认为,不仅这两次讲话,而且这几年陈云的多次讲话和文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人了解。陈云几次三番坚决反对。但刘少奇站在国家大局的高度,尽力说服他,并说“只是印发中央少数同志、中央财经小组的同志看,做参考”。刘少奇秘书邓力群等根据指示编辑了《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一书,摘录了陈云1956年1月25日至1961年8月8日间的讲话及文章共15篇,基本上反映了这些年陈云指导经济工作、解决经济建设与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与急迫问题的思想。
默默不语:建言支持包产到户遭到冷遇
在南方疗养期间,生病的陈云时刻在关注着国家的经济发展。
向毛泽东建言包产到户
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各部门困难最严重的领域。陈云一直在思考破解农业困难的办法。他看到安徽在农业方面搞责任制的材料后,非常重视。他说,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陈云对包产到户重视并非心血来潮。1961年6月,他通过调研就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份报告。从题目可以看出,这些主张已经比较接近包产到户的主张。
在经过充分了解之后,1962年6月,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分别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基本一致。陈云决定向毛泽东进言。
此时向毛泽东进言谈此事,无疑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已经从允许试验到不能容忍。1961年3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实行责任田的情况,毛泽东说可以试验。7月,曾希圣再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可以扩大,多搞一点。1961年12月,毛泽东曾以商量的口气询问曾希圣,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去。曾希圣表示还要搞下去,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毛泽东的询问,本身就表明他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并被撤了职。4月,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情况,提到了当地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办法,暂时渡过难关。将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的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明确表态。
尽管有别人规劝,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陈云向毛泽东进言的决心。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希望与他谈谈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于当天下午1时收到来信。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对此事发表意见了。“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到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同志,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默默不语。”
受到严厉批判
7月中旬,陈云离京赴北戴河疗养,并准备参加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但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让陈云改变了看法。7月25日,毛泽东将《波兰农业社会化》一文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阅看。接着,陈云又收到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综合种种迹象,陈云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7月28日,陈云致信中央,表达自己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同时希望请假养病,不参加北戴河会议,之后又请假不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北戴河会议,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将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等问题。所谓“黑暗风”,就是指西楼会议至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经济形势严重困难的估计,包括陈云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的应对之策;“单干风”,就是指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对一些农村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做法的支持。会议批判的“三风”中的“两风”都指向陈云。对于陈云没有被点名批评,毛泽东在会后说:“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北戴河会议后,实际上停止了陈云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直到1966年。这四年间,他虽然仍是中央副主席,但一直养病闲居,没有参与中央最高层决策和活动。这一期间,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听评弹”。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虽然几次在不同的会议上,肯定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但毛泽东肯定的主要是在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中,陈云对压低计划指标的贡献,对陈云1962年的经济工作尤其是包产到户建议几乎未做评论。
自此之后,陈云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陈云也成为了唯一一个在“文革”前就不再参与中央决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文选》第3卷可以反映出陈云的政治“轨迹”,从1962年3月7日到1973年6月7日,没有一篇文章。
陈云不再参与最高决策,但中央在实际工作中一直贯彻着他的思想。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功,陈云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