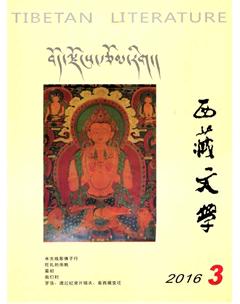我们村(外一篇)
官晓丽
玛岗村位于白朗县西南约80公里处。去过的同志都说那里海拔高,路不好,但同时又安慰说那里是个小气候,夏天很美,山坡上可以采蘑菇,还可以到小河沟里去捉鱼。带着点儿对那个“遥远”村落的想像,极力打消各种拖后腿的想法,打上背包坐上车就这样上路了。
路上路过羊湖。羊湖还是那样安静美丽,逶迤的山峦环抱着瓦蓝瓦蓝的湖面。湖边的观景台上依然站着不少外地来的游客,他们对着羊湖各种看各种照各种赞美。可是我怎样也打不起精神来欣赏这美丽的景致,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一个影像:在离天很近的地方,有一个荒凉的村落,它的名字叫:玛岗。
终于过了白朗县,走上了风尘漫天的土路。驾驶员以前去过玛岗村,可是岔路太多,已经不大记得该怎样走了。在和村里等着我们的老队员联系上以后,算是找对了路,一阵功夫就把车开到了楚松水库前。对了,我们正是夏天去的,路两旁田野里青稞已经抽穗,眼看油菜也要开花了。大家在车里有说有笑,感情是去玩的吧?只有我沉默着,像一个异类,像一个患了恐惧症的人被自己的想像纠缠着回不到现实。现实怎样呢?那段时间正是心情极其灰暗的时候,天空怎样蓝,在我心里也是灰的。据说断臂疗法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治疗办法,这和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差不多,反正一刀下去就出来结果——不死即活着。我是去断臂的。所以看见羊湖时,有什么可乐的呢;看见四野的绿意时,有什么可乐的呢。我悄悄用餐巾纸擦干一串串泪水,心里唱着自己的歌。
到村里时已近黄昏。人们已经盛装等待了我们好久。切玛被美丽的姑娘端着,青稞酒也送到了手里,“不喝成吗?”我傻乎乎地问。怎么可能呢,到了日喀则到了村里怎么能不喝酒呢,有人用藏话说,有人便翻译给我听。然后我二话不说仰头就喝了一碗。酒、哈达,哈达、酒,两样让人应接不暇的东西。我周旋在人堆里,有些找不着北。老队员上车后准备离去了,老队长拉着我的手说,“看你这么小的个儿,驻村真的是……”我听出了话里的话以及她真挚的同情。人哭的时候是不好看的,喝了酒也不会太好看,但那时到了高海拔的玛岗村,心里已经想不到这些了。我吸吸鼻子,紧紧拉着对方的手说,“放心去吧,你们能行,我也能行。”我不是易水河边的壮士,虽然我不断腕只断臂。
车子开出村委,不愿再出门相送,心里空成一片。也许是以前塞进心里的东西太多,一下子清空后还适应不了,像一个空心稻草人。村委里热闹极了,乡书记带着一班年轻人,村两委全体成员和村民代表,坐满了偌大一个活动室。平时人们总说我文静,内心里我也按照读书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偶尔颠覆一下常规又何妨。坐在玛岗村村委活动室里,我大着嗓门和第一次见面的乡书记聊起来。我拉着他的手臂,像认识了许久的哥们儿,“书记,我不懂藏语,情况也不熟悉。到了这里,工作和生活都得靠你和乡亲们多照应了!”书记自然没有推辞地答应了。在闹轰轰的环境里,人容易忘掉自我,我就需要这样。我四处打量,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天地了。村民代表们可能也在打量我,一个弱小的汉族女人。我不在乎,起身来和他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样过了不到半小时,就把自己重重地摔倒在了小床上。合衣躺在那里,那个陌生的乱糟糟硬邦邦的小床上,一动不敢动,动一下就天旋地转。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点。我清楚地知道,我是驻村干部,我已经开始了我在玛岗村的驻村生活。
村里派来一个叫巴普的年轻姑娘,帮助我们烧茶煮饭。这姑娘一脸晒斑,身板倒结实,一看就是个勤劳能干的人。第一天来,她有些腼腆,见了我只会怯怯地笑。她会捻羊毛线,线锤在她手里飞快地旋转。我让她教教我,可是笨得很,总是把线捻断,只能逗她大笑。笑过以后,她渐渐不怎么怯我了。我们一起喝酥油茶吃早饭,一起晒太阳洗菜做午饭。我不会藏话,她不会汉话,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沟通的。队员告诉她,“这是官队,你可以叫她官姐。”她羞答答地觉得别扭,喊不口出。有一晚我在房间里看书,她做好面疙瘩从厨房端过来,“官姐,吃饭啦!”她终于说。我绽开一脸笑,吃得很开心。
玛岗村是个极小的村子,全村不到六十户人家,有时散步就可以把整个村子全走到。初来乍到,总得给大家报个到吧。我和队员商量,去各家走走看看吧。我们带上笔记本就去了,听他们聊家常倒也有趣。有的家有两个女主人,有的家又有两个男主人,我一头雾水,搞不清状况,又不便追问。有的人家屋子里宽大亮敞,有的就要窄小陈旧得多。村民见我们把倒上的茶都喝了个干净,知道我们不见外,待我们也就没有初来时那么拘谨小心了。偶尔有点事,他们也愿来村委走动走动。我们到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村委协调农用灌溉水渠的修复。后来日子稍长我就知道,驻村干部的主要任务和城里的街道办事处差不多,太大的事干不了,能够把些家长里短的事处理好,也算尽到责任了。
和村民们混熟后,我躺在床上看书,他们在外屋玻璃暧棚下聊天,我们彼此不相干,各得其乐。村民走了,两个藏族队员告诉我,村里不少家庭都是儿子几个娶一个媳妇回家。我听了大为吃惊,认为不可想象。“他们不会争风吃醋打起来么?”我直率地问。“你这是城里人的头脑,人家乡下人都想得简单,只要家里劳动力充足,把生活过好,都不会有意见。”队员说。我的聪明脑袋已经变笨,想不起来该往下说点什么。事实是,有一天我在村里遇到一个患了小儿麻痹症的男子,三十好几了,衣帽穿戴得干净整洁。待他走远了,队员告诉我说他们兄弟四个合娶了一个媳妇,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哥儿几个也很和睦,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算是村里的模范家庭。老实说,我以为巴黎红磨坊的裸舞表演就已经够让人开眼界了。我还有一资深闺蜜,为了爱情不死,至今不结婚只恋爱。当然,说得远一点,李银河女士还专门研究过同性恋。前次德国外长访华,连他的男朋友一起带来中国,让人亮瞎了眼。话说我们的玛岗村,它也有特别的风情,这一点我呆得越久就越清楚,同时也越困惑。这偏远贫穷的小村,没什么可资发财的资源,大家都过得紧巴巴的,村委的门从来不上锁,可我们没丢过一件东西。有一阵子我包里放了几万元做培训的经费,成天担心会丢。可是包扔在床上那么多天,村委里人来人往,直到培训结束也没丢过一分钱。城里四个男人养一个女人,恐怕早就打破头了,可这里没人为这种事出头,顶多过不开心了另起炉灶单过。在城里时,我常对着一面大衣柜不知该穿什么出门。可是看看巴普,她有什么穿什么,逮什么吃什么,天天没心没肺快乐地活着。我想问问她,你知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吗,你知道香奈尔和路易威登吗?想想还是算了,城里人矫情到这个份上,实在可怕。我不想说城里人比乡下人更懂生活,也不认为城里人一定比乡下人过得快活。我只知道城里的规则在这里全行不通。
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我渐渐开始由外而内地乡土化了。远在北京的妞妞说,“妈妈,你在乡下返璞归真了吧?”我答,“当然,我早已返璞归真,从内到外充满了乡土气息。”连村里的狗,也成了我的朋友。没有什么是改不了忘不掉的,除了自己不想改不想忘。
我常一个人散步,喜欢安静,喜欢这自在天地,任我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四处随意乱走。我沿着河边走,一忽儿在河左岸,一忽儿又跳到河右岸。那能叫河吗?充其量是一条小河沟,在村委对面山脚下布满砾石的空旷河道里,不足两米宽的河面闪着鳞鳞波光清清浅浅蜿蜒着淌向远方。他们不是说河里有很多鱼可以捉的吗,我倒是在这河里见过鱼,一条两条,小得可怜,怎么下手去捉。河流是时间的故事,以前我就这么写过。它在带走一些东西的同时,又会带来另一些东西。这是永恒的规律。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所喜爱的王小波先生还说过,“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因此,每一种生活经历都可看成是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处于果壳中的宇宙,一切都显得无可抗拒。你选择了,就要承受;而不选择也即是选择,谁也无法逃避,除非用死亡来终结时间。“只活一次,等于未曾活过”,这话谁说的?我想不起来,但觉这话太残忍。在夕阳璀璨的光芒里,难道我未曾活过吗?
玛岗从我生活中的一个可能性慢慢变成了必然性。习惯了从村委院子的厕所后窗去看那一片油绿的麦田,习惯了夜晚山峦上的星空如此静穆深沉,习惯了村民走过村委时进来打招呼的那一口日喀则方言。
玛岗海拔高,慢性缺氧使我吃下了大把的丹参滴丸,喝下了几大包红景天,把以前驻村工作队留下的两小瓶旅游用氧也吸光了。我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的体能再决定每天的活动量。一早一晚风奇大,有时得憋着等风小了再上厕所。到高海拔地区驻过村的人都知道,上厕所风太大是什么概念——扔下去的手纸会飘上来贴着屁股,这只是其一。上厕所变得多好玩呀,像打仗,得瞅准战机。再说说水的问题。我们喝的水是从山上淌下来的地表水,经常有泥沙杂质等沉淀物,有一次还从水里发现了一条小鱼儿。有一天村支书多吉兴冲冲来村委说,趁着夏天天气好,干脆把全村的饮水渠再修修吧。我们早有这样的想法,用水问题解决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于是第二天就随他一起去山上找水源。水源在半山腰海拔接近五千米的地方找到了,是从山里涌出的一个泉眼,水质清澈透亮。多吉说,这泉眼冬天不结冰,夏天水又清凉干净。他对这村子太熟悉了,村前村后一草一木他都了解。我们当即同意把这个泉眼作为饮水水源,开挖水渠,埋设水管。村里来了一队人马,用了整天时间,算是把这件事办了。那天下午天气陡然变化,一阵狂风呼啸而来,天上风卷残云,眼看要下雨了。队里驾驶员的那把大伞被狂风吹下了山,我们两个女队员也提前撤离了劳动场地,被狂乱的山风一口气“刮”回到村委。玛岗村果然是个小气候,天气变幻无常,遇到打雷下雨天经常停电,停了电我就和同住一屋的女队员胡吹海侃地神聊,她讲的鬼故事一次也没吓住我。
在村里呆得久了,遇上和外人谈村里的事,动不动就来个“我们村”,“我们村”变成了口头禅。我在我们村里的时间其实前后也就几个月,但感觉上仿佛天长地久。记得初来时,村前一片青稞地。我戴着遮阳帽和无缝头巾,像个外地游客一样成天游荡在那片地里。除了看书,忍不住就想去检阅门前这一亩三分地。走近了看,农田里有青稞,还有油菜和饲草。到了七月,油菜花渐次全部开放。放眼看去,一片一片蛾黄铺展在天下。我躺倒在田边的青草地里,眼望着蓝天,嗅着这芬芳的空气,身心都醉了。我盼着整个夏天都这样,有油菜花,有草场上各种颜色的细碎的野花,喜鹊飞来喳喳叫,戴胜鸟在路边草丛里找食吃,秋天不要来,冬天更不要来。这是多么孩子气的想法。到了九月底,庄稼就由绿转黄,要成熟了。我也忘了夏天时的想法,和队员商量去参加村民的秋收。秋收一定是一件好玩的事,就像小时候在地区,去收割完的农田里拾麦穗,捉蚱蜢。队里的驾驶员说,“你们两个这么瘦小,去割青稞行吗?”我们俩异口同声回答说,“行!当然行!”然后我们就穿上劳动服去地里了。太阳老大,青稞金黄,如果梵高能画下这一切就好了,我劳动到极累时开始幻想。弯腰,曲膝,一手捉住青稞杆一手挥镰刀,这简单的动作无限重复下去,我快晕倒在地里了。脸上烧灼得厉害,汗水沿着脸颊往下滴。我眨巴着眼睛看世界,整个世界都变得金灿灿的。女队员动情地说,“原来秋收这么累,老百姓真是不容易,我以后再也不浪费一颗粮食了。”是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料料皆辛苦。”我们的老先人早就教我们爱惜民力物力,珍惜一切当珍惜的东西。
我的两只手臂完好。驻村结束走的那天,我还用这双手臂接住了青稞酒,接住了洁白的哈达。也许我是忘了断臂这个任务,这要怪玛岗村,它在海拔接近四千五百米的地方,以一种审视和爱悦的姿态看着我,我一激动就忘了。离开玛岗村以后,时常会想起它来。我在梦里也遇见过它,它是清冷的晨风,是小房子里升起的牛粪炉子中的火苗,是我孤独失意时远方来的一个问候电话。我喜欢小李飞刀艺术化的生活,但我情知自己生活在现实中,一步不能离开。
色麦村的春天
听人们说,色麦村是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它离拉萨不远,往返一天时间足够。才从林芝回来,藏南温柔乡里那满眼淡红粉白的芳菲还萦留在脑际,我想不出色麦村的桃花会是怎样的。
周日约了闺蜜一共三人,预备去色麦村。娟说,那儿的桃花好看,还有细软的沙滩。我问,那路怎样走?她沉思半晌曰,“反正是往日喀则那个方向走。”我有点傻眼了。车是借来的,我的车技也菜得不敢恭维。只有莎莎信心满满,“有导航啊!”她说。
在导航的指引下,我们半路从机场快速通道下来上了318国道。走出去不到一里路,就发现318国道正在改扩建,原来的水泥路面全部被挖掉,变成了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心里开始犯嘀咕,不知道这路挖到了什么地方,会不会一直这样烂到终点?导航搜索显示,色麦村隶属曲水县,虽然此去只有六十多公里,可是轿车底盘很低,越过坑洼时一不小心就会被挂住。窗外路边成行的树都绿了,是那种浅浅的“草色遥看近却无”一般的绿,鹅黄的绿,正在萌芽酝酿的让人心疼的绿。娟很文静,坐在后面只一心欣赏这春天媚人的阳光与绿树。我听得车底“哐、哐”的声响,着实坐不住了,让莎莎下来我来开。我是个有一点点温柔的小女子,在这种往来车辆不多的土路上不需要多么高的车技,只需要小心慢行就可以了。
车自然是很颠簸,却也禁不住双手被解放的莎莎在车里发疯。她东戳戳西戳戳从仪表盘上找到播放器,把音乐开得老大。听了不大一会儿,又觉得碟片不好听,自己开了手机上的酷狗来让大家一起欣赏她喜欢的音乐。有大货车从旁经过,卷起漫天尘土。莎莎照了图片,发到往常我们常聚众聊天的群里。“我们去看桃花咯!”她图文并茂地在群里聊起来。酷爱写诗的超哥神回复,“没见花,只见天路通云霞。”这话十分传神,说明诗人真有两把刷子。把着方向盘,我耳朵里只听见两个女人在车里的笑声、闹声。
过了曲水县,终于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一道笔直的油路,伸展在青蓝的天底下。天边有两座耸立的高山越逼越近,仿佛两个威猛的战将,守护着这路,路旁的村寨,村寨里的人们。我只关心桃花,一路上不下十次只问娟一个问题,“还有多远?桃花在哪里?”娟也每一次有问必答,“快了快了,就在路边,放心吧你一眼就能看到。”
放眼四望,麦田枯黄而寂静,四围群山亦萧瑟,只有我们的心是不安分的。我想起龙应台在散文集《目送》中描写拉丁舞的那一段,非常撩人的一段文字,却是那么贴切。春色只是撩人,因为一切看似死去的又都悄然复苏,所有生命都处在一种厚积薄发的状态,它只是等待一个被触发的信号,然后就来个生命大爆发——也许是一场久旱的雨,也许是地球公转时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一点点与太阳夹角的变换。连张爱玲也说,在暧洋洋的春天里,一切生命都这样容易浸淫滋生,所以街上多了许多大肚子的孕妇(这让我发笑,但我也承认作家说得没错)。
路好了,我倒觉得自己的心神不够用了。路上的车子都开得“嗖嗖”的,让人心惊。我还要留意路边的标识,以免错过了“桃花村凉粉店”。听到娟的这个切中要害的介绍,我不相信身心健康的人不会嘴馋想吃。反正我是饿了,桃花当然要看,可是先来两碗藏式凉粉吧。这是符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人处在饥荒困顿中,多么好的风景也会看不见。我要的是“perfect”,身心健康地去做一切不问“意义”的事情。言归正传,话说那个令人心向往之的“桃花村凉粉店”就在路的左边,可是店前停满了车,我一脚踩住刹车,车便斜停在路正中。莎莎急得眼都绿了,“姐,你干嘛把车停在路中间?”“那我停哪儿?”我也着急。“姐,快倒,把车倒到后面的路边,不然那辆车要撞上你!”她指着店前一辆正在往外倒的车说。我一下慌起来,把车往前开了几米停住,“快,莎莎你来倒!”我命令。
女人们就这么无事忙,而尤其女司机忙起来让人害怕。车子在莎莎的鼓捣下,终算是停妥当了。店子是那种黑黢黢的在拉萨常见的藏餐馆的式样,门前搭着藏式布帘。在掀开帘子进去之前,我看见村子下边就是江水涛涛的雅鲁藏布江,在这江的拐角处的冲积扇面上,稀疏地散落着村民的民居,掩映在田间的桃红柳绿中。
当我们填饱肚子出来时,起风了。原来湛蓝的天,飘来大片大片云絮。路边几株上了年纪的老桃树虬根错节,满树繁花只剩得星星点点碎花,茂盛的枝叶在风里摇曳,仿佛奏响的春的尾声。诗里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我不信这偏僻山村的桃花就这样开完了结了。
娟以前来过色麦村,她义不容辞地在前面带路。我们沿凉粉店侧面的小路往山坡下的江边方向去,可今年不同去年,老远就看见隔着一道山涧对面山坡上已经拉上了绿色的围栏。大概这里桃花的名声已不胫而走,每年开春来赏桃花的人日渐多起来,因这半壁桃花都在江边山坡上,为着安全,就围上了围栏。
我们伸伸舌头,从半坡里爬回到马路上,不再作探险越过山涧去对面看桃花之想,沿着马路旁边敞开的铁栅门进入桃林才是正道。带针刺的灌木丛挤占了人们迈向桃林的道路。山风掠过耳畔,吹乱了头发。怔在枯黄的足有半人高的蒿草丛中,看这片汪洋恣肆的老树发着新花,颜色深浅不一地铺陈在只听得见风声的广袤的寂静里。仰头看看,天空亘古未变。一条浅碧的江水从灰黄的山下横过视野。成团的粉色,娇柔地漫过心头。这是色麦村的春天,无论怎样的天风地寒,都不曾阻挡它来临的脚步。
每个人都惊叫着躲避路上的针刺灌木丛,几乎是跳着脚一路走过去的。莎莎闪身跳下一道土坎时差点摔倒,屁股被针刺扎到,疼得哇哇大叫,一路走一路揉,几乎要脱下裤子来察看伤情擦药水了。她着恼地说,“我要痛死了,你们还拿我开玩笑!”我和娟于是又大笑不止。
这片带着古意的野生桃林没规没矩地占领了一整面坡地,既不成行成排,姿态高矮也不一样,我想想,送它两个字——“任性”:你要这般统领一切地萧瑟肃杀深沉,我偏要兀自漫天卷地温柔地自开自谢;花自飘零水自流,我不叹息流年易逝,只需要按自然的意图走完这趟万物逆旅的时光就够了。“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而且我知道我要的不多。”坐在花枝下的石头上想着有人评价古龙小说时说的这句话,我看看花,花也看看我,我懂得了花的好处,但不需要它懂得我有什么好处。它只是色麦村春天的一个症候,等我在季节里与它相逢。我颓废消沉了很长时间,像脑死亡一样写不出一句诗一篇散文,所有的春夏秋冬都不能让我感动。有时候坐车出远门,嗅到了空气里的某种味道,就努力地回想,像一个迷路的人想找到回家的路那样想找到往日那种没来由的欢欣。可那种感受很难再找到了,它似乎被某种奇怪又可怕的力量彻底击碎毁灭了。这让我绝望。我有时候想哭,可是哭不出来。走到色麦村来看春天,是一种需要,也是一次不经意的安排。
对于怎样形容花,怎样形容桃花,我是又拙又笨,诗人和才子写得太多,我就不要班门弄斧献丑了。在弥漫着枯草与灌木的这一片山坡上,我们想方设法摆出各种造型来与那一簇簇花团共舞。莎莎不知疲倦,“娟姐,你说的沙滩在哪呀?”她在桃林里跳来跳去地玩,心里却还惦记着沙滩,一个玩不够的大孩子。
桃林下面就是雅江了。我们伸长脖子向下看去,江边上怪石嶙峋,颇为壮观好看。对面山势很陡,谷底江面通常不会太宽,因是枯水期,江水多由雪水融汇而成,清澈透亮。这时节的江水借得春天三分绿、偷来天空一抹蓝,又改了汛期那种勇猛咆哮的姿态,变得安静柔顺不少。连滚带爬下到沟底,走得越近,越觉得江滩上那一片石头雄奇伟岸,布列得很有阵势。这里没有赤壁和战舰供人慨叹周瑜的遗憾与卧龙的踌躇满志,也没有腾王阁借我们登高远望想像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美妙,所以我不能发思古之幽情。我只能说,青藏高原这片隆起于地球的第三极,它极目蓝天的姿态是那样纯净、无畏、美丽。在时空流转中,我们有缘得见交汇,实是三生有幸。我趴在江边一处巨大的怪石上,望着一江春水开始胡思乱想。娟脱了鞋子,赤脚在石头上走来走去,用心体会着什么。看见我发神,又大喊让我小心不要掉到江里了,她不会水,救不了我。
江边上的风快把头发都吹掉了。这里除了峥嵘的大石头哪有什么沙滩!在石缝中,偶尔出现一小片较平整的石头拦截堆砌下来的沙,果真很细软,脚踩在上面一定很舒服!娟来回踩着,口中念念有词,“你们问哪有沙滩,这不就是沙滩吗!”她的一派天真,与这里千年万载被水流冲刷得奇形怪状的石头很是相称,反正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和这石头一样,是老天造化的产物,自己是从来不刻意有所雕凿矫饰的。为着她是这样的人,我和莎莎也就不追究她说有沙滩这件事了。沙滩肯定是有的,不过究竟在哪里就说不好了。也许娟是在山南见过一片细软的沙滩,睡了一觉醒来,她又认为自己是在色麦村见过那片沙滩。
太阳从斜地里冲出云层的埋伏,又普照着色麦村这片人间福地。附近的人家,有薄田三分耕牛数匹,就足可安享人生。记得在凉粉店里,几个当地姑娘头挨着头凑在一起玩弄手上的手机,她们得了空也愿意挤在小世界里用手机看外面的大世界。大世界和这里的小世界很不同,她们嬉笑着吃完凉粉说完话,又各自散去,忘掉外面那个大世界。也有忘不掉的,卯足了劲要跳出山村这个龙门。我在次仁罗布的小说集《放生羊》里看到过类似的人物,在迷惘中,他们还是更愿意凭本心生活,用本心来度过困厄和苦难。我喜欢他们的眼眸,从那里可以读到春天的问候,没有更多的言语,一切都在不言中。无染,才能美好。鲁迅谈到过,别光劝那拉出走,你得告诉她出走以后该怎么办,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累了。我很愿意听着小提琴协奏曲《我和我的祖国》一路这样开下去,在漫天想像的春色里开下去。色麦村就留在身后那片大山里,离我越来越远。小提琴优美的琴声安抚了我心底里泛起的情感的涟漪。我们在桃林里看见人们丢弃在地上的塑料水瓶子,东捡西捡装满了一只纸箱。这一刻我的思想又回到了现实里,同意娟和莎莎的想法,为了明年色麦村的春天还能这么美,我们得捡回那些被人们随意丢弃在荒山野岭的不可降解的垃圾,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负责任的行为。
色麦村不说话,就在我们身后,露出了春天微微的笑。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