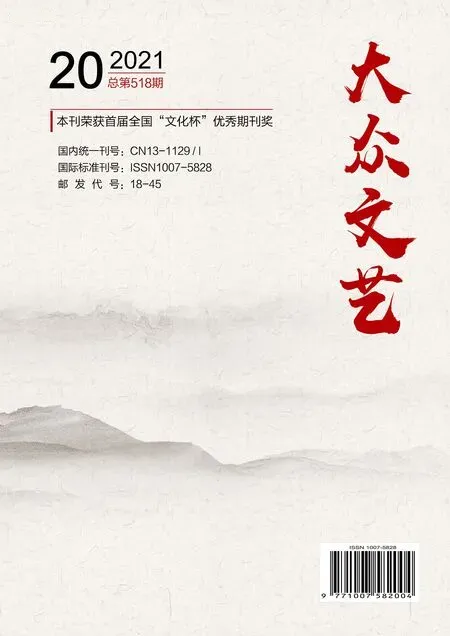“绿帽”下的史诗
——叙述自我视角解读福特式“凯尔特朦胧”
朱华根 (南昌大学 外国语学院 330031)
“绿帽”下的史诗
——叙述自我视角解读福特式“凯尔特朦胧”
朱华根 (南昌大学 外国语学院 330031)
《好兵》是英国现代主义开山大师福特·麦多克斯·福特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约翰·A·麦克沙恩认为:“《好兵》是20世纪文学成就之精品,是高度艺术性的创造,必须列入所有问世的伟大小说之列。”本文将陪伴读者重回彼时生动的历史现场,以叙述者道尔的叙述自我视角为研究视阙,重点分析道尔对其不忠之妻弗洛伦斯,情敌爱德华的理解甚于怨恨的复杂且矛盾的情感,继而管窥福特式“凯尔特朦胧”即构建骑士乌托邦,恢复古老绅士神话的理想世界。
福特;好兵;叙述自我;凯尔特朦胧:绅士神话
《好兵》是英国现代主义大师福特的匠心之作。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和读者对他的研究和关注与日俱增,其文学声誉也稳步上升。作为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评论界一直对福特高超的叙事技巧赞誉有加。凯瑟琳·安妮·波特由衷赞叹道:“任何一个读过《好兵》的人都会对艺术技巧的认识有长足的进步。”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道尔的叙述自我视角,试图再现其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重点探讨道尔对其不忠之妻弗洛伦斯,情敌爱德华的重新审视和再定位,进而探究和阐释福特式“凯尔特朦胧”即构建骑士乌托邦,恢复古老绅士神话的理想世界。
《好兵》中的叙述者道尔既是一个重要的故事参与者,又是与故事保持一定距离的旁观者。根据F·K·斯坦热尔的《叙事理论》,道尔被称为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者(The Peripheral First Person Narrator),因为道尔只是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此外,第一人称叙述体又分为经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和叙述自我(Narrating Self)。前者视角聚焦客观的经验世界,爱德华是这一世界的主角,叙述者道尔则是讲述他人的故事;后者则重点关注主观的精神世界,道尔是主人公,他向读者诉说内心的烦恼和困惑。两种视角作用迥异却相辅相成。与传统的第一人称小说不同,福特大胆采用双重聚焦的叙事技巧,并侧重于叙述自我视角且关注叙述自我即道尔的“现在”意识,并拉大叙述自我视角和经验自我视角的距离。他将叙述焦点从爱德华的故事逐渐过渡到道尔对故事的印象和理解,从描写外部现实转向揭露内心现实,着重探索道尔的心路历程。道尔特殊的身份使得其参与故事不密切、认识能力不足、观察力较弱,但是这反而使客观真实再现12年的生活成为可能。道尔以一种客观的叙述方式和极为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讲述着爱德华的爱情故事,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观看弗洛伦斯、爱德华等人的心态和思想。
一、福特式“凯尔特朦胧”
“凯尔特朦胧”一词最先由著名诗人叶芝(1865-1939)为首的爱尔兰前拉斐尔派创造。“它象征着一个模糊的、充满尘世困惑和烦恼的世界,也象征着一个充满理想的神话世界。”叶芝曾说:“要从一个毁坏了的,粗陋的世界中,创造出一个小小的、美好、愉快、有意义的世界,这是他想象中的爱尔兰。”相较与叶芝生活在同一时期的福特,不难发现,两人似乎有着耐人寻味的,尤其在艺术思想上的契合。二人均生活在维多利亚中后期,并于同年去世。叶芝的父亲是前拉斐尔派的肖像画家,叶芝也深受此流派的影响。福特的外祖父福特·麦多克斯·布朗也是一名前拉斐尔派的画家。另外,由于姻亲关系,前拉斐尔派代表人物罗塞蒂家族也成为了福特的家族圈,因此福特亦耳濡目染,“他的童年常常住在有拉斐尔派和古典韵味装饰的房间”,后来以唯美主义童话作家(唯美主义亦深受前拉菲尔派影响)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叶芝的“凯尔特朦胧”意在追求的是一个理想的、愉悦的新爱尔兰。本文试将福特式“凯尔特朦胧”具体界定为它既象征着一个模糊的、充满尘世困惑和烦恼的世界,更象征着构建骑士乌托邦,恢复古老绅士神话的理想世界。换言之,福特胸怀改良社会的赤诚之心,试图在工业化语境下重新建构骑士乌托邦,恢复古老绅士神话的理想“英格兰”。
有评论认为福特所有的作品都透露出“激情、骑士”的主题。福特缘何有如此深的骑士情结和古老绅士神话理想?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就如一个患了精神病的人一样,从一个他所不愿意的现实中退缩了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因此福特的骑士情结似乎有其个人因素:他出生于一个有着文化修养的绅士家庭,后来又在伊顿和牛津受到英国贵族的变迁的熏染,因此其作品中反复出现一群堂吉诃德式的贵族绅士形象。此外,博学多才的外祖父时常向他讲述一些有关亚瑟王、冰岛的英雄浪漫传奇故事。另一方面,福特的骑士情结可能亦是英格兰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型批评家荣格认为文艺作品是一个“自主情结”,其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自觉意识的控制,而常常受到一种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这种集体经验就是“集体无意识”。换言之,骑士在西方人的记忆中是一种道德与情感完美结合的象征,骑士情结是所有英国人的情结。
二、道尔的困惑和烦恼
道尔的困惑和烦恼主要来自于不忠之妻弗洛伦斯和情敌爱德华的婚外情。道尔漫不经心地讲述这段世纪之交上流社会的生动历史,尝试捕捉在特殊历史当口上层贵族间的复杂的、矛盾的、难以言表的纠结情感。对于弗洛伦斯,评论界由于忽视或无视两种叙述视角的距离,简单地将其标签化:“最虚伪、最自私、最寡廉鲜耻的人”“水性杨花的荡妇”等。弗洛伦斯究竟是怎样的人物?这样的评价是否有失公允?起初面对妻子与爱德华的的暧昧举动,道尔认为:“它就仿佛一条蛇已经从洞口探出头来。”这里妻子的反常举动可以理解为魔鬼撒旦的堕落沉沦。在知晓妻子的婚外情后,他憬然有悟:“她是一个烂透了心的漂亮的大苹果。”狭义而言,弗洛伦斯的心坏透了。广义而论,“苹果”在西方文化语境里涵义丰富,意味深长。伊甸园里智慧树上的苹果象征着人类的原罪。“烂透了心的苹果”喻指背负原罪的弗洛伦斯,罪大恶极。“苹果”还象征智慧,象征着人的羞耻之心。弗洛伦斯虽掌握了不少的知识,却失去了心灵的乐园,也没了羞耻之心。“漂亮的大苹果”还象征着魔鬼撒旦的诱惑。爱德华即亚当也因抵挡不住诱惑,而最终堕落。总之,道尔恨她,恨得咬牙切齿,想将她置于永恒寂寞的煎熬之中。
另一方面,跟随道尔的叙述自我视角,我们也许可以管窥道尔对妻子的理解同情甚于谴责愤恨的复杂情感。一个英国古老骑士价值、绅士文明神话的卫道士弗洛伦斯的形象出现在英国史诗里。一言蔽之,由于妻子的对骑士情结、古老绅士神话的执念,道尔随之产生了反常而奇特的情感。首先,弗洛伦斯的祖上即是英国的名门望族,曾是布兰肖庄园长达两个世纪的主人,因此她从小就对古老的贵族情结和精英意识耳濡目染,随后便疯狂地迷恋上英国风俗。另外,她的叔叔约翰对其性格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约翰是一个仍然保留着古老绅士遗风,残存欧洲文明之光的“现代人”,乐善好施,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此外,弗洛伦斯还热爱参观考古遗址、古纪念碑和古堡,喜欢谈论哈姆雷特,勇士和国王、圆桌骑士的传奇故事,甚至嘲讽利奥诺拉“说话不像淑女的谈吐”……她最大的愿望即在祖先的庄园里当一位乡村妇人,感受古老家族的荣光。最后,紧随道尔的叙述轨迹,读者还可能会意识到道尔本人对英国古老绅士神话的认同和向往。道尔坦言:如果妻子和爱德华确实真心相爱,他向上帝发誓绝不会拆散他们,并会用体面地方式使他们结合,还会付一笔生活费。道尔所言似乎颇有绅士风度。另外,当道尔与爱德华一起在布兰肖庄园并驾齐驱,策马扬鞭驰骋草原时,马儿动作优美,乡村静谧和谐,村民质朴健康,古老的大厦美轮美奂……道尔惊呼:第一次品尝到英国生活的滋味,那真是惊人,令人倾倒。道尔所叹亦可看出其对英国古老绅士神话的赞美和向往。因此,当道尔脑海里浮现最后审判日里妻子孤独落寞,踽踽独行的情景时,他的心里有着一股巨大的冲动想去安慰。
三、结语
《好兵》中充斥着叙述者道尔的两种含混交织的声音。道尔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其叙述前言不搭后语,评论也常常自相矛盾。弗洛伦斯和爱德华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即便到了小说的最后一页,一切都在混沌之中,模糊不清。道尔含糊又痛苦地问自己:这些人本应该怎么做?“这一切都令人疲惫、厌烦,烦透了。”这一切都是漆黑一团,朦胧不清。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一样,福特也认为文学必须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外部事件对个体经验的影响和个人对事件的价值判断。本文借道尔的叙述自我视角,尝试全景展现道尔对于弗洛伦斯和爱德华的重新审视和再定位的心路历程,希冀反映福特式“凯尔特朦胧”。从《好兵》中绅士遗风的卫道士约翰叔叔颇具戏剧性的离世,到“英国情结”的追梦人弗洛伦斯和绅士神话捍卫者爱德华相继自杀,我们也许可以解读出福特构建骑士乌托邦,恢复古老绅士神话的理想世界以改良社会的构想似乎流溢出一种朦胧不清的悲观情绪。
[1] J·A·Meixner.Ford Madox Ford:A Critical Study[M].1962.
[2]许锦霞.从《好兵》看福特的艺术追求和道德探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7).
[3]马瑜.创作的非个人化及叙述中心的内移——评福特《好兵》的叙事风格[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
[4]王佐良,周钰良.英国20世纪文学史[M].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2(8).
[5]福特,张蓉燕译.好兵——一个激情的故事[M].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6]贺一舟,胡强.从《好兵》看福特的伦理观与骑士情结[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7]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朱华根,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