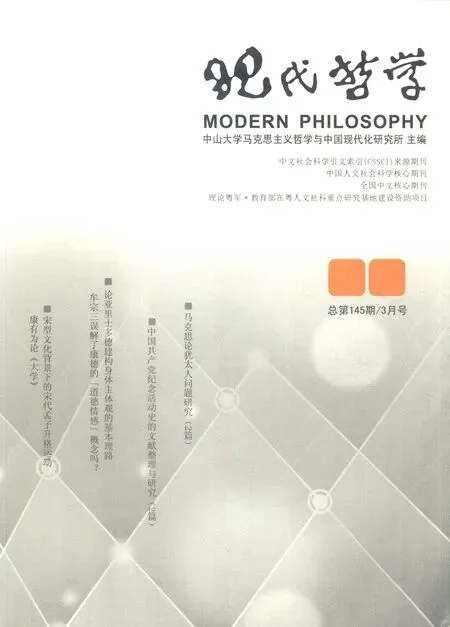凶手、寻找者、超越者:“上帝之死”中“超人”的三副面孔*
马新宇
凶手、寻找者、超越者:“上帝之死”中“超人”的三副面孔*
马新宇**
【摘要】“超人”是“上帝之死”这一事件中的主角之一,而不理解“疯子”及其与“超人”的关系就无法完全读懂“超人”。上帝死了,“疯子”承认自己是凶手之一,而以权力意志为本质的“超人”也是上帝走向死亡之路的推手,“疯子”或者凶手是“超人”的第一幅面孔;上帝死后,“疯子”呼喊着寻找上帝,“超人”作为本质上失去上帝的人,不知所寻为何却同样处于寻找的维度之中,寻找者是超人的第二幅面孔;在“上帝之死”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中,“疯子”对围观者和“超人”对“迄今为止的人”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并在信仰之可能性、寻找之态度、思之有无这三个方面表现相同,超越者是“超人”的第三幅面孔。对这三幅面孔的描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超人”之超越性,并有助于全面把握尼采视阈中人之本质的绽出历程。
【关键词】疯子;超人;上帝之死;权力意志
“超人”是尼采哲学的核心词汇之一,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读,这一术语与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原文为“Der Wille zur Macht” ,又译作“强力意志”。、虚无主义、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合法性*合法性原文为“Die Gerechtigkeit”,又译作“公正”、“正义”等。一起构成了尼采形而上学的五重内涵*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 6.2,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ein, 1997, S.233.中译本参见 [德]海德格尔:《尼采》下,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2页。。因而在对尼采的研究中,“超人”吸引了太多目光,而那个宣布“上帝死了”的“疯子”则黯然失色。这不由得让人追问,“疯子”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宣布“上帝已死”,其使命就此完结?断言其为“疯子”的根据何在,仅在于“疯子”之言与理性思维相悖?“疯子”若然已疯,言语何以如此睿智、诗意并充满历史感?他与“超人”有无关系,若有,是何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既是理解“疯子”的关键,也是理解“超人”的关键。
一
对“疯子”与“超人”之间的关系的探究绕不开尼采的一句话,即“上帝死了”。尼采正是通过“疯子”之口宣布了上帝的死讯:“疯子跃入他们之中,并用眼光逼视他们。‘上帝去哪儿了?’他呼喊道,‘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我们所有人是杀他的凶手’。”*Nietzsche Friedrich,Morgenröteu.a.,KritischeStudienausgabe(KSA).Bd. 3,hg. v. Giorgio Colli/Mazzini Montinari,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KG, Berlin·New York ,1999, S.480.中译本参见 [德]尼采著,黄明嘉译:《快乐的科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译文略有改动。这段话鲜明地告诉我们,“疯子”已经意识到了上帝之死,并指出了杀死上帝的凶手。
“疯子”的德文原文是“Der tolle Mensch”,形容词“toll”除了具有“发狂的,发疯的,疯狂的”等意之外,还有“了不起的,极好的”“非常的,非同寻常的,惊人的”等意。在口语中,后者用得反而更多。因此,“疯子”不仅仅是疯了的人,还有可能是异乎寻常之人*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对此亦有说明,参见上书第208页注释一。。因而原文可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意识到上帝之死的这个人是疯子,因为按照一般的理性思维,上帝能决定生死,但他自己不会死亡,高呼“上帝死了”的人很有可能是疯掉了;一是意识到上帝之死的这个人异乎寻常,能超越一般的理性思维,并说出振聋发聩的话语的人,一定异于常人。在中文语境中,我们一般都在第一个层面理解“疯子”。
此外,“疯子”不光意识到上帝之死,他还参与到上帝之死的进程中,并起着主导作用。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凶手”,但其他人对这一点无动于衷,“他重又注视听众,听众缄默不语,诧异地望向他”*Nietzsche Friedrich,Morgenröteu.a.,KritischeStudienausgabe(KSA).Bd. 3, S.481.中译本参见上书第210页,译文略有改动。。这些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疯子”的言语,因而虽然所有人都是凶手,但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只有“疯子”,这说明了“疯子”之异于寻常。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如果上帝之死属于伟大事件,并且所有人都参与到其中,但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人与这种行为根本就不相匹配。“这种行为之伟大对于我们是否太过伟大?我们自己是否必须变成上帝,以看起来配得上这种伟大?”*Ibid.,S.481.中译本参见上书第209页,译文略有改动。也就是说,完成杀死上帝这一伟大行为,可能意味着实施这一行为的凶手即使不能变成上帝,也在地位上接近上帝,以与行为之伟大相称。但所有凶手中只有“疯子”对上帝之死有直接意识,这就意味着“疯子”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的定位,其他凶手即使和他地位相同,也对此毫无感觉。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上帝究竟怎能被杀死?人们曾经怎能杀死上帝?”*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67,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ein, 1999, S. 180.这从常识角度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西方文化中,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人与上帝密不可分。对人的诠释离不开上帝,反过来也一样”*刘森林:《“上帝之死”与“现实的个人”》,《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帝之死究竟实现了什么。因为如果上帝之死是一种既成事实,并且找到了凶手,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再现杀死的过程,以明晰杀死的动因和途径,而实现这一点的惯常做法是由果溯因。尼采认为,由于杀死上帝这一行为,“始终在我们之后出生的人,应被放入比迄今为止一切历史更高的历史中!”*Nietzsche Friedrich,Morgenröteu.a.,KritischeStudienausgabe(KSA).Bd. 3, S.481.中译本参见[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第210页,译文略有改动。也就是说上帝之死开启了一种更高的历史。

笛卡尔的“我思”虽然强占了传统形而上学中上帝、理念的地位,但它还不是设定价值的最后的根据,实现这一点的是尼采。因为他提出了权力意志,并将其视作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度。“主体性就到达价值设定本身最后的根据……当形而上学将权力意志经验为所有现实之物的现实性”*Ibid., S. 182.,人就是承载这种主体性的存在者,并因具备权力意志而超越其传统本质。“人——超越了其迄今为止的本质,进入被明确经验和接受的权力意志之‘更高历史’——就是‘超人’”*Ibid., S. 183.。因此,以主体性作为价值设定的最后根据就是将“超人”作为根据。并且,“如果超人创造了一种新的价值,那他不是在抽象的思想高度虚构这种价值,他多数情况下基于新的生活表象”*Hans-Martin Schönherr-Mann,DerübermenschalsLebenskünstlerin, Matthes & Seitz Berlin, Berlin, 2009, S. 23。
由此可见,杀死上帝的过程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是笛卡尔的“我思”强占上帝、理念的地位,获得对其他存在者的优先性;二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成为主体进行价值设定的最后根据,并使具备这一意志的“超人”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人。
“超人”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权力意志之人属,在他以出自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的话语显露之前,就已经是历史的。如果他说另一种语言并从权力意志而说——这意志按照产生过的权力的本质从未说出他想说的——那么他同样是历史的,并且之后仍是。”*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67, S.185.这意味着,在杀死上帝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超人”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凶手,而是自始至终与人对上帝的信仰、质疑、杀害同步。
通过前文对“疯子”这一词语的分析可知,该术语本身包含非同寻常之义。“疯子”也是所有凶手中最具特性的一位,在地位上接近上帝以配得上行为之伟大,在本质上迥异于上帝之死这一事件的围观者。而“超人”在杀死上帝中亦处于关键地位,他以权力意志这样一种无条件的主体性的形式强占了传统哲学中上帝的地位,并在本质上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因此,从“上帝之死”这一事件来看,“疯子”与“超人”不过是一体两面。那么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称呼呢?
海德格尔的回答是:“超人走出迄今为止的人(理性动物)所遗留的、形而上学的、未成熟而思的本质,只不过是为了进到理性和动物性的本质基础即权力意志中。因此,在所见的迄今为止的人属和他的形而上学世界的迄今为止的海平面中,超人必然被视作疯癫的人,亦即疯子。”*Ibid.,S.186.这就是说,“超人”是以权力意志为本质的人,在没有到达这一点之前,人依旧停留在理性动物的层次。从这一层次出发,必然会把“超人”视作“疯子”或者凶手,这是“超人”的第一幅面孔。
二
通过分析“疯子”与“超人”在上帝之死这一事件中的性质和作用,并以超越了理性动物的眼光为视角,可以发现“疯子”本质上就是“超人”。又因为现实上我们囿于理性动物的眼光之中,必然把会“超人”视作疯子,但两者本质上同一。这种同一亦可被上帝之死中的种种表现所证实,而在这些表现中,我们可以发现超人的另一幅面孔。
“疯子”已然经验到了上帝已死,为了宣布这一消息而寻找上帝,从表象上看就体现为寻上帝不见而宣布上帝已死。“他在大白天点着灯笼,跑向市场,不停地呼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Nietzsche Friedrich,Morgenröteu.a.,KritischeStudienausgabe(KSA).Bd. 3, S.480.中译本参见[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第208页,译文略有改动。这种寻找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出,而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找不到,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上帝之死。寻找更深层的目的在于找出上帝之死实现了什么。这一点我们在前文有所提及,即上帝之死开启了一种更高的历史。但需要进一步明确,更高的历史究竟高在何处?
“疯子”在宣布上帝之死后接着说道:“我们怎能吸干海水?谁给我们海绵,以拭去海平面?当我们让地球脱离太阳的锁链,我们意欲何为?”*Ibid., S.481.中译本参见上书第209页,译文略有改动。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这里的“吸干海水”“拭去海平面”意指传统的超感性世界、本质世界、理念世界、可知世界的瓦解,以及上帝对世界的支配地位的消除,代之而起的是主体地位的上升和主体性的兴起。
“地球脱离太阳的锁链”含义更为丰富,“一方面使人想起普罗米修斯这个帮助人类、反对诸神的人。他被宙斯用铁链锁在石头上,后又被赫拉克勒斯(一说被宙斯本人)解开锁链放出来。另一方面……暗示由哥白尼学说引发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的转变。这两件事都……赞颂‘生命’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第210页注释一。。表面上看,把这句话与哥白尼革命联系起来似乎稍显牵强,因为哥白尼革命确证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句话则是让地球脱离太阳,两者在方向上完全相反。但哲学上讲的哥白尼革命不纯粹以事实类比,更强调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从康德把自己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称作哥白尼革命可以看出。事实上,“地球脱离太阳的锁链”更应该让人想起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因为他通过这种革命确立了主体的绝对地位,“人为自然立法”是对这一地位最直接的概括。
由此可知,“疯子”找到的就是人的地位的改变。上帝之死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摆脱了上帝、摆脱了理念的阴影,确证了人相比其他存在者的优先地位,从而开启了一种更高的历史。这是作为上帝寻找者的“疯子”寻上帝不果而告诉我们的,但寻找不光是“疯子”之所为,上帝寻找者也不单指“疯子”,海德格尔同时以之意指“超人”。
如果说“超人”也是上帝寻找者,那么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寻找?“超人”走上寻找之路是由其特点决定的,因为“超人不是从上帝的位置上抛弃上帝,以占据这个位置自身。这样,超人就是本质上失去—上帝的人”*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67, S. 193.。因为失去了上帝,所以要寻找上帝,这就是他寻找的原因。这一点和“疯子”对上帝的寻找是同一个路径,因为“疯子”也是预设了上帝之死而走上了寻找之路。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超人”究竟要寻找什么,他能找到什么?“超人”因为失去了上帝而寻找上帝,但他必须意识到寻找上帝只是寻找的出发点,而不是归宿。因为“上帝死了”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必须坦然面对。人成为超人,就是为了“能忍受谋杀上帝”,并且“只有超人能忍受自己创造的祛神之后的世界的空虚”。*Bernhard Sorg,Homunculusalsübermensh, Unverönderter Text einer im Wintersemester 2003/2004 an der Universtät Bonn gehaltenen Vorlesung.也就是说,“超人”必须面对并超越“上帝死了”这一事实这样他才能有所寻获。这一点也和“疯子”所面对的情况一样,“疯子”正是通过确证上帝已死这一事实而发现人的地位的改变。
海德格尔据此确证了“超人”与“疯子”的同一,并进一步追问:“不能从这个新的位置,从超人之思中,还并且正好开始新的寻找吗,这寻找——如同疯癫之人所表现的那样——甚至成了一种对上帝的‘永不停歇的呼喊’?”*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67, S. 194.这里的疯癫之人(Der verrückte Mensch)与“疯子”(Der tolle Mensch)虽然在原文中用的是不同的形容词,但海德格尔将两者用“也就是”等同起来。之所以出现书写上的区别,是因为后者含有非同寻常之义,前者则无。这句话用“疯子”的寻找方式注解从“超人”开始的寻找,充分说明了“疯子”与“超人”之间的同一关系。
然而,我们还是没有回答“超人”到底找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可能的答案包含在这段话中:“一种总的来说按照超人方式的思,出自权力意志的思向来能找到寻找上帝的维度吗?这种思能把具有神性的东西思为存在吗,这思究竟能思存在吗?”*Ibid., S. 195.“按照超人方式的思”与“出自权力意志的思”是同一种思,这种思的第一重任务是寻找上帝,这一点我们已经很明确,另一重任务是思存在。海德格尔对这一点抱以怀疑的态度。他区分了“作为存在的存在”和“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并且不认为超人之思能实现对存在本身的思考,而只能实现对“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的思考,所以他说:“尼采把权力意志思作存在者之存在。这是肯定的。但是,对于在权力意志的意义上经验存在者本身的思者来说,什么是存在?‘存在’是一种在权力意志中被设定的价值。”*Ibid., S. 195.
因此,“超人”找到的就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即权力意志,但“超人”本身就是以权力意志为本质的人,他找到的东西就在自身之中。但由于超人从超越传统而来,因而必须寻找上帝,找寻的过程更加明确了自身所具备的权力意志的超越性。这个过程使“超人”实现了从自在地具备权力意志向自为地具备权力意志的转变。权力意志“乃是权力本身的本质,这个本质就在于权力的那种强势作用,也就是使权力进入它能支配的自身提高之中的强势作用”*[德]海德格尔:《尼采》下,孙周兴译,第646页。。权力所能支配的自身提高就是主体相对客体而言的优先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意志才能成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度,因此,以权力意志为本质的超人所获得的无非是一种无条件的主体性。这和“疯子”所找到的人的地位的改变异曲同工。
由此可见,“疯子”和“超人”寻找的动机相同,无非是宣布“上帝死了”;寻找的出发点也相同,“疯子”必须面对上帝之死这一事实才能有所寻获,“超人”也必须超越“上帝死了”才能找到寻找的维度;所寻找的东西更是相同,“疯子”找到的是人地位的改变,即成为主体,“超人”获得的无非是无条件的主体性。因此,我们可以从寻找的维度断定“疯子”与“超人”的同一,并且在上帝死后,两者都作为寻找者而出现,寻找者因而是超人的第二幅面孔。
三
我们不仅可以从“疯子”与“超人”在上帝之死中扮演的角色来断定两者之间的同一,也可以从他们在上帝死后的表现来确证这种同一。这种同一关系还体现在“疯子”之于围观者与“超人”之于“迄今为止的人”的超越中。这两种超越本质上是同一种超越,只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接触这种超越,因而形成不同的认识。超越者正是“超人”的第三幅面孔。
“疯子”对围观者的超越首先体现在他对待上帝之死这一事件的态度中。当他以寻找上帝的形式宣布上帝已死时,得到的是其他人的嘲讽。“其中一个问,上帝走丢了吗?另一个问,他像小孩一样迷路了吗?或者他把自己藏起来了?他害怕我们??乘船走了?流亡了?——他们就这样乱糟糟地又嚷又笑。”*Nietzsche Friedrich,Morgenröteu.a.,KritischeStudienausgabe(KSA).Bd. 3, S.480.中译本参见[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第208页,译文略有改动。海德格尔把这些人称作围观者(die Herumsteher),该词在德文原文中是指“站着不做事、无所事事”的人。这些人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上帝,更没有严肃地考虑过上帝之死,自然无法理解上帝之死。这些话语如果只是用来形容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当然非常恰当。但这些围观者不仅仅是不信仰上帝的人,因为疯子说地非常明确,“你们和我,我们所有人都是杀他的凶手”,因而围观者“也指那些认为自己信仰过上帝的人。‘我们所有人’——这词让人想到西方的历史的人属,他的历史建基于形而上学的历史进程”*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67, S.186.。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历史在形而上学中获得了基础,在形而上学的视阈内看到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在内。他们都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上帝之死这一事件。所以,疯子才会说:“我来得太早,还不在对的时间,这惊人的事件还在途中并徘徊着,它还没有渗透进人的耳朵。”*Nietzsche Friedrich,Morgenröteu.a.,KritischeStudienausgabe(KSA).Bd. 3, S.481.中译本参见[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第210页,译文略有改动。这种状况把“疯子”与围观者鲜明地区分开来,通过“疯子”的先知先觉证明其对围观者的超越。
这里所讲的围观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迄今为止的人”。“尼采把迄今为止的人——其本质仍没有从权利意志意愿并同时思——称作‘尚未被固定的动物’。”*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67, S.183.这一说法主要针对“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论断。在尼采看来,理性并不足以作为最后的根据来定义人,“只要理性没有建基于权利意志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既不会固定理性本身,也不会固定人之本质的动物状态”*Ibid., S.183.。即是说,以理性为本质的人尚未实现人之本质的完全形态,因而人本质上就是“尚未被固定的动物”。
不过,“超人”与“迄今为止的人”即这些尚未意识到上帝之死的围观者并非截然对立。海德格尔在多个地方明确地表明了这种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有两处。
第一处在刚引入“超人”这个概念时:“尼采用这个极其令人误解的称呼不是意指任何一种迄今为止的‘人’种的被隔开的样本……相反,这个称呼指的是这样一种人属的本质形态,即在未来将其本己的人之存在,经验并承认为权利意志之人属。”*Ibid., S.183.
第二处是在论述权力意志之后:“超人走出迄今为止的人(理性动物)所遗留的、形而上学的、未成熟而思的本质,只不过是为了进到理性和动物性的本质基础即权力意志中。”*Ibid., S.186
把这两段话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超人”:一是“超人”不是“迄今为止的人”,即使我们把他和其他存在者隔开,以彰显其特殊地位,他根本就不在迄今为止的领域;二是“超人”并非横空出世,他的出现是超越“迄今为止的人”的结果;三是“超人”是以权力意志为自己的本质形态的人,这是他的超越性的体现,也是他和“迄今为止的人”的最大不同。
如前所述,“超人”就是“本质上失去上帝的人”,因为他以权力意志为本质,因而对上帝之死有明确认识,但“迄今为止的人”根本就没有经验到这一点。这是“超人”超越性的体现之一。这一点和“疯子”对围观者的超越是同一维度的。需要指出的是,在论述“疯子”对围观者的超越时没有从“疯子”的未来样态展开论述,而超越了“迄今为止的人”的“超人”则“代表原则上的开放状态、不可固定状态”*Johanna Rahner, Zwischen Projektion und Wahn, Akademie der Diöyese Rottenburg Stuttgart,Weingarten,9-10 ,Januar 2010.。这是由“疯子”与“超人”的出场顺序决定的,不代表这种超越不处于同一维度。
海德格尔正是经验到了“疯子”之于围观者、“超人”之于“迄今为止的人”的这种同维超越,因而在论述时直接将“超人”与“疯子”放在一块儿进行论述:
超人虽然——从迄今为止的人出发并仅仅这样来看——是在其本质中疯癫的人。但“疯子”与那种类型的不信仰上帝的围观者没有共同之处,原因在于,围观者不是因此而不信仰(因为对于他们说上帝已经难以置信),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放弃了信仰的可能性并且不能再寻找上帝。他们不能再寻找,因为他们不再思……与之相反……“疯子”对这一点毫不含糊……还更为坚决,他以呼喊上帝的方式寻找上帝。*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67, S.193.
这段话简明扼要地讲清楚了“超人”、“疯子”与围观者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围观者已经放弃了信仰的可能性,“超人”与“疯子”没有放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还继续信仰上帝,因为上帝已死。毋宁说,他们信仰某种不期而遇的找到物,这找到物必须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找出。第二,围观者不再寻找上帝,“超人”与“疯子”还在继续寻找。他们已经经验到了上帝之死,所谓的寻找只是为了找到寻找的维度,以在这维度遭遇某种找到物,因而他们以寻找上帝为出发点,但不以找到上帝为归宿,而围观者根本就没有尝试寻找。第三,围观者不再思,“超人”与“疯子”以思为己任。“疯子”呼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这“也许就是一位思者在作真正地歇斯底里的呼喊?我们的思的耳朵呢?它总听不到这种呼喊,只消它没有开始思,它就会长期听不到这呼喊”*Martin Heidegger,Gesamtausgabe.Bd5,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ein, 1977. S.267.中译本参见[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19页,译文略有改动。。这里把“疯子”和思者等同起来,这思者可能是尼采,可能是海德格尔本人,也可能意指任何一个走上了思之道路的人,但作为上帝寻找者就是“超人”。“我们”没有走上思的道路,因此“我们”听不到这种呼喊,并将呼喊上帝的人视作“疯子”,这个“我们”就是围观者。故而超越者是“超人”的第三幅面孔。
综上所述,我们从“疯子”与“超人”在杀死上帝中所扮演的角色推定,“疯子”或者凶手是“超人”的第一幅面孔;从上帝死后“疯子”与“超人”的行为可以看出,寻找者是“超人”的第二幅面孔;从杀死上帝和寻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疯子”与围观者、“超人”与“迄今为止的人”的关系可以看出,超越者是“超人”的第三幅面孔。因此,“疯子”就是“超人”,凶手、寻找者、超越者是“超人”的三幅面孔。
(责任编辑林中)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的逻辑与价值虚无主义的关系研究”(2014C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新宇,哲学博士,(西安 710127)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武汉 430074)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3-0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