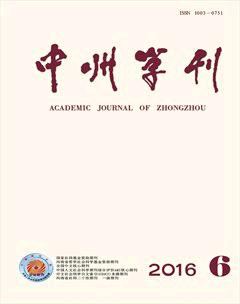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刘生良
摘要: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魏晋玄学;庄学著述;《庄子》文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6-0138-08
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甚多,但流传下来的却很少。从现存文献资料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庄学著述,主要是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故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正始时期,始盛玄谈。由此开始,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何、王等人在东汉尤其是建安文士有关言论基础上,祖述老庄,糅合儒家经义,清谈玄理,建立了玄学。特别是王弼通过对相关哲学问题进行抽象论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玄学理论,并提炼出“名教出于自然”的重要命题,成为正始玄学的标志性理论成果。而随着何晏被杀、王弼病逝,正始玄学暂时休歇。第二个时期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嵇、阮等人面对司马氏专权、“名士少有全者”的黑暗恐怖局面,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经过他们的努力,原来以老子为主体的玄学至此演变为以庄子学说为主体,流行语“老庄”也变为“庄老”,从而把魏晋玄学推向新的阶段。而随着嵇康遇害、阮籍谢世和晋朝建立,魏末玄学亦告一段落。第三个时期是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在短暂统一、相对稳定的局面下,西晋玄学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由魏末的激烈批判转而与之合一。其显著标志就是名士郭象由不愿做官而做了高官,特别是他通过注释《庄子》,在向秀“以儒道为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使“名教”和“自然”的矛盾得到统一,也把玄学理论推向最高峰。第四个时期是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鉴于王室南迁,偏安一隅,玄风再盛。东晋名士在实践中将名教与自然融通为一,把玄学带入了审美的境界,并与佛学合流。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整个南朝。而随着庄佛结合日益紧密,玄学也开始式微,走向衰落。但庄学却未受影响,依然持续不衰,甚至因与佛学合流而更加兴盛。
从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其以“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论题,自始至终都与《庄子》有密切关系,且多以庄学为主。其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这在先秦《周易》《论语》《老子》中都多少谈到过,尤其《庄子》中多次谈到“言”“意”关系。《天道》篇云:“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秋水》篇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在《外物》篇,庄子更明确提出了“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命题。这些说法虽属哲学命题,但对于文学来说同样极有意义。这是因为“言”和“意”的关系,反映了文学创作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庄子看来,无疑应以意为主,以言为辅,言乃达意工具,得意可以忘言,且言有尽而意无尽。这一理论是与他的哲学思想和创作实际密切相关的。庄子哲学“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尽的;《庄子》文本又是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和“寓言”“重言”“卮言”写成的。他重意轻言,其意在于提醒读者:勿以吾意尽矣,所言不过道之粗者耳!且吾言有尽,吾之哲理则奇奥深闳,广远无尽;亦勿以吾言之荒诞诡谲,而忽视吾意之深闳精辟!且吾言在此,寄意于彼,需用心体悟。在《徐无鬼》等篇中,庄子又从精神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不言之言”的命题。这些探求,表明庄子实质上已朦胧地意识到了文艺创作应构成一定的形象和境界,来吸引、打动读者,让读者去自己感悟、会意等问题。至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名士们在其“有无本末”之思想观念指导下,对言意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做出了富有创意的阐释,使庄子的言意观得以拓展和深化。
作为正始玄谈的先导者,汉魏之际的名士荀粲率先发起言意之辨。据何劭《荀粲传》记载,荀粲在回答其兄疑问时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①很显然,荀粲是运用和发挥《庄子》中《天道》篇和《秋水》篇的言意观,来反击儒家《易经》“立象尽意”“系辞尽言”的观点,认为“象”和“系辞”表达的只是象内和言内之意,而“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有“象”“辞”所不能尽者。随后,魏初术士管辂亦谓神智之“几微”者“可以性通,难以言论”(《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裴松之注引)。荀、管之说,为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开了先路。
正始时期,年轻有为的名士王弼(226—249)以其高卓的才识,对言、象、意的关系作出了更富思辨色彩和创新意义的阐释。其《周易略例·明象》云: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和荀粲相比,王弼这段话同样是就《周易》而言的,也同样采用了援《庄》释《易》的做法,但不同之处有二:其一是他没有像荀粲那样采用和发挥《庄子》中《天道》篇及《秋水》篇的言意观以反对儒家“立象尽意”“系辞尽言”的观点,而是一上手就指出象是用来表达意的,言是用来显示象的,意是可以通过象与言来把握的,并强调“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可见他十分重视言、象对于表意的作用,并未简单地认为“言不尽意”。他以此来阐释言、象、意三者的关系,反倒是肯定和发挥了《周易·系辞》“立象尽意”“系辞尽言”的观点,同时还纠正了庄子糟粕书籍、轻视语言文字的偏颇。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援用和发挥了《庄子·外物》篇“得意而忘言”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学说。王弼沿着庄子“得意忘言”的思路,并且袭用其《外物》篇“得兔忘蹄”之类的比喻,但并未简单地因袭庄子的言意观,而是在“言”“意”之间加上了“象”这一中间环节,从而架起了一座联通三者的桥梁,并从本体论角度对其内涵和关系作了系统阐述,还将其化为玄学最重要的方法论。他所说的“忘象”“忘言”,是要人们打破“言”“象”的有限性,以领会其本意,而不是主张遗弃“言”“象”去凭空冥悟那虚无的宇宙本体②。虽然王弼在此只是援《庄》释《易》,并非专门阐释《庄子》,但这毫无疑问是对庄子思想的祖述、发挥和超越。王弼还运用言意之辨这一方法论,解决了不少玄学难题。正如汤用彤所说:“此‘得意忘言便成为魏晋时代之新方法,时人用之解经典,用之证玄理,用之调和孔老,用之为生活准则,亦用之于文学艺术也。”③亦如方勇所说:“从这个方面说,《庄子》不只是玄学的原始材料和讨论对象,还要更深一层,即其思辨方式和玄理意蕴已经渗透进玄学的躯体。玄学正是站在庄子学这个巨人的肩上,并不断超越自己,最终才独立于老庄之外别树一家。”④
王弼之后,出现了一些关于言意问题的专论,如嵇康《言不尽意论》,欧阳建《言尽意论》等。嵇文已佚,难知其详,参考其传世文章中的相关言论,可知他对庄子的“言不尽意”论有所补充和发展。欧文是有感于世之论者咸以为“言不尽意”的风尚而标新立异地提出“言尽意”论,理论上无多创新。接下来,郭象则在治《庄子》过程中,根据《庄子》一书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寄言以出意”的思想,很有价值和意义。这在下文再作讨论。
整个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差不多就是沿着“言”到底能不能尽“意”这一思路延续下去的,是对《庄子》言意思想的拓展和深化⑤。庄子的言意观,经过魏晋名士的讨论和创造性阐释,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使言意及其关系不仅成为玄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和方法论,而且成为我国审美学和文艺学领域的重要命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理论,对当时和后世文艺创作、文艺欣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陆机《文赋》论其创作甘苦,“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而力求得心应手以达意。卢谌《赠刘琨》云“谁谓言精,致在赏意;不见得鱼,亦忘厥饵”,在诗歌中阐发了庄子言不尽意的思想。陶渊明在创作中更深有体会,时有以言寄意、以文导意会意之说,尤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名句。谢灵运《山居赋序》云“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道出了其深受庄子影响的创作思想。范晔《狱中与诸甥书》,倡言“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事外远致”。刘勰《文心雕龙》标举“义生文外”“言外之意”,同时重视通过“陶钧文思”等多方面的努力最大限度地达意。锺嵘品评诗歌,发明“滋味”说。这些,都是庄子言意观和魏晋言意之辨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和发挥。后世为人们所熟知的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情在词外”“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许多术语和说法,都是从这里滋生出来的;在中国诗文理论中占重要地位的“意象”“意境”学说,也是由此衍生和发展而来的。
二、阮籍《达庄论》以文学语言阐释《庄子》
阮籍(210—263)是著名的“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世守儒业之家,其父阮瑀受学于蔡邕、郑玄,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籍“本有济世志”,然“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于是由崇尚儒学、“博览群籍”转而“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而且“以庄周为模则”(《三国志·魏书》卷二一)。他撰有《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等玄学论文,其中《达庄论》乃通达、光大《庄子》的专论。
《达庄论》一文⑥,是以假托一位道家“先生”回答并反驳“缙绅好事之徒”之诘难的方式展开对庄子学说长篇大论阐发的。作者开篇写道:“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坌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这位逍遥自在地遨游于《庄子》一书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的“先生”,显然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效法庄子的这一系列思想行为,自然引起了一帮“缙绅好事之徒”的不满,遂一起前来向他发难。其中有一“雄杰”在“怒目击势”地陈述了一番儒家的思想主张之后,便攻击庄子学说道:“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徼惑以失贞,而自以为诚者也?”于是,“先生乃抚琴容与,慨然而叹。俯而微笑,仰而流眄,嘘噏精神,言其所见”,说了很长一段话,以十分轻蔑的态度回敬对方,随即展开自己对庄子学说的正面阐释和发挥。他首先以自然之旨阐发了庄子的本体论和齐物论思想: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温。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
阮籍以为天地之生成乃是自然而然,自其生成起即保持着自我本真,故“自然者无外”;天地又涵盖着世间所有物体,故“天地者有内”。世间万物彼此虽差异万千存于天地,却无一差别都生于自然。其中“故曰”以下四句结论,显然来自《庄子·德充符》篇。不仅如此,作为与其他事物一样生于天地间的人,也是自然之产物。所以作者进一步认为,“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在天地自然面前,其所谓生死、寿夭以及大小、是非也是齐一的。接着他便援引并组合《齐物论》《德充符》《秋水》等篇的有关文字,进而对庄子齐生死、一是非的思想作了发挥:
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只有庄子才是从天地自然出发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强调指出“庄周之云”乃“循自然、推天地”的“寥廓之谈”和“致意之辞”,而儒家学说只不过是“分处之教”“一曲之说”罢了,且流弊十分严重。接下来,他又综合《刻意》《缮性》《在宥》《天地》等篇旨意,阐扬庄子所标举的“至人”思想,褒扬广成子这样的“潜身者”,贬斥轩辕氏这样的“离本者”:
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不消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
顺势而下,他又联系庄子《秋水》《在宥》及《山木》等篇所述人物故事,畅论“自然之道”和“至道之极”,抨击大道不行的混乱现象尤其是“儒墨之后”的种种弊端及危害,从而指出:“庄周见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辩也哉?”最后,他还说道:
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兹容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
在他看来,庄子之书还有不足,其顺应自然以逍遥的主张和做法还与自己高扬自我以逍遥颇有不同,故他在“以庄周为模则”的同时,对其还有所批评和超越。“于是二三子者,风摇波荡”“乱次而退”“丧气而惭愧于衰僻也”。
总的看来,阮籍此文偏重于对《庄子》思想的阐释,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却也可以说是对《庄子》的文学语言性阐释,即以文学的方式对《庄子》思想作出的生动阐释。这对后世文学创作中的《庄子》文学阐释颇有影响,故不惮其烦地论列如上。《达庄论》直接援引和化用《庄子》13处,兹不烦列赘述。阮籍还有一篇《大人先生传》,此文与嵇康《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传世之作类似,虽与庄学有关,但不属于专门的庄学论文,在此不作讨论。
三、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
郭象(253—312),字子玄,河南洛阳人。少有才学,雅好《庄》《老》,颇善玄谈,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时人以为王弼之亚。其生平事迹见于《晋书·郭象传》和《世说新语·文学》篇。著有《庄子注》《庄子音》《老子音》《论语隐》等,但只有《庄子注》流传至今。
郭象《庄子注》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庄子》注本。据《世说新语·文学》及相关文献,此前注《庄子》者数十家,除《文选》李善注提到的《七贤音义》外,其中较重要者有崔譔、司马彪、孟氏、向秀等人的《庄子》注本,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郭象《庄子注》的篇目编次,据日本高山寺残抄本《庄子》后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是在司马彪五十二篇本基础上,参考崔、向等人的做法和已出现的二十七八篇的不同版本,“以意去取”,经过认真的辨妄剔杂、删芜集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又在分类编排上略作调整,把部分原属外篇的篇目编入杂篇,从而形成了新的三十三篇本,成为后世通行的定本。在注疏阐释方面,郭象在向秀《庄子注》基础上,袭、创并用,述而广之,被认为“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庄学史上还有一桩“郭象剽窃向秀”的公案,原自《世说新语·文学》和《晋书·郭象传》的记载,兹不详叙。对此,宋明学者几乎都认为郭象有剽窃嫌疑,然自清代开始,学者通过对照向、郭二人的《庄子》注本,就越来越不相信剽窃之说。尤其是当今熊铁基、方勇在参考王叔岷、冯友兰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公案作了进一步审慎详细的辨析,已经得出了《晋书·向秀传》“述而广之”的说法“倒是相当确切”⑦,“应该比较符合实际”⑧的中肯判断和结论,笔者深表赞同。揆诸实际,郭本至少比向本多出五篇,分类更细;郭注虽然不乏与向注雷同者,但更多的是对向注的增损改铸,尤其是对向秀的哲学思想颇有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如由向秀的“自生”“自化”说发展为“独化”论,由向秀的“以儒道为壹”进而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新命题等。后人著述,因袭沿用前人某些成果,这在当时乃至当今本属正常现象,只是郭象未加注明,颇失“规范”,这就难免授人以柄,以致有“剽窃”之嫌和“薄行”之诮。平心而论,的确还是“述而广之”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除了对向注“述而广之”外,郭注还对司马彪、崔譔等数十家旧注作过不少借鉴、批评与修正,更对《庄子》作了许多改造性诠释,借以表达自己的独到见解,还调和了玄学发展中“贵无”和“崇有”等诸多矛盾,综合了前人治《庄子》的思想成果,从而把玄学理论推向最高峰,成为代表魏晋玄学发展创新和庄学研究深化的集成性标志性成果流传后世,广受推崇,影响深远。
郭象作为魏晋庄学的典型代表,他注《庄子》,“是借《庄子》这本书发挥他自己的哲学见解,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⑨,故其《庄子注》中对《庄子》文学的阐释并不突出,但仔细寻绎,尚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对《庄子》“三言”的阐释
《庄子》自谓其行文体例是由“寓言”“重言”“卮言”组成的“三言”体,并对此作了一些解释。除了《庄子》自身的解释外,据现存资料,最早对其作出全面阐释的就是郭象的《庄子注》了。其《寓言注》云:
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连叔之类,皆所借者也。父之誉子,诚多不信,然时有信者,辄以常嫌见疑,故借外论也。己虽信,而怀常嫌者犹不受,寄之彼人则信之,人之听有斯累也……非借外如何?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虽使言不借外,犹十信其七……夫自然有分而是非无主,无主则曼衍矣,谁能定之哉!故旷然无怀,因而任之,所以各终其天年。⑩
其《天下注》又曰:
卮言,不定也。曼衍,无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故以卮器以况至言。而耆艾之谈,体多真实,寄之他人,其理深广,则鸿蒙云将海若之徒是也。
在上述注文中,郭象所谓“十言而九见信”“七见信”的解释,虽被唐人陆德明、成玄英等因袭沿用,但不合庄子文意;至宋人林希逸对此作了纠正,重新解释为“十居其九”“十居其七”,这才切合庄意,被学界普遍接受。然郭象上述其他解说,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尤其是他认为“寓言”乃“寄之他人”之言,“重言”乃借重“耆艾”之言,“卮言”乃“因物随变,唯彼之从”而合于“自然之分”的“至言”,皆十分中肯,一直为后人所认可。同时,他在注文中对庄子的“寓言”“寄言”等也有所指认。特别是他首次把“卮言”的“卮”和“满则倾,空则仰”的酒器“卮”联系起来,谓《庄子》是“以卮器以况至言”,这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庄子》“三言”中最难以捉摸的“卮言”来说,无异于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诚可谓发皇开窍,对千百年来的治《庄子》者和广大读者有莫大的启发!
诚然,郭象关于“三言”的见解,还只是注《庄子》过程中针对《庄子》文本字句而言的,未必具有文学意识或从文学角度进行思考和阐释。然而无论如何,这对于后人理解《庄子》的行文体例和文学特色,显然不无启示和帮助。
2.“寄言以出意”新论的提出及其文学意义
在阐释“三言”的同时,郭象还上承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从《庄子》一书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寄言以出意”的新论。他在《山木注》中说:“夫庄子推平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他认为庄子是运用“三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寄托自己的宏旨深意。既然庄子是“寄言以出意”,那么读《庄子》解《庄子》者就要略“言”而弘“意”。故其《逍遥游注》云:“鲲鹏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可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则阳注》又云:“求道于言意之表则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这正是强调读《庄子》解《庄子》宜“遗其所寄(言)”而“要其会归(意)”,求其“言”外之“意”,得“意”而忘“言”。
郭象“寄言以出意”的思想,是对《庄子》言意关系的深化认识。正因为他有此深刻认识,又如法炮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庄学研究及其阐释实践中,才诞生了一部同样具有“寄言以出意”特色的极富创造性的《庄子注》。难怪有人这样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郭象提出“寄言以出意”新论的意义,当然还不限于此。尽管他主要着眼于对《庄子》言意关系及其表达方式或阐道方式的发现、总结和揭示,并用于自身的《庄子》阐释实践,未必着意于《庄子》文学,但却有助于对《庄子》之文学表现手法及文学特色的理解和认识,后世的咏庄作品乃至其他方面的文学创作,也往往受到庄周、郭象“寄言以出意”思想和做法的启发与影响。
3.对《庄子》话语风格及文学地位的评论
郭象在其《庄子序》中首先指出:“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虽无会而独应者也。夫应而非会,则虽当无用;言非物事,则虽高不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起者,固有间矣,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尔。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曾设对独遘而游谈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在郭象看来,庄子可以说是知道根本的,即懂得“无心”“无为”这一根本,但是他只是空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言论,即使其与道相应也行不通,所以他的著作不能与儒家经典并列,而可称为诸子百家之冠。可见,郭象为了适应时代需要,是把庄子置于孔子之下和老子等诸子之上的特殊地位上。接下来,郭象对庄学的内容和特色作了概括:
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
这就是说,庄子虽未身体力行“无心”“无为”之道,但是他的话已经说到极致了,这是其他诸子所达不到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云云,实际上是郭象所理解和发挥的庄子思想,姑且不论。在笔者看来,此处最关键的是这两句话:“其言宏绰,其旨玄妙。”它显然是对庄子行文之话语风格的概括和评论,既与《庄子》的思想特色有关,又与《庄子》的文学特色有关,具有重要的文学阐释意义。相应的,郭象所谓“不经而为百家之冠”的评语,也不仅仅是对庄子学术思想的评论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亦可看作是对《庄子》文学成就的评论和定位。还有被称为“庄子后序”的郭象《庄子注·天下》篇后跋语(见日本高山寺《庄子》残抄本)所谓“然庄子闳才命世,诚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更是对《庄子》话语风格和文学特色的高度评价。后世学者论《庄子》行文之奇,谓庄子“辞趣华深,正言若反”,“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尤以文辞陵轹诸子”等,都受其影响,与之一脉相承。
由此看来,郭象的《庄子注》中,还是有一些对《庄子》文学的阐论的。
四、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主的一批名士,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周易》及《老子》《庄子》之道,就某些玄奥深微的问题互相辩难,极力发挥,玄谈风气由此兴起。时人把名士们这种聚集围坐、高谈玄辩、探幽析微、借题发挥的做法称为清谈,这是玄学思潮在生活层面的表现,是魏晋风度最明显的表现和当时士人最突出的行为之一。如《世说新语·文学》所云:“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像这种宾朋满座、清谈玄理的情景,在历史上颇不多见,而当时的名士却热衷此道,乐之不疲,甚至达到废寝忘食、如痴如醉的地步。这种风气进而弥漫于整个士林,并延续到东晋南朝,伴随着玄学衰落而消歇。其谈论的对象,也渐次由以《易经》《老子》为主演变为以《庄子》为主,最后与佛学合流。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即开始以《庄子》《老子》为主,在一起畅谈玄理,批判名教,并且饮酒吟啸,放情肆志,在生活中实践庄老哲学。西晋元康时期,以裴頠、郭象为杰的“中朝名士”,尤以阐发《庄子》为尚,既著文立说,亦雅好清谈。《世说新语·赏誉》称郭象“有俊才,能言老庄”,谓其语议“如悬河写(泻)水,注而不竭”;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说“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到东晋时期,玄学清谈在以王导、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一大批“江左名士”中再度盛行,加之一批名僧的加入,以庄学为主的玄谈进而与佛学交融,又随着佛理化的推进而渐趋衰落。
可以看出,在整个魏晋玄学清谈过程中,《庄子》显然是最重要的谈论对象。和此期的玄学著作一样,玄学清谈中的《庄子》阐释,主要是对《庄子》玄理的阐发,而不是对《庄子》文学的阐释。但可以推想,在魏晋名士的庄学玄谈中,应该是既有精妙的玄理辨析,也少不了优美的语言表达,可惜他们清谈的内容大都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因而难知其详。其中最值得珍视者,当属《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对东晋名僧支遁等玄谈《庄子》的记述了。
支遁(314—366),字道林,俗姓关氏,原籍陈留。家世奉佛,25岁出家,先后在余杭、吴、剡等地寺庙中修行,常与名士交游谈玄,是一位身披袈裟又爱好玄谈的高僧兼名士。据《高僧传》等记载,他曾与刘乐之等谈《庄子·逍遥》篇,又先后与冯太常、王羲之等讨论过《逍遥游》,在玄谈之余,还“退而注《逍遥》篇”。支遁在治《庄子》方面最为人推重的贡献,就是著名的《逍遥论》,其言曰: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鴳。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鴳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
关于《庄子》的逍遥义,此前向秀、郭象认为:“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鴳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郭象《〈逍遥游〉题解》亦云:“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冯怀)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向、郭以为大鹏、斥鴳“任性”“当分”,同为逍遥;支遁则认为鹏“失适于体外”,鴳“有矜伐于心内”,皆有所不足,都不逍遥,只有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才是逍遥。相比而言,支说显然是切合庄子本义的中肯之论,的确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故后世“遂用支理”,直至今天其观点仍为人们普遍称引。而从“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的记载看来,支遁的《逍遥论》,乃是其与名士玄谈《逍遥》之言论的记录,魏晋名士的清谈之言于此可略见一斑。
《世说新语·文学》所载支遁等玄谈《庄子》,其重要者还有以下两条:
王逸少(王羲之)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孙绰)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支道林、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否,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初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言,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自佳耳。”
王羲之自恃才高气隽,一向蔑视支遁,后来支遁前往王之居所谈论《逍遥》,作数千言,令王深深折服。名士雅集谈论《渔父》,支遁先通(解说义理使之畅通),作七百多语,众咸称善;谢安先诘难,接着自叙其意,作万余言,四座莫不服膺。这两次玄谈的主旨,自然是对《庄子》哲理的深度发掘和充分阐说,而非专门讨论《庄子》文学;对支遁等人的玄谈之言,也无具体而微的详细记录,但从“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以及“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的概括叙述略加推想,其所用话语也一定是文学色彩很强的妙语美言。此外,《世说新语·文学》所载殷浩的清谈亦可佐证:“谢镇西(尚)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此条记载虽未点明其清谈的内容,想来必与《庄子》有关,殷作数百语,“既有佳致”是指其义理,“兼辞条丰蔚”则显指其言辞,两相结合,竟能使人“动心骇听”,“流汗交面”!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庄学清谈,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可言的,和前述阮籍《达庄论》类似,也可算作对《庄子》的文学阐释。这种在特定场合即兴发挥的精美玄谈,既可与魏晋庄学著作中的有关论述相互印证,更可与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庄子》接受与阐释相互辉映,共同构成《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的一道奇丽景观。
总观魏晋玄学中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阐释为主体,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有的还在玄虚的理论层面上,并非十分突出,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十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②④⑤⑧方勇:《庄子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7、300、334、381、337、299页。③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⑥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⑦熊铁基等:《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129页。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4页。⑩本文所引郭象《庄子注》的文字,皆出自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佛教高僧慧觉禅师语,又见归有光《南华真经评注》冯梦祯序。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出自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马叙伦:《庄子义证·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0页。本文所引《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的文字,皆出自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
责任编辑:行健
The Zhuang Zi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Metaphysics
Liu Shengliang
Abstract:The Zhuang Zi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metaphysics, which represents the whole studies of Zhuang Zi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t mainly includes Wang Bi′s idea about speech and meaning of the debate, Ruan Ji′s "Explain Zhuang Zi with Literature" in Da Zhuang Theory,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in Guo Xiang′s Annotations on Zhuang Zi and idle talk of metaphysics. In this period, studies of Zhuang Zi are essentially to interpret its philosophy,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is minor, collateral and limited, but in the Zhuang Zi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history, it has unique an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Wei and Jin Dynasties′ metaphysics; studies of Zhuang Zi; explain Zhuang Zi with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