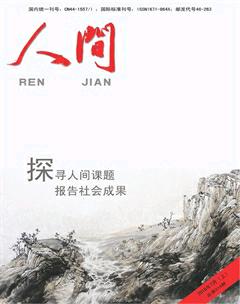“救救孩子”
——浅析张冲“问题”困境的生成
赵艳艳(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00)
“救救孩子”
——浅析张冲“问题”困境的生成
赵艳艳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400000)
摘要:《少年张冲六章》通过父母、老师、同学、亲戚、“课文”和“他”自己六个叙事角度讲述了一个原本单纯美好的儿童如何变成一个“问题”少年的故事。少年张冲的成长问题让我们为之遗憾,故事发人深省,让我们不禁发出疑问:到底是谁将一个白纸般的儿童塑造成了一个父母不认的孩子,并最终进入少年劳教所的“问题”少年。本文旨在分析少年张冲“问题”困境的生成原因,包括父母、老师、同学和个人方面的显在生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寻找这些显在原因背后潜在的文化原因与现实困境。
关键词:《少年张冲六章》;“唯有读书高”;教材文化解读;教育现实
鲁迅在《狂人日记》一文所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在近百年之后得到了作家杨争光的响应。2010年三月,杨争光发表《少年张冲六章》,
《少年张冲六章》给关注教育的人带来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如今六年已过,重新阅读《少年张冲六章》,我们仍然有必要来重新思考教育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问题少年张冲的成长,但实际上在中国教育中张冲不过是沧海一粟,张冲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试问哪个受过教育的人在自己班级中找不出几个张冲的存在?既然有如此之多的问题少年存在,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个像张冲一样曾经拥有“亲爱的时光”的儿童,长大后会逐渐变成一个个问题少年?
一、张冲“问题”困境的显在生成原因
(一)家庭影响。
家庭的影响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父母行为的直接影响,一是家庭作为一个场域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氛围熏陶,也就是观念和精神价值的建设。
在“课文”一章中,作者选取了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部分文章,并通过老师,父亲张红旗以及小张冲三方面不同理解,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父母对孩子思想观念建设的引导作用,家庭场域对孩子精神价值建构的熏陶。
“课文”一章中有一篇名为“三个儿子”的二年级课文,讲述了三个妈妈对自己儿子的评价,一个说自己儿子“聪明有力气”会翻跟头,一个赞赏自己儿子会唱歌,最后一个妈妈什么也没说。但当三个儿子看到自己妈妈在提水时,只有最后那个妈妈的儿子去帮妈妈提水。这篇课文的立意是要告诉孩子们对父母孝顺关爱才是最值得称赞的。但张红旗对此解读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会翻跟头、会唱歌、帮妈妈提水都不是好儿子应该做的事情。“真正的好儿子一定乖乖呆在家里做作业”①,这就是张红旗的好儿子观。
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张红旗的这种价值观引导,给张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无名的罪感。这种压力与罪感蓄积终会爆发,使张冲走向父母的对立面,出现厌学,反叛等一系列问题。
(二)学校因素。
如果说家庭是第一个文化熏陶的场所,那么学校就是另外一个对儿童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的所在。张冲的第一个老师上官英文是一个民办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文体活动,文革结束后就成为了一位乡村音乐教师,亦农亦教。这样的老师的教学水平和育人水平可想而知,他对学生没有耐心和爱心。书中详细讲述了张冲第一次挨抽是因为张冲问上官英文“你叫英文为什么不教英语教唱歌呢”②。作为一个老师,他简单粗暴处理学生问题的方式,无疑是促使张冲走向反面的重要因素。
作为张冲在学校的另一个主要关系群体的同学们,对张冲们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文昭们的近墨者黑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班级中虽然无声但影响颇大的众多同学,他们或许充当着张冲某些哗众取宠行为的助兴者和观看者,或许表现着对于“问题”少年的冷漠与排斥。这种影响是一种无形的,温柔的暴力。
“几个同学”一章讲到张冲在上课期间与袁老师展开的一段无聊的,哗众取宠的对话。从“学生们哄一声笑了”③,到“学生们又一次哄笑了”④,再到“学生们笑得已经不亦乐乎了”⑤,这些看似平常的反应实际上正是张冲想要与老师纠缠并言说此番无聊对话的原因之一。他的目的是得到同学关注,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成为班级中的焦点。他用蛇皮袋装上自己所有教科书在校园穿梭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博得关注,他最后不再背书也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没什么意思了”,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了。他的耳洞、染发、奇装异服和特立独行都是为了受到关注。
在种种表演过程中,其他同学充当的就是观众,是张冲表演的起哄者和推动者,是鲁迅笔下的看客。其他同学在张冲们标新立异的行为挑动感官神经时做出的哄笑和关注之中,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把张冲们推向问题深渊的参与者。
(三)个人原因。
纵使父母、老师、同学对张冲“问题”困境产生种种影响,但张冲个人的缺乏毅力、自律能力和叛逆、顽劣性才是是他“问题”困境的内在主要原因。
在我看来,张冲是一个缺乏毅力,缺乏自律能力的人。他在经历过一两次的成绩不理想之后,父母的责备之后,就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想不出问题之后就开始看着天空发呆,经常只是做出一副学习的空样子而已。如果说他第一次爱抽的原因让人同情,那他之后的遭遇多少就是他的咎由自取了。和文昭一起窥探上官英文和英语老师的私人生活,在上官英文老师的屋外挖洞让同学们排便使老师屋子熏臭难闻,不上课却掏鸟窝……如此种种,张冲的顽劣和捣乱可见一斑。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并非全部都是如上官英文一样的老师,也存在着像李勤勤这样的好老师。她下决心要帮助张冲,找他谈话交流,并为了回答一个他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百思不得其解后的自责和无助,都是一个优秀教师的品质。可张冲却自暴自弃,并不配合老师的工作。
二、张冲“问题”困境生成的文化原因
文化具有历史连续性,传统文化对教育也具有重要影响。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一文中讲到,“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⑥。在分析家庭父母,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因素之后,我们还应该思考一点文化上的深层原因。
(一)“唯有读书高”的成才观念。
读书入世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中,一直被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要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教育观念。从古代进入仕途的科举制到今天选拔人才的高考,“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育价值观念,一直在中国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主流方式,即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只有读书考上大学,才能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光耀门楣。
从文化角度来说,众多张红旗们所奉行的教育方式中潜藏的是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意识。可是这种教育观念产生的效果并不总会如其所愿。这种把读书作为评价一个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的教育观念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教育理念。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传统教育观念塑造的存在,是“唯有读书高”塑造的一个只会读书却无法生存的形象。鲁迅曾说:“看见了讲到‘孔乙已’,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⑦。在现代教育中,我们更应该做到“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
单一过度的病态的读书考大学的成功期望加重了孩子作为受教育者的心理负担。当这种负担过重时,孩子就会像弹簧反弹一样,开始强大的叛逆心理。
张冲在上学之初,如其他人一样是很爱学习的,他懂得父亲张红旗带他去见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陈光升,是想让他像陈光升一样读书成人,明白父母的望子成龙之心。他也曾在父亲为他改造的石桌前努力学习,思考问题,也曾在别人欢度春节时候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学习,但是这些并没有换来与付出成正比的回报。所谓的回报在张红旗看来就是一张成绩单,这张成绩单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有简简单单的分数,这个符号一样的分数中并没有张冲在一整个寒假中的努力。张红旗并没有想到张冲是付出努力的,他只是觉得这个分数就是张冲不好好学习的结果。他没有想到张冲到底适不适合体制教育,适不适合像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文化课知识的教育,于是,他就用牛绳将张冲像牛一样绑起来,并向邻里展示。
在父母这种过度期望之中,孩子走向了父母的对立面,开始了反叛。在“说讨厌父母”一节中,张冲认为父母经常表现出来的“只要你好好念书给咱考上大学我们累死也值”⑧的压迫与希望是“病态”的,这让他觉得自己“像个罪人一样”。有些学生甚至为了减轻折磨,用烟头烫胳膊。这种行为是一种自虐,是一种因对父母产生很大的自责内疚与罪感之后的对自我肉体的折磨。
(二)语文教材文化的解读。
文化作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气息,潜移默化地熏陶并建设着我们的价值观和精神信念。语文课作为小学、初中和高中的重要课程,对于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语言文字,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的同时,更承载着文化价值和精神的解构与建构。语文教材,作为语文教学活动中最直接的语言文字材料,更是建设青少年精神文化的主要参与者。对于语文教材的解读也是价值观的建构过程。
“课文”一章中的“爱爸爸妈妈”这篇课文的编排者和讲解的老师让孩子学会对父母表达爱的美好立意,到了张冲这里却变了味。张冲认真完成家庭作业,就想像课文里的田田一样帮爸爸妈妈做些事情,饭后帮妈妈端碗,结果妈妈却说“放下放下”,帮爸爸端热水,爸爸没接水也没像课文里田田的爸爸表扬他,反而像看怪物一样地看他,认为整天想着端茶抹桌子念不成书。在这里,张冲的父母将课文编排者和讲解者的美好立意解构掉了,将课文所要传达的爱的文化和精神扼杀了。同时,在张冲的精神价值体系中建构起来的是一种缺少爱的价值观,所以,在张冲父母看报纸,抹桌子时候,张冲就不再对此有任何反应。这些微小的生活细节,慢慢累计起来对张冲的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他日后对父母冷漠并走向问题少年的原因之一。
在语文教材的文化解构中还存在着一种误读,历来对于《丑小鸭》的解读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之上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事实是,本来就是天鹅蛋,而不是鸭蛋。也许你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美好的谎言,但建立在真实之上的故事更加美丽动人,我们不能因为真实比谎言悲伤和丑陋就拒绝,更何况真实比谎言要美丽。“简单地美化实践,对于教育理想和教育实践,都是一种损害”⑨。
三、现实的困境
(一)个人现实困境。
除了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之外,社会现实的规训更是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对于张冲成长产生影响的父母、老师和同学都在社会大环境中自我挣扎着,所有的挣扎对于张冲和其他青少年的教育成长都产生着影响。文中谈到“教育的现实也就是社会的现实,学校的现实,学生的现实,也是每一个学生家长的现实”⑩。所有的社会、学校、学生的现实构成了教育的现实。
张冲的父母希望自己能像陈大一样受到别人的羡慕,希望张冲不要像他自己一样继续做农民,能够像陈光升一样离开乡村进入城镇,获得优越的生活条件,不再为生活挣扎。如此现实的考虑,他才会说出只要张冲“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就算“累死也值”的话。在父母为了子女上学付出血泪债之后,孩子就必须以上大学作为回报这累累之债的唯一手段和方式,如果没有实现这一还债方式,那孩子就会担负着巨大的压力和罪感,这也是今天很多学生高考失利选择轻生的原因之一。这也是父母的现实所带来的子女的现实。
老师作为一个社会职业者,一个社会存在,也有无法满足自己生活的现实问题。李勤勤在对待要张冲留级的问题上是犹豫的态度。一方面她的良心和职业道德不允许她这样做。另一方面来自学校和校长的压力,升学率所带来的利益,以及生存的考虑,都促使她不得不做出张冲留级的选择。作为一个离婚的女性,一个单亲妈妈,一个照顾卧床父亲的女儿,她也有自己的现实困难,在生存面前,选择让张冲留级。李勤勤作为一个为解决张冲提出的“祖国”问题而辛勤思考答案,且因找不到答案而饱受内心折磨但最终勇敢面对学生的好老师,选择让张冲留级,很大程度上是受现实生存的逼迫。
(二)教育现实困境。
《少年张冲六章》是以一位名为“张冲”的乡村少年从一个健康的儿童变成一个“少年犯”的真实故事为原型的。《少年张冲六章》也向我们呈现出乡村教育有别于城市教育的特殊困境。
何为乡村教育?在刘铁芳看来,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两大问题。如果重心在“乡村”二字,那么乡村教育这个概念就只表现为与城市教育的差异性,诸如教学条件,师资力量、升学率、失学率等等一系列乡村教育之不如城市教育的地方。如果重视“教育”二字,那么我们就应该从教育自身出发,切切实实以教育本身出发考虑乡村的教育观念和模式。而不是把乡村看为城市教育的另一个实施场所,从教材内容、教学资源、到教育理念与教育目标无一例外,丝毫不改变的将城市教育模式照搬到乡村共同体。
第一,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客观条件上的差距,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是一个最基本的教育现实困境。“按国家义务教育的规定,小学三年级就要学英语,事实上,城市可以做到,农村则不行,为啥?没人教”11,这种教师数量和素质的欠缺是乡村教育常见的困境。乡村学校有很多民办教师,书中谈及的“文革”中的文艺活动者上官英文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一名小学音乐老师,这类民办教师的教学水平整体上无法与城市学校教师相比。“民办教师也是现实的需要”,民办教师虽然教学水平没有城市教师那么优秀,但他们的态度比较认真负责,另外也只有他们愿意留在乡村坚守教师岗位。另一方面民办教师的自身困境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书中说到在2000年时民办教师的工资“每月三十块,最高时一百五十块,不到公办教师的三分之一”12。他们的转正又是很困难的。
第二,城市价值取向的单一教育模式是乡村教育的另一困境。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是乡村少年厌学和走向“问题”的原因之一。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乡村传统风俗,乡村道德构成的乡村文化场域并没有多少进入到教育价值体系中,乡村少年很难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独特乡村审美精神价值的培育。
从书中得知,张冲帮助姨夫王树国的苹果增产,他喜欢看培育苹果的小册子,如果在乡村教育中存在一些此类教育,发现他的兴趣,或许他不至于变成少年犯,或许他拥有另外一种健康的人生。
我们不是要切断乡村与城市的联系,也不是彻底反对乡村教育的现代化追求,而是应该在现代化教育的过程中给予乡村教育中乡村价值的重视。
四、结语
张冲“问题”困境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盘根错节的过程,我们需要抽丝剥茧地去正视各方面的问题。父母、老师,同学及其自身的弱点是少年张冲的“问题”困境生成的显在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唯有读书高”的教育观念,实际语文教学活动中对语文教材的解读与教材编排立意的错位,是张冲问题“困境”生成的文化因素。隐含在教育背后的社会现实对于教育实践者与参与者的规训造成的个人生存现实困境,以及对教育本身的限制造成的教育现实,生成了张冲“问题”困境的现实因素。
教育依然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始终去关注并力求解决。这是作家杨争光写作的初衷与目的,也是本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参考文献:
[1]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2]鲁迅.鲁迅论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08
[3]王春林.一部忧愤深广的社会问题小说——评杨争光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J].小说评论,2010-07-02(4):82-88.
[4]刘铁芳.乡村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5]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文化教育的缺失[J].书屋,2006-10-06:45-49.
[6]刘铁芳.文化破碎中的乡村教育[J].天涯,2007-05-08:22-29.
注释:
①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97.
②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1.
③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26.
④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30.
⑤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30.
⑥鲁迅.鲁迅论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08:113.
⑦鲁迅.鲁迅论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08:113.
⑧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16.
⑨刘铁芳教育生活的永恒期待[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12.
⑩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69.
⑪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4.
⑫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3.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24-03
作者简介:赵艳艳(1989-),女,满族,河北承德,硕士研究生,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