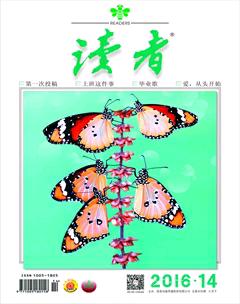父亲的严厉
莫言
20世纪60年代,父亲40多岁,正是脾气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在我们兄弟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板着脸。不管我们是处于怎样狂妄喜悦的状态,只要被父亲的目光一扫,顿时就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大气也不敢再出一声了。
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村里的人都不解地问:“你们弟兄几个怕你们的爹怎么怕成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为什么怕父亲怕成这个样子?父亲打我们吗?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骂我们吗?也不,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他既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那你们为什么那样怕他呢?”是啊,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怕父亲。我们弟兄长大成人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但谁也说不清楚。其实,不但我们弟兄几个怕父亲,连我们的那些姑姑、婶婶也怕我父亲。我姑姑说,她们在一起说笑时,只要听到我父亲咳嗽一声,便都噤声敛容。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瘆人毛。”
如今,我父亲已经80岁,是村子里最慈祥和善的老人,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没有帮助带,但我二哥的女儿、儿子,我的女儿,都是在我父亲的背上长大的。我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见了爷爷,还要钻到他怀里撒娇。她能想象出当年的爷爷咳嗽一声,就能让爸爸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吗?
后来,母亲私下里对我们兄弟说:“你爹早就后悔了,说那些年搞阶级斗争,咱家是中农,是人家贫下中农的团结对象,他在外边混事,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边闯了祸,所以对你们没个好脸。”母亲当然没说父亲要我们原谅的话,但我们听出了这个意思。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家族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李中一摘自春风文艺出版社《写给父亲的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