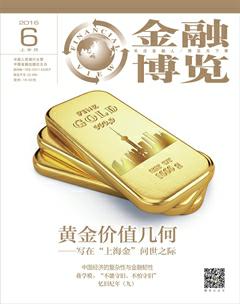市场冲破围墙,古典城市格局的解体
龙登高
中国古典城市的坊市制是由一道道围墙拼接而成——众多封闭的居民区及与之隔离的独立市场区。这些围墙在唐宋时逐渐倒塌了,坊市制城区格局随之解体。
封闭与隔离:
古典城市的坊市制
古典城市中的市场大多是封闭的,以围墙将同样封闭的各居民区、行政区相隔离。城市通常设有成片的手工业作坊和专门市场,大城市还有若干个市场。西汉长安形成东、西两市制度,西市由6个市合组而成,东市由3个市合成,每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各包括4个里,九市共36个里。1971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东汉墓葬壁画上,绘上谷郡宁县县城图,有城墙、城门、街道、市场、衙署等,其中有一个四合大院,中间榜题“宁市中”,就是县市。市场的繁荣,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状况的标准。
一般而言,县市设几道市门(多为4道门),供车马人流出入。黎明开启市门时,常出现《史记·孟尝君列传》所谓“侧肩争门而入”的拥挤情景。交易时市场内甚为热闹。工商业者居住其中及附近,故《管子·大匡》谓:“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也有城市,市不在城墙之内,商贾富人居于城外,市场活动在城外进行。古代城市由内城外郭组成,城的面积一般是有限的,而郭则可以很广阔。
隧是市内通道,能容纳车马通行,《史记·信陵君列传》有“公子引车入市”的事实。如果市场繁忙,很容易发生堵塞的现象。《西都赋》形容长安市场“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店肆排列于隧的两旁,为商贾居住与营业之所,称“市列”、“列肆”。
市的开业时间都在白天,因此,《风俗通》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夜间交易,需要增加照明费用,也不便于官府管理,因此一般没有夜市。直到唐宋之时,交换频繁,并且突破了政府的管制,夜市才得以兴起。
市内商贾不列入一般户籍,而别列“市籍”,与通常的编户齐民相区分。没有市籍者不准在市内营业,《汉书·尹赏传》有搜捕“无市籍商贩作务”的记载。市籍身份之人,不得入宦,不得名田,甚至不得操刀、乘骑马,并且“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身有市籍,地位低下,不仅本人,而且影响及后世几代。
有市籍者,不管其营业好坏,都必须定期交纳市租,拖欠者将受处罚。市场管理体制自成体系。令署,即市场行政管理机构,设于市楼,悬挂旌旗。市吏管理市场秩序,负责督巡市场,“吏巡之不谨,皆有罪”。市场实行价格管制,商品明码标价。
上述规范的市场,多出自长安、洛阳两个最大城市。对于其他城市而言,这可能更多的是政府有关城市建制的一种制度,而不一定是实际情形。位于城外的市场,就很难做到规范。即使当时全国五大城市之一的成都,直到公元前311年才修成初具规模的城墙,市场及其市门、店肆,经修整才与咸阳的制度相同。
秩序严明的坊市制格局延续到唐中叶。《唐会要》、《唐六典》有关唐令对城市市场做了规定。
唐代坊市制市场及其管理制度深刻反映了当时市场体制的性质,这种市场是从属于政治的,是为各级官府服务的,所以官府对产品质量的管理较为严格。
与此相关,唐后期出现宫市。出自皇宫的中官宦者,在长安两市等处强买物品。他们口含敕命,以宫中多余的次品衣服、不成尺寸的绢帛,高估价值,作为酬价,强行贱取买卖,并且强迫卖者倾车乘,罄辇驴,送至禁中,少有不甘,有殴致血流者。白居易《卖炭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迈的小商贩,他的悲惨遭遇,正是白望宫使的罪证。
隋唐坊市制市场,相对于城市经济规模来说,是很有限的。市的面积在城市中比例很小,长安坊市总110区,才有东西2市;洛阳126坊,3个市才占2坊之地。
隋唐都城,高墙森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为种菜畦”的整齐城市规划,正是政治控制经济与市场的产物。《新中国考古收获》分析:从长安整个城市中宫殿区所占的地位、封闭式的坊制和受严格管理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种城市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城市有很大差异。统治者控制着整个城市,是贵族、官僚、地主的集居之地。工商业虽然较前代获得了发展,有了固定的市场,但在整个城市中却并不占主要地位,还受着严格的控制。但是市场关系是无孔不入的,它的壮大必将冲决旧的秩序。中唐以后,市场关系敲开了沉重的城门和高大的城墙,打破了规整划一的坊市分隔制度,导致了唐宋时期深刻的城市革命,出现了中国城市史上最重要的质的飞跃。
唐中后期坊市制开始突破
城市市场关系的不断扩大,使坊市制市场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中晚唐不少城市开始新建、扩建市场。唐贞元时,成都于万里桥隔江创置新南市,很快便人逾万户,交易繁荣,为一时之盛。元和中,荆州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政府填平城郊方圆十里的后湖,辟为新城区和交易市场。同时,市场交易时间延长,逐渐突破坊市制的交易时间的规定。市与坊,都设有门,击鼓启闭,但后来,“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而未闭”。各地普遍出现夜市,扬州夜市最为文人所乐道,如徐凝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夜市的记载,在成都、杭州、汴州、楚州、梓州、象州、湖州等大中小城市都有出现。
市场的空间形态,也逐渐改变。有的城市,“市”内交易增多,于是出现增设店铺或破墙开店等现象。如两京各市,纷纷在正铺前加造偏铺以增加营业面积,甚至地方政府出于牟利而破坏旧制度,如天宝九年(750年)京畿“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更多的现象则是在居民区坊巷内,逐渐出现买卖行为,进而开设商业店铺。洛阳的许多里坊街巷内,都出现了商业店肆。
在长安,商业同样发展到里坊之中,仅《两京城坊考》中有旅馆的坊区就有永崇坊、宣平坊、道政坊、布政坊、崇贤坊、延福坊、长乐坊、新昌坊八坊。贞元末年,长安市场已不限于东西两市区,有的坊区还成为热闹的商业区,被称为“要闹坊”,这些地区遂成为宫市掠夺的必至之地。
这种变化一开始是严行禁止的,隋文帝巡幸路过汴州治所,这是一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而杨坚从心底里“恶其殷盛”,下令凡有向街开门者,封闭之。后来渐渐多了,也就熟视无睹,为人所认可。
坊内已经存在或潜在的市场因素,在坊外及城外市场的催发与刺激下,发育膨胀起来。坊内的商品,迫切需要在市场的风浪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实现。于是,在各坊内的小街曲巷,终被一个个店肆所占领,居民区与市场也就浑然一体了。坊市制的空间形态就这样消失于城市历史舞台。
商品流通是没有政治边界的,城市的高墙深池阻止不了交易的扩大,市场同时越过城墙,向城郊扩张。唐中后期城郊草市的兴起,进一步冲击着坊市制市场体系。
附郭草市从一开始就是在官府控制之外兴起的,为城市市场注入了新的血液。城市的进一步扩展,促进了市场性质的改变。大中七年,“废州县市印”标志着官府控制城市市场的结束。
宋代坊市制的终结
中唐以来中国城市市场发生的深刻革命,至宋代基本完成,从此开启了城市市场发展的新纪元。
城市新兴交易街市的形成。城市市场空间布局发生根本改变,市场交易从固定的商业区“市”渗透到居民区“坊”,渗透到城墙内的每一个角落,并扩展至城墙之外。城市布局的变化不仅削弱了城市的封闭及城乡对立,为商人、市民、农民等的交易扩展了空间,而且使市区得以不断扩大,这是城内商业区扩大与人口不断增多造成的。
草市是城乡交换的产物,附郭草市受到农民和城里人的欢迎。在城市,买卖行为必须交纳交易税,农民的细小交换难以应付,即使离城不远的农民也尽量避免入城买卖,宁愿在城门之外进行,正如陆游《鹊桥仙》词有云“卖鱼生怕近城门”。随着城市市场活动日益溢出城墙,附郭草市被纳入城市市场之中。因此宋代展筑外城的现象普遍出现。全国各地“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
各级治所附郭草市人口增加,市场发展迅速。草市市场的发育,使之与城内市场的区别逐渐消失,这体现于附郭被纳入城市建置之中。不少附郭草市,改变了以乡、都、里为体系的乡村管辖制度,并入以坊、厢管辖的城市体例。这在大城市尤为突出。附郭草市之名逐渐为厢所代替,从而,城乡分界线不复以城垣、沟壕为标志,而代之以坊厢与村落的交界。(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