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院二宝
姬中宪
西院二宝
姬中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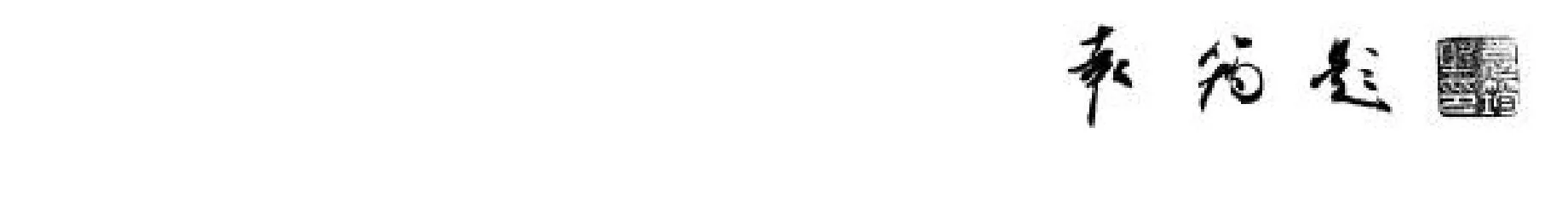
1
向素云个头矮,站着不起眼,坐下去几乎要消失;面貌倒是凶,一说话牙齿就漏气,气里带出些东西,医学上称飞沫。医院负责招募义工的是一位年轻女社工,她和向素云对了几句话,就说:向阿姨,你就别在咨询台了,去科室吧,你想去哪个科室?向素云脱口而出:小儿科!
向素云虽然个子小,年轻时却是开“龙门吊”的,就是码头上、造船厂里,轨道架在空中的那种桥式起重机。45岁那年,厂子搬到嘉定去,她家在浦东,早晨五点就要出门,骑自行车,转公交,换轮渡,再转公交,折腾三个小时才能到。她去了几次,就不高兴去了。她心脏本来不好,而且她就一个女儿,拼什么拼?她办了早退,去小区附近一家糖厂包糖,挣够自己的饭钱就下班,下班的时候,兜里装着没达标的糖块的边角料,回去哄一家老小开心。她有一家老小需要哄,她的母亲,年轻时胃疼,听人讲抽烟治胃疼,就学着抽烟,结果从18岁抽到今年91岁,胃没抽好,肺也坏了,现在整天躺在床上哼哼。除了照顾母亲,向素云还要照顾外婆和外孙。2010年外婆去世前,她家一度五世同堂。
如果不算她那个不学无术的母亲,向素云家其实是典型的“学习型家庭”,一家子都好钻研,做事也认真。她父亲自学财会,做了三十年会计,没出过一分钱差错,厂里给她父亲颁布了财会荣誉证书,至今还在墙上高挂着,激励着一家五代人。她继承了父亲的认真好学,年轻时学裁剪,自己做衣服,直到现在,她还常穿着一些造型稀缺的衣服来医院,材质挺好,样式却不入流,看不出什么品牌,知情人透露:是她剪了女儿不穿的衣服,自己缝的。
因为认真好学,她看不上不认真不好学的男人,结果嫁了一个比她还认真好学的丈夫。丈夫是学机械制图的,又对电器感兴趣,下了班就钻进屋里,把一个收音机拆成一床零配件。1994四年丈夫第一次接触电脑,立刻被吸引,在阁楼里鼓捣了几个月,竟组装出一台电脑,跟真的似的。一台还不够,又照方抓药,组装出另外四台,送给四家亲戚,带领全家人率先进入了办公自动化。丈夫还自学医学,买回家一大本《人体解剖学》,墙上贴着皮开肉绽的人体图,每天对着图练,也不知道练好了给谁用。那时候上海二医大的学生到工厂来学工学农,向素云所在的厂搞工宣队,也要去二医大,她就跟着一起去,人体器官标本室里没人敢进,只有她敢,她把那些瓶瓶罐罐里的恐怖器官端详个遍,还做了笔记,回来交给丈夫,像一对偷师学艺的野郎中。他们不但自学,还学以致用,拿自家人开刀,直到现在,她还把女儿的健康和茁壮成长归功于他们夫妻俩的自学成才——女儿直到工作后第六年才因为生孩子第一次住院,第一次挂盐水。
不过,向素云自认为她最擅长的领域还是教育,尤其早教。纵观其大半生,她好像一直在带孩子,带大自己的,又带别人的,带完一轮又一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她收到宜兴表弟的来信,信上说《解放日报》登了,儿童六岁半就能读书了,想让儿子来上海读书,让向素云帮忙报名。后面附了表弟夫妻的证件和儿子的出生证。向素云去打听了,七月十五日报名截止,还有几天时间,赶紧拍电报回去,让表弟火速带儿子来上海。表弟来了,向素云带着他们父子走了卢湾区的五所学校,没一所学校要他。他儿子虽然六岁半,但自小在田里野惯了,没人教文化,到现在只会举着两只手,从一数到十,而且只能从左往右数,倒过来不会。向素云向学校求情,学校方面说:来也行,能通过我们的考试就行。
向素云借来教材书,熬了一个通宵,把整本书的知识点捞出来,记在小本子上,第二天起,她开始手把手教孩子。有一个邻居在淮海路中学当老师,她向邻居借来很多试卷,让孩子做,一天一张数学卷子,一张语文卷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愣是把孩子从一个纯文盲教得认了字、识了数。学校专门为这孩子组织一次考试,就在教导主任办公室里考。向素云等在办公室外面,比孩子爹妈还紧张。考试结束,主任出来,向素云迎上去,还没问,人家先笑了,说:行的,你家孩子聪明的,语文93,数学97,来吧!
向素云却来了劲,非要看数学卷子,说:语文93就算了,数学怎么会97的,哪里给扣掉3分?人家让她看了,结果是因为试卷是油印的,一个小数加一个大数,中间加号少印一竖,变成减号,孩子就傻了:小数减大数,怎么减?姑姑没教啊,纠结到最后也没减出来,扣了3分。
向素云从此出了名,她用一个多月时间,补足了一个乡下孩子的全部学前教育,创造了教育界的奇迹。她逢人就讲:要不是那一竖,数学满分!
2
向素云初做义工,是在政府下面的一个单位。她老来无事,一身绝学无处施展,又怕不接触社会,学习跟不上,就跟着朋友来这单位做义工,一周来一天,帮人家理理材料,还算轻松。但是年底,因为要评一个先进,里面人闹起来,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向素云就不高兴去了。另一位钟阿姨给她打电话,说:跟我去医院做义工吧,医院里好白相。
向素云说:医院有啥白相的?我不喜欢医院,每次回来,要从上洗到下,麻烦吧?我家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家里老的老小的小。
钟阿姨说:哪里有你讲的这样可怕,你陪我去一天,不好你就回来。
向素云于是去了医院,第一天就逃回来。钟阿姨电话追过来,说:好好的怎么说跑就跑了?
向素云说:我是开过两次刀的人了,我站在那里,手扶了下后面的玻璃,垫了一下腰,他们就说我,哎哟你怎么这样站?这样站难看吧?我说我本来就是来做义工的,累了乏了,就是坐下来坐一会儿也没关系的,干嘛这样说我,我不去了。而且你说,站在那里像个木头牌子,人来人往都看你,难受吧?
钟阿姨说:你也真是的,就是说了你一句嘛,而且你穿了这身衣服,就代表医院形象,要站有站相嘛,他们其实人蛮好的,因为和你不熟才这样,你回来吧,我跟管义工的人说说,看能不能给你换个工作。
向素云说:我不去的,我跟他们说了我死也不去的。
钟阿姨说:又瞎讲,什么叫死也不去,真要死,可不就得去医院吗?好了,我请你去,你看我这张脸好吧?
向素云就笑了,说:我要不是看你的脸,我要不是看你的脸比我的脸好看,才不去。
钟阿姨说:我的脸好看?我的脸还不如那谁的脸好看呢——哎哟我不跟你讲她了,你肯定也看不上这种人的,你知道吧我们院里有故事的人多的来,好白相来,你来了我再讲给你听。
向素云第二次来医院,选了小儿科。社工问她:为什么想去小儿科?她说:我喜欢小孩,我会带小孩,我带过很多小孩,带出来一个硕士生,一个本硕连读,三个本科生,一个明年高考……社工说:小儿科又不是学堂咯。向素云说:我还学过医,我爱人也学医,我们家全是医学书,我们看病都不要来医院的,我女儿比你还大,你相信吧,她就住过一次院,挂过一次盐水,我跟你讲中国人动不动就挂盐水,这不对的,人家美国人……社工说:那好那好,你懂医,又喜欢孩子,那就去小儿科吧。
到了小儿科,向素云算是活过来了。作为医学界和教育界的跨界人才,向素云在这里很有市场。很多人来医院不单为了一纸药方,还想有人说话,尤其想和医生说话,医生一句顶千金,能多说一句就多赚一千块。偏偏医生是世界上最不爱讲话的物种,不看到检验数据不说话,看到也惜字如金,只说报告单上有的,不说报告单上没有的,你想让他多说点,至少多听你说点,他决不容许,喊一声“下一个”,就把你赶出去。这个时候,向素云的作用就显露出来,她专门负责说话,那些医生没空说不便说的话,全让她说了。
她对一个年轻爸爸说:医生跟你讲什么?是不是就讲了两个字,正常?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说正常,是不是?可你呢,觉得什么都不正常,是不是?这就对了,我跟你讲,你自己别想七想八,刚出月子的宝宝,几天不大便也正常的,你只要看两点,一看体重长不长,二看肚皮胀不胀,体重在长,肚皮不胀,就说明正常,说明宝宝吸收好,懂吧?我自己带过八个孩子,我自己的,我女儿的,我舅公家的……
她对一个年轻妈妈说:哭?哭怕什么?不哭才怕!我跟你讲,宝宝不会说话,宝宝所有的需求都是靠哭来表达的,你要学会观察哭,哭分两种,病理性的哭和生理性的哭,饿了困了躺得不舒服了哭,是生理性的哭,这种哭响亮,但你只要满足了他,让他吃饱喝足躺舒服了,他就不哭了,你满足了他,他还哭,你就要观察了,可能是病理性的哭,可能要来医院了,我跟你讲,我带大了八个孩子,我女儿当年哭的最响,结果怎样,我女儿最健康了,我生了我女儿,一直到我女儿再生女儿,她才第一次住院挂盐水,我跟你讲中国人……
一个妈妈从门诊出来,亲孩子,嘴对嘴地亲。她冲过去,对妈妈说:小妹妹,我提个建议,你这样做不对,大人的口腔里面有细菌,小孩子口腔可能没这个细菌,你大人口腔有细菌不生病,你亲到小孩嘴里面小孩就生病!
一个孩子咳嗽,吃了医生开的药,副作用比正作用还明显,爸爸妈妈带孩子来复诊,结果不但开了同样的药,还加了量。她对这对爸妈说:食疗当然好,你们说的生梨冰糖,也可以试试,但我说这不是最好的,我推荐白萝卜,长的白萝卜,又便宜又好。你们买回来,把它洗干净,切成一片一片的,放在水里面,咕嘟咕嘟煮,再加一点点冰糖。不加糖孩子就能吃最好,他不能吃,你就加一点点黄冰糖,记住不要买白的,白的又贵又不好,还是黄冰糖的营养成分好。你们记住,这也是方,咱们祖先不是早就讲了吗,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小儿科等候的时间长,向素云有的是时间来做宣讲和普及。她也看人,觉得对方好沟通的,或者格外焦虑的,病急乱投医的,她会重点关照,主动搭讪。时间长了,有些熟悉的人也会主动来找她,护士台的人被问烦了,也转介给她,说:这个问题你别问我,去问那边义工阿姨,喏,穿蓝马甲站在饮水机旁边和病人家属聊的正开心的那个。
有的人慕名找到她,牵着衣角把她带到消防通道的僻静处,说:阿姨,您在这里时间久,您见识多,您说,哪个医生最好?
向素云说:不能这样讲,哪个医生都好,政府办的,二级甲等大医院,不好的医生能进来?但是呢,每个人都有心情好的时候,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跟你多说几句,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认为你烦,你也有心情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对不对?那怎么让医生心情好?阿姨年纪大了,经的事多了,告诉你办法只有一个:你自己先心情好点,你好了,对他笑了,他哪怕不太好,也会好一点,是不是这个道理?
来人被她说得没话讲,千恩万谢准备随便去挂个号就行了,向素云还不放他走,牵住对方衣袖,说:还有一点,你不要认为年纪大的就好,年纪小的就一定不行,不是这样的,年纪大了他觉得他资格老了,就可以马虎一点,我一看知道了,就可以开药给你,年轻的呢,他自己正在钻研的时候,反倒好的。
来人一边答应,一边就往外走,向素云跟出来,从消防通道到签到台,她一路上还在讲:喏喏喏,要我说,给孩子看病,不在乎医生好不好,在乎你这个做家长的有没有本事,这话怎么讲?阿姨讲给你听:孩子小,不会说,你给他吃了什么你给他做了什么,他什么时候发病的病情怎么样,都得从你嘴里讲出来,你讲对了,医生就对症下药,你不了解不观察,讲得不对,再好的医生也没办法,对不对,对不对,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她差点追进门诊室,非逼着来人连说几句对对对,才放他进去看医生。医生护士们旁边看着她,已经有人嫌她话多了,但更多的人则默认她的话痨。有医生私下里聊她,说有她在,等于消灭了很多潜在的医患纠纷。
她一做四年。四年里,她只请过一天半假。一天是因为父亲去世,半天是因为牙疼。
3
去年冬天的一个中午,向素云正靠在屏风旁打盹,一个爸爸找到她,急急地说:我们昨晚也去了,今天又来了,昨晚他们说不像肠套,今天来了又说肠套,到底是不是肠套?什么叫肠套?是不是就是肠子打结,像绳子一样系上了?
向素云还没醒透,说:你慢点说,一个一个说,什么来了又去了,到底谁说肠套谁说不是肠套?
爸爸说:昨晚我们在附近地段医院看的,人家说不是肠套,叫我们来大点的医院看看,我们来了,这里医生就说是肠套。
向素云说:先给你纠正一下,肠套不是肠子像绳子一样打结,肠子怎么能像绳子呢,绳子实心的,肠子是空的,肠套就是——她拿两根食指比划——上面一截肠子掉下来,把下面一截包住了,你炒股票你知道的,套牢了,这叫肠套。
向素云开始现场坐诊,她问爸爸:吐了吗?吐了。拉了吗?拉了。大便里面有血吗?没血。你把孩子举上去又放下来这样玩过吗?没有。向素云确诊了:不是肠套,肯定不是肠套。
爸爸说:那是怎么回事?
向素云掂量一下,说:吃了凉的东西,是不是?
爸爸拍大腿:对了!昨晚给他吃了西瓜,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
向素云说:你这样不是害孩子吗,十一月了,吃冰西瓜?
爸爸不吭声了,又说:您太厉害了,您怎么知道的?
向素云说:刚才问你那些情况,基本断定不是肠套了,然后你一开口跟我讲话,我断定你是上海人,上海人一般不会吃坏,因为上海人比较讲卫生,我不是看不起外地人啊,但外地人有个习惯就是不大讲卫生,上海人不会,所以我断定你是吃了凉的东西。
爸爸说:那医生怎么说是肠套?
向素云说:医生肯定看错了,你去跟医生——要么我去跟医生讲!
爸爸说:那不要,已经很麻烦您了,我去。
爸爸去了,一去不回。过几天,医院的人来了,找向素云谈话,先是肯定和感谢她的贡献,然后就说到正题,说:义工的职责呢,招募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的,还是辅助和引导,我说的引导是指带路啊,指引一下哪个科室在几楼啊等等,检查诊断的事,那当然还是医生,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情,您说是不是?现在医患矛盾尖锐啊,我们要想办法化解,而不是激化,我也不避讳,那天的话您说得不大合适了,肠套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尤其这几年,又有新的变化,不像一般人想的那样简单,按医生的说法,还可能是淋巴腺肿大,还可能是肠壁长息肉,甚至还可能是肿瘤,弄不好要出人命的——我不是管业务的我也不大懂啊,医生还说……医生责任大,所以说话比较着急,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大好听,我就不引用了啊,反正呢,总之呢,就是说,是不是……
向素云神色肃穆,说:是不是以后就不让我来了?
那人倒怔了一下,马上放松,说:哪里哪里,来还是欢迎您来,也需要您来,但是呢,做好义工本份,不介入医院其它流程,听说您对孩子教育问题很有研究,那就多和家属聊聊这方面的话题,不是更好?您说呢,向阿姨?
向素云的话,一下少了很多。人也没精神了,每天午觉多睡半小时,下午提早半小时就想走,连个头也好像又矮了一截。自言自语倒是多了,过去她的话多,再多也有听众,现在这听众只有她自己。她靠在玻璃门上嘟囔:言多必失,多做多错,还不如像那谁,啥也不干,直直站那里,像个木头牌子,专给人指路,指东指西,永远指不错,指错了也没关系,大不了再指一回,出不了人命……
小儿科来了一个混血儿,爸爸法国人,妈妈上海人,引得左右都来看。混血儿眼睛生得漂亮,哭起来也吓人,他听懂了要打针,哭了两小时,护士也没找到机会把针扎进去,爸妈也不上心,还嘻嘻哈哈的,举着手机给孩子拍照。护士叫来保安:去,到底楼,把向素云叫来。向素云驾到,围观人群自动分开两侧,闪出中间过道,向素云立在中间,大有王者归来、闪开我来的气势。刚近了身,还没揽到怀里,混血儿睁眼看到她,竟不哭了,还改回了国语,清清楚楚说:奶奶,要奶奶!这下众人可乐了,一片赞叹声。向素云就势抱起混血儿,找个椅子坐下来,熟练地踮着脚哄他。人群外那个长得像齐达内的光头大个子突然冲进来,挥舞双臂,冲向素云大喊大叫,也听不懂他叫什么。混血儿听到法语也激动了,又哭闹起来,向素云和护士还没明白过来,怀里孩子就被她的中国妈夺走。人群外,齐达内还在跺脚,晃着光头,好像要顶人。护士长用英文跟他交流了,过来扯向素云衣角,说:阿姨,你先出去,出去。
事后大家才明白,混血儿看到向素云,睹物思人,突然有了逃避打针的新灵感,他要奶奶,可不是向奶奶,是正宗的法国奶奶,法国奶奶到了,他才肯打针,法国奶奶在法国,肯定到不了,他就不用打针。也不知为什么,坏孩子非用汉语说,搞得中国奶奶自作多情了。齐达内爸爸冲过来,是因为他一向反对在孩子哭的时候哄孩子,认为只有在孩子不哭的时候才能哄他,要哭就让他哭去,坚决不哄,他尤其反对奶奶哄孩子,尤其尤其反对中国奶奶哄孩子……
这件事后,向素云的自言自语又多了新素材,她不再提美国人,常提法国人,她说:法国人教育孩子,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这样不对的,法国孩子也是孩子,哪能这样教呢?哭了不哄,不哭了才哄,这叫什么理论?不哭了要你哄!
总之,继医疗领域受挫后,向素云在教育领域也接连受到挑战,不但混血儿,她那本土的外孙也让她头疼。有一次女儿从家长会上回来,对她说:妈,你以后别教孩子写字了,现在的笔画顺序和我上学时都不一样了,和你们那时更不一样了。向素云说:瞎讲,都是中国字,笔画怎么会不一样。女儿说:我也想一样啊,可现在书上就是这样教的,我又没办法了。向素云把语文书丢给女儿,说:你随便找几个字出来,我写给你看,看看我写得对不对。女儿给她找了四个字,她写了,一对照,两个写对了,两个写错了。女儿还安慰她,说:妈你不容易了,还写对了一半。她却心里暗惊:看来很多事情真的不一样了,还得不断学习啊。
她和女儿带外孙出去,外孙不去,女儿把他从卧室拖在门口,他就站在门口,拖到楼下,他就站在楼下,女儿命令他:我数到三,走!外孙说:我不走,我爬。数到三,他真的趴在地上,像个蜥蜴似的,肚皮贴地,两手两脚伸出去,爬起来。向素云跑过去抱他,女儿说:别抱他,让他爬!向素云说:不好爬的,衣服脏了还好,手要磨破的。女儿说:都是让你给惯的——爬!爬!我让你爬!
向素云的话越来越少了,有时说到一半,自己先否定了,说:不说了,都是老掉牙的了,现在什么都变,现在连肠子都跟过去的肠子不一样了,你说还有什么好说的……真要说的话就一条,还得学习!
她回到医院,看门诊大厅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大千世界,不知从何学起。不过看得久了,也还是有所收获。有一次她遇到一个刚当了奶奶的老人,她把最新的学习成果跟她分享,她说:你看出来没有,来小儿科的人,妈妈越来越少了,比爸爸还少,现在不是有个电视节目叫爸爸去哪儿吗,我看不是爸爸去哪儿,是妈妈去哪儿了。现在都是谁在带孩子?是我们。
有个爷爷,边排队挂号边从口袋里掏药吃,她对他说:我外婆活到105岁,前几年才过世,为什么?就一条——她天天看养生堂!每天下午五点二十五分,中央台的养生堂,她一直看,看到死。我现在也看,我不光看养生堂,我还看上海台的健康之路,名医大会诊,浙江卫视的健康零距离,湖南卫视的百科全说,我全看,老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看现在是学到老,才有可能活到老。
有个外婆,女儿刚离婚,她带外孙来看病,护士出来叫号,说:王童泽,王童泽小朋友的爸爸在吗?旁边一个爸爸噌一声站起来,她却眼泪掉下来。向素云劝她:单亲怎么了?我爱人十五岁就没了爹妈,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是他带大的,现在怎么样?不也蛮好吗?也没犯法啊。
还有一个外婆,女婿有外遇,她逢人就讲,讲得整个小儿科的人都知道。向素云说:丈母娘最好别插手,丈母娘一插手,没事也有事,我现在也长记性,不管他们的事,我说多了,他们会吵架,真吵分了,还不是我烦?你说对不对,还不是我们烦?
她说:我年轻时是开天吊的,就是那种横在天上的起重机,也叫龙门吊,你想不出吧,天吊多高?十五米,我呢,一米五!我还恐高!我沿着铁梯往上爬,腿抖啊,上去就不敢喝水,怕上厕所,而且你知道吧,上去就算了,下来的时候更怕!但是没办法,你就是干这个的,后来我也总结出办法,现在我告诉你,你也能用,就一条:眼睛看远处,别看脚下!
4
冯家慧的脸好看,她站在门诊大厅的问询处,脸上有一种天生的镜头感。来来往往的人,不管匆忙或是麻木,眼里总有她。从后面看,她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美女,绕到前面,她也不让人失望,如果不考虑她的年纪,以及她脸上那层像被粉底覆盖的悲戚底色,她仍不失为一个美人。她给一个贸然闯入大厅的病号指路,姿态优雅,连伸出的指尖都富有诗意。身旁一位年轻护士,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比她更胜任这工作,偏偏没有人问她。据说,有一种人天生容易被人问路,冯家慧属于这一种。
按医院义工宣传手册上的说法,她是医院的“一道风景”。悲伤使她更加动人。
2006年9月,她的老公查出得了肠癌,9月26号开刀,第二年7月4号走掉。冯家慧再难忘记这两个日期,比她老公生日记得都牢。说到底,老公的生日与她无关,只与她婆婆有关。而老公的死,与她有关。
她还记得夹在这两个日期中间的一天:2007年4月5日。那一天,她的检查结果出来,乳腺癌。那天,东院门诊上正好是给她老公开刀的那位医生,医生看到她,还笑,摘下口罩的一边,说:咦,你怎么来了?
那时她老公还在化疗,情况已非常危险,每天挂盐水,抽腹水,人瘦成一条,走路都困难。她像往常一样来到病床前,从包里掏出检查报告。她必须要带报告来,白纸黑字地宣布这个消息,否则,她怕老公说她开玩笑。那时刚过完愚人节没几天。
东院不是专门治疗乳腺癌的,有人建议她去中心医院开刀,中心医院的乳腺癌科室全国有名。但是女儿听到这个消息,说了一句话。她说:就在这里开吧,否则我一会儿跑这个医院,一会儿跑那个医院,跑得过来吗?
她不说话。女儿就是这样,在她的眼里,爸爸永远排第一位,她自己排第二位,如果冯家慧能有幸排进女儿的视线,也是排第三位。但是这时,她老公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咱们在一起开吧,这样,我还能去看看你,你真要到别的医院,就怕我……
冯家慧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在选择一家医院,更可能是生死之别。
几天后,她在东院开了刀。她老公在五楼,她在十一楼。她老公其实在四楼,但所有标识都写五楼。
她老公挂完这一天的盐水,摇摇晃晃起来,去十一楼看她。她还在昏睡中,老公坐在床边,摸她的头,说一句“前世作孽啊……”,眼泪就掉下来。
他坐到她醒。醒过来后,她看到老公的笑,他拍拍她的头,说:“你没事的,你这个小毛病,我比你严重呢。”
女儿在一旁哭,她听得出来,这哭并不全为她,即使全为她,也不像刚知道爸爸生癌时的哭。刚知道爸爸生癌时,女儿曾脱口对妈妈说出:都是因为你!
她也想哭,竟没有泪。她想,死就死吧,活着也没意思。
她也开始了化疗,像在重走老公的路。此时,老公已经病危,东院不再需要他了,他被急救车拖走,好腾出昂贵的床位,留给下一位更需要的人。他被送进了一家地段医院。这里是火葬场的前站,进到这里的人,很少再出来。
化疗的间隙,冯家慧又做回到一个病人的家属。早晨六点,她去医院替女儿,女儿抹把脸,乘第一班地铁去浦东张江上班。上午九点半,老公的妹妹来替她,她回去路上买点菜,回到家里,一样一样地烧。过去,这些事都是她老公的,她完全不擅长,每次放盐都要用勺量,恨不能一粒一粒数。下午三点,她再去医院,带去饭菜,也替下老公的妹妹,直到晚上女儿下班回来,再替下她。有老邻居在她经过时迎上来,抚她的衣袖,仰望她,不阴不阳地笑说:啊哟,家慧勤快嘛,一天两趟医院。
早晨,她老公捏住她的手,说:最好你一直陪着我,晚上也陪。
晚上,女儿回来了,就把所有人赶走。她两颊陷进去,瘦了近二十斤。
死神并不想一下收走他和她,而是慢慢咀嚼他们,不让冯家慧错过任何一个痛苦的细节。到后期,她不敢看她老公的脸。即使在患病前几个月,他也还保持着魁梧、英俊,他们走出去,仍是让人艳羡的一对。而现在,他黑瘦得像一截木炭。只有眼睛仍恐怖地明亮着,每当有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那眼睛就烧起来,好像看到了又一个救星。那眼神让医生都难面对,也让她加倍痛苦。
医生趁冯家慧和女儿交接时来,很随意地聊起来,说:有一种冬眠针,现在有些病人和家属都用,你不要误会冬眠针不是安乐死,不是打下去就走掉了,冬眠针是让他慢慢地睡,慢慢地……她有些心动了。
女儿说:不。
说完看了冯家慧一眼。这一眼,她有意保持了三四秒的时间,眼神由挑战、决绝,渐渐变成忿恨。医生看一眼体温计,去了下一个病床。
冯家慧第二次化疗时,老公走了,才59岁。女儿为他准备的60岁生日礼物,最终送进棺材里。
老公走前的三四天,冯家慧早晨去医院,女儿没去洗脸,眼睛肿着,端坐着,向她宣布了一个消息。或者也不单是向她宣布,是向全世界宣布。
等爸爸走了,我也走。
你走去哪里?
印度。
5
家家一直被人追,她的跑道上从来不缺人,但她一直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直到高三,一个男生追上了她。或许也不全是他追上她,她也有意放慢步伐,等他追上来。这是一段被普遍祝福的恋情,同学老师都知道了,连爸爸都知道了。他们也挺争气,直到大学快毕业,他们的热恋仍没有要疲软的迹象。直到有一天,妈妈知道了。
妈妈神通广大,居然暗中搞到了男生的生辰八字,等家家知道时,检测结果已经出来:她和他八字不合。不是一般的不合,是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那种不合,用妈妈的话说:谁嫁给这个男的,谁就要死掉!
像一切电视剧的惯常情节一样,妈妈成功地拆散了他们。男生远走新加坡,在那里娶妻生子,彻底杜绝了再来骚扰家家的可能性。但是多年以后,这恰恰是让妈妈最难堪的一点,妈妈开始逢人就讲:蛮好当年该让他们结婚的,我女儿眼光不错的,他后来去新加坡,一去月薪就五千块,五千新币哦,换成人民币,五五两万五呢!
妈妈没说的一点是,男生的妻子并没有死掉,她一直健在,他和她,幸福得像电视剧一样。
家家在那一年发了很多誓,把一辈子能发的都发了。她从小个性强,大多数誓言她都说到做到了,除了一点:迷信。
2009年9月,家家也开始迷信了。不过她不信妈妈那套被她称为“邪教”的东西,她要追随的是佛教的起源地:印度。爸爸手术结束后,有几个月病情相对稳定,12月,家家飞往新德里,参加第二届华人宗门实修法座,同时也是印度十七世大宝法王的愿法会。在印度,她花了整整两天的时候,接受了法王噶玛巴的胜乐五尊大灌顶,又用十五天时间,去了玄奘曾到过的所有佛教圣地,去了佛祖当年在菩提树下成佛觉悟的佛陀伽雅,第一次向五位门徒宣扬佛法初转法轮的鹿野苑,佛祖涅之地库什那伽……
这同时也是一份旅行团的标准行程单。她为此交了一万五千块钱的团费,并将两万块钱在指定账户冻结了四个月。
她在每一处胜地流下眼泪。她的团友与其说是被法王震慑,不如说是被身边这位胖姑娘莫名的虔诚所打动。自从与初恋分手后,家家一直把自己养得很肥,最近半年多,她的肥胖与爸爸妈妈的消瘦形成鲜明对比,像是另一种贫病。
十七天的行程里,除掉必要的交涉,她坚持不与任何人说话,不拍照。
行程结束,她从五千公里外的异国佛乡,直接飞回到上海的病床旁。
她每晚为爸爸诵经。谁要想留下来陪她一起,定会遭到她的怒斥。她把黑暗的、充满死亡气息的病房,变成她密修的暗室,变成她和爸爸相互加持的宝地。
但是法王并没有格外开恩,爸爸的死期,仍精确遵循了医生和检验报告的预言。她把这归罪于自己的业力不够。爸爸后事一了,她立刻飞去印度。她的行李箱早就收拾妥当,里面装满了她舍不得丢的全部旧物,不包括妈妈。
她没想过再回来。
在她最艰难的时刻,一个印度男人帮了她。只过了两个多月,她就嫁给了男人的弟弟。一年多,她生下了混血女儿,这中印友好的结晶。
上海的一切,都被她远远地丢在了上海。她几乎脱胎换骨,生完女儿后,她甚至想过重新减肥。
但是,在女儿出生的那一夜,她惊觉竟没有一个人可以报喜。在同学朋友同事眼中,她几年前就失踪了,虽然她留有所有人的联系方式,但她不敢贸然露面。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逆转的剧情,怕吓着他们。
微信上,一条关注请求已经跳了很久,她一直没同意,也没删除。这一夜,趁着这辞旧迎新的历史时刻,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她点了同意,然后,以妈妈的身份,给另一个妈妈发送了一张宝宝照片。
6
冯家慧的老公去世前一年半,她的父亲先去世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先是失去了父亲,又失去老公,紧接着又失去女儿。
她自小被宠,家里有一个父亲,四个哥哥,后来又有老公。她一直被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男人宠,却与女人搞不好关系,甚至女儿。
他们给女儿取名家家,是从她的名字里取出一个字,也寓意家。现在,这个家变成阴阳两隔。
但是,生活仍然滚滚向前,冯家慧把与老公和女儿有关的一切都清理进一个房间,一把锁,封住了这个家的过去。她新烫了头发,把侧面几绺染成酒红色,买了新款的太阳眼镜,遮住她的黑眼圈,也遮住人们内容各异的眼神。她的胸前空洞,碗口大的刀疤时刻拉扯着她,使她不能走得更优雅,但她仍然把高跟鞋踏得笃笃响。她想,她活着回来了。
她重新开始唱歌跳舞。她的那些来历不明的老搭子们,全都识趣得很,没人提那些扫兴的旧事,好像她只是外出旅行了一圈,错过了几场聚会,如今她回来了,随时可以归队。他们都喜欢唱卡拉OK,冯家慧仍然负责去网上团购优惠券,只需29元8角,就可以让这群没心没肺的老头老太们唱六个小时,从上午九点唱到下午三点。有时他们也从浦东到浦西,去四川路上的一家,走大连路隧道,两站路就到,那里价钱还要便宜,但音响不够好,歌也不全。在昏暗的包厢中,冯家慧妖娆地唱着,她不喜欢怨妇式的悲情调调,也不像退伍的老黄一样只唱红歌,她喜欢男女对唱的情歌,她仍然可以把其中的女声部分唱得甜美,而且不管谁来唱男声,她都觉得那首歌是专为她写的。因为某些情愫,她的歌声里有了更多“演唱”的成分,她每每唱得很动情。但是音乐声和哄笑声太吵,没人留意这些。
有一天,她接到东院的一个电话。她熟悉那个噩梦般的号码,近几年来,她们家几乎每一个噩耗都是由这个号码来宣布的,但是现在,她不怕这个号码了,她身边没人——除了婆婆,婆婆最近也病重,但这与她何干?她按了接听,是东院的社工,问她愿不愿意再回医院来。
……还有很多人,几乎每天都有,正经历您当年的病痛,您愿不愿意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他们讲一讲,告诉他们癌症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您的一句话,可能比我们十句话更管用……
社工解释了很久,她从一开始就听明白了,她老公住院的时候,也曾有癌症康复者来做过他的工作。她突然打断社工,说:你们是东院,那一定还有个西院了?
是的,还有一个西院,不过阿姨您离东院更近,肯定更方便来东院,西院太远了,西院而且条件差,我们三甲他们二甲……
我去西院。如果西院也需要我的话,我去西院。
冯家慧成了西院的一名义工,每星期去一天半,其中一天在肿瘤科,半天在大厅做导医。一旦变身旁观者,她就有更多机会来感受医院,这个与卡拉OK厅一样掺杂了喧闹与绝望的地方。她款款立于来往人群中,落寞与淡漠,混合着敷在她的脸上,让她看上去如此与众不同。即使那件义工蓝马甲,套在她的身上似乎也别比人更得体些。
她发现肿瘤患者竟然这么多,比她想象的还要多,他们不分年龄、性别、贫富或地位高低,前一天他们还活蹦乱跳,对世界不屑,一朝被宣判,立刻缩下头,眼神恢复到初生婴儿般的无助与惶恐,甘心接受死神与医生的联手拨弄。她突然就有了强烈的表达欲。
她讲她和她老公的抗癌故事,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悲观者和乐观者各取所需,都能从中得到论据,生或死,仍然各占一半。她讲这些故事,既开导别人,也是安抚自己,那些汁液茂盛的故事,每多讲一遍,悲伤的水份就被拧干一层,到最后,只剩下干硬的情节,像别人的故事。
义工们来路各异,有的人能迅速与所有人打成一片,有的人则准确计算出每个人的家底,还有人热衷于传播别人的家事。冯家慧因为参与得很少,因此被议论得最多。她听到过几耳朵:外面花头多的……女儿都不要她了……美女本不宜被女人堆接纳,有故事的美女就更容易招惹非议。她坦然听着,并不辩解。也没什么可辩解的。
不到万不得已,她不和别人一起吃饭,都是自己吃。多数时间在外面吃,偶尔也回家,烧一到两个小菜,吃一到两顿。老公住院期间她练就的一点手艺,如今是她仅存的生活技能。
外孙女27个月大的时候,女儿携全家回上海过年。她当然高兴,但有保留,也透着小心。那个眼窝深陷的女娃,已经与照片完全不一样了。她盼着能听到一句“阿婆”,女儿说:她叫过了,你没听懂。
她和那个手臂爬满汗毛的印度男人没讲几句话,看都没看几眼。他和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坚持和女儿讲上海话。其实她知道,即使讲普通话,印度男人也听不懂。
她一眼就看出来,女儿过得并不好。印度男人没有正式工作,基本全靠哥哥家接济,还懒,从不插手家务,和上海男人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物种,女儿好像嫁了一个外星人。可是,女儿是当上海女孩养的啊。她能想象到女儿的辛苦,有一年国航在印度招人,女儿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去应聘,本来人家已经看上她了,月薪开出一万也不错,但看到她怀里的孩子,人家又改口了。
而且,那个男人还吃素!一胳膊毛没褪尽,还好意思吃素!女儿还好说,原本荤菜吃得就少,只可怜外孙女,每天跟着吃斋,饿得精精瘦。
她隐约怀疑,印度男人可能还打过女儿。
不过,她什么也没说,过去的、现在的都不说,假装所有人都很幸福。
女儿这次回来,还帮上海一位亲戚带了点药,顺便赚点差价。印度的药便宜,880块钱的药,可以吃一个月,放在上海,880块只能买到一粒半。看女儿点钱的神态,她已经把宗教和法王扔得远远的,彻底投身到火热的世俗生活中。
一家人吃好饭,冯家慧洗好碗,就去换上皮裙,长靴,宝蓝色的收腰羽绒服,波点围巾,犹豫拿哪个包。女儿说:妈,你去哪?
我去……唱歌,他们等我。
妈,你能不能不去。
他们等我……
妈,你能不能不去,能不能陪陪我。
我不是天天……
妈,你能不能不要一吃完饭就走,要吃饭了再回来。
你回来,我一天三顿给你们烧好,吃好,洗好弄好,你还要怎样?
妈,我多少年没回来了?我回来,就为了吃你烧的菜吗?不吃你烧的菜我就活不到今天吗?
你多少年没回来了?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没有他们陪我唱唱跳跳,我能活到今天吗?
她随便抓一个包出门,免得听到女儿的下一句话。看上去,这一轮她赢了,但她比输了还难受。
她并没有去唱歌,这一天不是唱歌的日子,她去了医院。市卫生系统要评优,医院请了记者来宣传造势,要她临时去一次。
换上蓝马甲,坐到一个患者的床边,冯家慧又讲起她和她老公的故事。这故事像黑硬的木耳,被晾晒了太久,不期然与她一腔苦水相遇,蓬勃发胀起来。她讲得声泪俱下,一个摄像机的镜头捕捉到了她。
人群中,她总是第一个被镜头捉到。据说,正是因为这一组镜头,她和另一位义工,喜获全市优秀志愿者称号。
她赶回家做饭,一进门,女儿把手机举到她脸前,说:谁把我的微信号告诉他的,你?
她看着女儿手机上的头像,一时没反应过来。
女儿说:你为什么把我的微信号告诉他?你想干什么?
冯家慧想起来了,女儿回来前几天,她的高中女同学打电话来,问她的联系方式。那时候,冯家慧正沉浸在女儿即将回家的巨大喜悦中,她以为一切即将回到正轨,于是毫不犹豫地告诉了女儿的同学。挂断电话前,女同学问了一句:阿姨,这个微信号,其实是他让我向家家要的,我能告诉他吗?
她说了一个名字。冯家慧不会不记得,是女儿那个八字不合的初恋男友的名字。
她想,不管她怎么回答,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女同学不聪明,或者太聪明了,才多此一问。当初女儿辞职时,向那家银行推荐了这位女同学。如今她混得多好,一个月两万六。
她含混一句,挂了电话。
她没想到,几天后,这含混一句竟如此发酵,变成女儿的咆哮。当着她和印度男人的面,家家摔了手机。新买的、八千多块钱的Iphone5,飞得满屋都是。
你凭什么告诉他我的号码,你凭什么说让我们断就让我们断,说让我们联系就让我们联系,你凭什么!
她想:家家,我错了,我不该透露你的号码,不该在电话里跟你的女同学说你如何不好,如何不快乐,我并不知道这些话等于间接说给那个男生听了,家家,我不该拆散你们,我鬼迷了心窍……
你这个霸道的女人,你对我爸霸道,对我也霸道,你对所有人霸道,你看看现在有没有人愿意理你!我烧饭怎么了?做家务怎么了?难道像你一样,什么都要爸爸给你做?你从来就不会照顾爸爸,你这个又懒又笨的女人,爸爸累死了,你还想让我也围着你转吗?你休想!我就是要让你孤独,让你寂寞,我宁肯伺候印度阿三也不会伺候你!
她想:你说我不关心他,不照顾他,不心疼他,那我的癌症怎么得的?还不是他得癌后我伤心伤的?辛苦累的?你能说和这个没关系?我原来身体多好,可知道他得癌,我哭了多少次?才过半年,我就得了癌,瘦了十几斤,要不是你爸提醒我去检查,我自己都没意识到……
女儿说一句,她在心里应一句,也轻微地驳一句。但是,她的驳终究无力,终究无凭无据。而且,她没说出口,女儿的反驳已经来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我爸得病了你开始伤心了?我爸要死了你开始难过了?开始学做饭了?你这个坏女人!我爸死在你手上!我一辈子毁在你手上!我的前程、我的幸福,全毁在你手上!
她想:女儿还是她的女儿,她依旧精准,每一句都命中。
她想:这迟到的清算,终归还是到了。
外孙女一直睡着,竟没被吵醒,或许她不会被她听不懂的话吵醒。这个混血儿暂时不会知道,两个女人间的仇恨。
她们最终和好了,至少在表面上。在机场,印度男人给老中青三代女人拍了合影。照片里,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笑。
她找到社工部,要求换一个岗位。医院方面说:等市里评选结果下来,再考虑。她说:评不上还好,评上了,不是更不让换?医院想一想,说:那不会,毕竟只是义工,你想换,医院自然会考虑。后来她果然换成了。
她去了聋哑科。市聋哑学校每周有三个老师过来指导,她只负责简单地指引,为此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手势。她喜欢上聋哑人,愿意与他们无声地交流。慢慢地,她的话也越来越少,终于不再开口。
7
其实西院里的老年人义工很多,都挺尽职,说起来,也都有自己的故事,不比冯家慧她们差。但是,因为最初她们二位以微弱优势被评上了西院优秀义工,等到区里再评时,她们就顺理成章被报到区里,等到全市卫生系统再评时,她们就被报到市里。市里开明得很,不打击下面积极性,报一个批一个,反正通知写明了要求下面配套资金,上面就是多印几个证书多敲几个章嘛。再加上西院宣传有方,结果出来,报了两个,评上两个。
西院的院长擅长即兴表演,到了谁的场子,就把谁捧成一朵花。西院与关心西院各界朋友恳谈会暨优秀义工表彰会上,院长前呼后拥地来到获奖义工前,突然举起双手,扭着身子,表情悬疑,像魔术师附体。他对左右说:别讲,你们都别讲,你们也别自我介绍,让我来猜一猜,您是……冯阿姨,对不对?您是向阿姨,对不对?对不对?
冯家慧和向素云,仿佛院长刚刚大变活人变出来的,并排站着,接受众人对院长鼓掌喝彩。冯家慧妆容得当,亭亭玉立,向素云身子紧一下,扯一下衣角,众人每鼓一次掌,她就向冯家慧靠一靠,向冯家慧的腰后面躲一躲。
最后,按照惯例,院长开始了即兴演讲。院长干行政出身的,文化不高,都是秘书给他写稿,他有一次把如火如荼读成如火如荼,从此秘书就只挑简单的字写,有时也用些民间谚语一类的。院长虽然识字不多,但领悟力强,又会表演,每次都搞得好像即兴演讲一样。
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西院有二老,有两个宝!都说我们西院不如东院,我们西院确实不如东院,可是我们西院有两个宝贝,东院没有,人无我有,我们就要好好宣传一下,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作家——院长指指我——来我们西院体验生活,写写我们医护人员的喜怒哀乐,写写我们西院人的光荣与梦想,我跟他讲了,也给我们两位义工阿姨写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就叫——我建议啊——就叫,西院二宝!
- 都市的其它文章
- 最珍视的技能永远是虚构(创作谈)
- 闪电(外三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