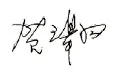考古学是研究“人”的重要科学
考古学是研究“人”的重要科学
时常有人问:你们做考古的整天摆弄的都是地下挖出来的物件,你们也会研究“人”吗?我们只好反复地解释:考古学当然研究人,许多考古学家都在追求“由物及人”的学术目标。广义上说,考古学揭示的物质文化世界是人如何生存、生产等种种行为模式的证明,透露出不同状态下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及其内心的种种诉求,通过它们,可以分析、追索人类各种行为模式的特征及隐藏在背后的产生原因。当然,具体讲到考古学是如何研究“人”的,其例甚多,略举一二为证。
首先,考古学要研究“人”这种“万物之灵”是从哪里来的?这方面的研究是由考古学与古人类学、基因人类学、古生物学、古环境学等所共同完成的。考古学家等通过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甚至包括前旧石器时代的古灵长类化石、人类的骨骼化石、石器、人类活动遗迹及共生动物化石等材料的研究,探讨灵长类动物及人科动物的起源,现代人的产生、演变、发展诸问题,其中涉及到人的体质形态、思维、语言、社会化、物质文化创造能力、不同时代的婚姻与家庭形态、人种、宗教、艺术、驯化农作物、驯化动物等种种方面的起源问题,包括起源和演变的时间、地点、原因、结果、影响等,这些都是涉及到人的一系列本质特征的问题。即“人”的产生不仅仅是指生物性种属和体质特征的形成,更是指文化创造能力的产生及各种文化行为的生成与演变。
其次,考古学可以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人的族群问题。人是一种社会化动物,“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因此,人的文化行为和结果体现了其族群化的社会性特征。考古学家能够对新石器时代或者青铜时代甚至铁器时代人的群体性创造予以“文化”的命名,用夏鼐、安志敏等先生的话说,“考古学文化”是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关于“考古学文化”与人的族群关系的问题,苏联学者A.R勃留索夫做过探讨,认为“如果在某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区内存在相同的居民(根据人类学资料),且全区的经济形态、居址形状和埋葬礼制等也都一致,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这一考古学文化是一族的共同体”。当然,一定的“考古学文化”与“族群”之间是否能一一对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利用考古学文化研究人的族群问题已有大量实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研究区域文化或族群文化如吴文化、越文化、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匈奴文化等等,无不大量利用了考古资料,也可以说,离开考古资料,古代尤其是缺少文献记录时期的族群文化是很难予以界定和阐明的。
此外,考古学家还可以透过各类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而表现的“文化”——这是特定人群所拥有的显著标志——窥探到各种有关人的探索、创造、审美、交流、播迁、痛苦、冲突、毁灭等种种行为证据。在“人”的视角下,一切考古发现的遗存都不再是冰凉、无言、死亡、寂静,而是一种生命的复活与延展,是一种来自历史深处并且面向未来的呈现、呼喊、馈赠与警示。
特别要指出的是,考古学可以用发现的“墓葬”这种人的归宿地遗存来观察有关人的诸种社会与情感现象:家庭、家族、阶级、阶层以及哀思、祈求、仁爱、慈悲、恐惧、迷失等等。当然,其中也有无知、压迫、残忍、贪奢……所以我们才说,考古学家面对各种发现时不能只是一味赞美,尤其是那些展现专制、残暴、奢靡、贪婪或一切人性之恶的遗存,我们应当抱以公正、理性和批判的精神。试想,那些来自普通百姓创造的奇珍异宝当时本应用于解决社会大众的贫苦,但却被权势者非法占有进而作为私产埋入地下墓葬之中,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在它的背后隐藏的恰恰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满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极不平等的人间悲剧,而这种荒唐的社会行为竟然成为今天的一个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我们在欢呼、惊叹、欣赏的同时,难道不应该多一份人文的思考、人性的剖析和对人类正义的阐扬吗?
总之,考古学不是仅仅发现、描述、诠释“物质文化”现象的科学,它更是“透物见人”,揭示人的运动世界和人性本质的科学。换句话说,科学是为人类的福祉事业而存在的,考古学自然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