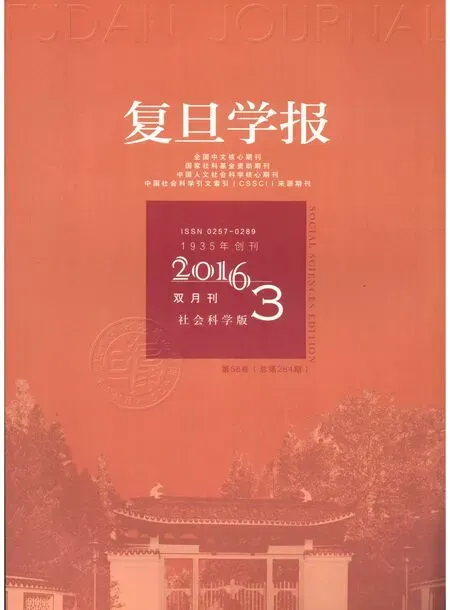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
[日] 川原秀城
(东京大学,日本)
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
[日] 川原秀城
(东京大学,日本)
【摘要】朝鲜朝后期即倭乱、胡乱以降,朝鲜实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瀷(1681~1763)与洪大容(1731~1783)的朱子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互相纠缠的思想性格,即一方面作为朱子学者在思想上普遍拥有强烈的正统意识,因而其思想本质对于异端思想采取的是非容忍的态度,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积极地研究来自西方的异端思想,并将其研究成果融入朱子学体系当中。事实上,在作为朱子学相对化的结果而出现的朝鲜实学的形成过程中,西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瀷基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三魂论以及脑为知觉中枢的西欧医学理论,改变了退溪“四端七情”等论述,并试图寻求朱子学与西学理论在所有命题中都能无矛盾的统一。洪大容则基于大地为球形的地圆说以及地球不过是无数世界之一的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对于中国中心乃至地球中心的朱子学世界观提出质疑,并以此为根据发展出价值相对主义的思想。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相对化,正可说明由于西学东渐而发生了18世纪东亚的宏大宇宙观的转换与变化。
【关键词】朝鲜朝后期实学李瀷洪大容价值相对主义
朝鲜朝宣祖二十五年(1592),丰臣秀吉派大军侵略朝鲜。这场战役(包含休战期)前后长达七年(1592~1598),此即倭乱(文禄、庆长之役)。另外,在仁祖期间,后金(清)军队两次(1627、1636~1637)入侵朝鲜,此即胡乱。倭乱、胡乱的战祸是未曾有过的,使得朝鲜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朝鲜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的朱子学权威开始下降,其对政治社会的思想影响力也已大不如前。
在社会科学中,对于因为社会变动而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一般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上的回应方式。其一是肯定传统价值,重视历史传承,对固执于“社会模型”的保守主义统治原理及其学术思想进行重新组合与强化;另一种则是绝对地信赖理性,正视“社会现实”,实行革新主义统治原理及其学术思想的变革。在我看来,在朝鲜朝后期,前者即表现为朱子学统治思想的绝对化,后者即表现为朱子学的相对化。
在朝鲜思想史上,最先有组织地推进朱子学的绝对化(教条化),是刚进入朝鲜朝后期时出现的宋时烈(1607~1689)。宋时烈重视朱子学理念的原理和原则,并将其绝对化,即:(1)通过理论整理以证明朱子学整体的正确性(无谬性);(2)作为社会全体绝对的指针进行广泛的普及;(3)回归根本的理念并追求严格的应用,以此克服朝鲜社会的危机。宋时烈自定的使命就是“明天理正人心,辟异端扶正学”(权尚夏《尤庵先生墓表》)。宋时烈政治思想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一点可由朝鲜朝后期的政界与学界中老论与宋时烈学派的持续兴盛得到证明。
另一方面,革新主义的朱子学者面对倭乱、胡乱之后的社会思想危机,正视两班社会的矛盾,拒斥教条(独断学说)而将朱子学相对化,试图通过推进思想的自由和灵活的社会应对以克服深刻的危机。这是因为朱子学业已丧失活力并严重衰退,很少有人还会原封不动地信奉其教义,也很难再对体制性教学的作用寄予期待,而更高层次的“义理”本身则与此相反,乃是天下共有之物,拥有无穷、无限的可能性。
初期的革新主义者超越以往的范围,构想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但他们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论,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看,都是不充分的。具备思想实质的真正的社会改革论,还要等到朝鲜朝后期18世纪实学(朝鲜实学)的登场。实学之名原是指实用之学问,然而朝鲜朝的实学家一方面重视保持朱子学的框架和严格区分传统与异端,另一方面又主张即使是异端之言,若有可观之处,亦必须学习,并且鼓励超越朱子学的范围(甚至不避攻朱),对于包含实用之术的广泛领域进行研究。*以上朝鲜思想史的概述,基于川原秀城:《朝鲜思想大观》,《斯文》第123号,2013年。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分析朝鲜朝后期实学家的朱子学研究的内容,以期阐明朱子学相对化的内在实质。*所谓“实学”或“朝鲜实学”,并非是存在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确定的历史概念,而是后世历史学家为便于解释当时状况而设定的概念。从实学的思想性格来看,形成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实学观,各种实学观各自主张自己的正当性,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本文分析的特点是,以对西学的接受为视角来考察朝鲜朝的实学,即以朱子学与西学在朝鲜的会通和融合来定义实学。具体而言,分析朝鲜实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瀷(1681~1763)与洪大容(1731~1783)的朱子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两种互相纠缠的思想性格,即宗朱与攻朱的奇妙混合(既保持强烈的思想正统意识,在本质上对异端思想采取非宽容之态度的同时,又积极地研究异端思想,并将其研究成果融入朱子学体系),以期论证这样一个问题:西学在作为朱子学相对化的结果而出现的朝鲜实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 李瀷的学术
李瀷,字子新,自号星湖,祖籍为京畿道骊州,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朱子学者、西学者之一。*有关李瀷,笔者曾有3篇论文发表,即《星湖心学——朝鲜王朝的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与亚里士多德的心论》(《星湖心学—朝鮮王朝の四端七情理气の辨とアリストテレスの心論—》,《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6集,2004年),《李瀷的科学思想》(《李瀷の科学思想》,《星湖学报》第8号,2010年),《李瀷的科学论与朱子学的相对化》(《李瀷の科学論と朱子学の相対化》。该文曾于2013年“星湖先生逝世250周年纪念学术会议”上发表)。
1. 强烈的道统意识与异端的西学研究并存
李瀷的一生,经受了17世纪末叶激烈党争的冲击,他是经常生活在政治剧变之阴影中的两班知识人。其家族为科举合格者辈出的南人名门,曾祖父李尚毅为议政府左赞成,祖父李志安任司宪府持平。其父李夏镇亦为司宪府大司宪,肃宗六年(1680)遭遇了南人大黜陟(又称庚申大黜陟)事件,随之失职而被流放到平安道云山。
肃宗七年(1681),李瀷出生于其父的流放地。第二年,其父李夏镇去世,李瀷随母亲移居先祖墓所在的京畿道广州的瞻星里。李瀷资质聪颖,优于常人,但是生而病弱,无法外出就学,其学问主要得益于稍稍年长的仲兄李潜。
但是仲兄李潜于肃宗三十二年(1706),以老论金春泽等人企图危害王世子为由而上诉,要求撤换老论的右议政李颐明,引发了肃宗的愤怒,拷问之后而被杖杀。仲兄因党争而惨死,李瀷为此而受到极大的冲击,失去了立身出世以及关心世事的意愿,从而放弃了科举考试的学习,此后作为在野的学者而专心于读书和著述。英祖三年(1727),虽被推举为缮工监假监役,他力辞而无意仕进。英祖三十九年(1763)去世,享年83岁。

李瀷学问的根本在于性理学*有关李瀷的性理学,可参见张志渊:《朝鲜儒学渊源》(亚细亚文化社,1973年)与《星湖全集》文集附录卷一等。,其学统属于退溪李滉→寒冈郑逑(1543~1620)→眉叟许穆(1595~1682)传承的畿湖南人一系。但是,李瀷不止于将自身的师承系于李退溪,而是从个人内心出发,十分仰慕退溪的学德。因此,李瀷模仿《近思录》编集了收录退溪言行的《李子粹语》,以及为退溪的四端七情论辩护的《四七新编》,从退溪的遗集中分类抄出与礼相关的书札而编纂了《李先生礼说类编》等等。另外,李瀷希望通过研究经书及性理学书来把握真理,以供社会之实用。这一点可由保存下来的有关《诗经》、《尚书》、《周易》三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以及《家礼》、《近思录》、《心经》、《小学》等大量读书笔记得以证明。《诗经疾书》、《书经疾书》等便是此类著述。
李瀷将继承与发展朱子学说作为其一生的志向,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如果反朱子学者的异端言论中有不得不看之处,亦应当学习。他积极地学习西学,果断地利用西学知识来解释儒家经文,并提出多种社会改革论。真正的学者必须为了振兴正学而批判异端,但是李瀷不受此拘束,而是在了解异端的同时,视西学研究为学者之当为而予以肯定,不得不说这是作为朱子学者不应有的态度。
在维持朱子学所固有的强烈的排他性之同时,对于必须拒斥的异端却予以宽容,关于这一点或许应当做这样的解释最为稳妥:“这是一种承认其他思想也有部分价值的有限的多价值主义。”*金光来之东京大学博士论文:《星湖心学形成的研究——坚守与自得的折衷与西学》(《星湖心学形成の研究—堅守と自得の折衷そして西学—》,未刊,2015年)。
2. 星湖西学的概要
朝鲜朝景宗四年(1724)春,慎后聃拜访李瀷而了解到有所谓“西洋之学”,于是,多次就西学问题,与星湖发生了争论,相关记录便是《遯窩西学辨》。该书大致由《纪闻编》、《灵言蠡勺辨》、《天主实义辨》和《职方外纪辨》所组成。《纪闻编》的撰写目的在于介绍星湖西学的概要。
根据慎后聃的《纪闻编》,可以看出李瀷西学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虽然李瀷自身最终否定基督教神学,但并不认为西教是耶稣会的阴谋(“张伪教而陷一世”),西学以外的西教也可成为分析考察的对象。例如,尽管慎后聃批评“天堂地狱之说”等西教理论的荒唐性,但是李瀷却介绍了西学的“实用处”(科学内容)而强调其有用性,拥护“利西泰之学”。这与后文讨论的洪大容认为西教不值一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第二个特征是,将脑主知觉说(“头有脑囊,为记含之主”)与三魂论(“草木有生魂,禽兽有觉魂,人有灵魂”)看作西学的核心命题。*参见金光来:《中世基督教灵魂论的朝鲜朱子学之变容:耶稣会的适应主义与星湖的心性论》(《中世キリスト教霊魂論の朝鮮朱子学的变容:イエズス会の適应主義と星湖の心性論》,《死生学研究》13号,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10年)。甲辰(1724)春,针对慎后聃的西学“以何为宗”的问题,李瀷自己以“论学之大要”提出上述两说,可见上述说法是可以确定的。另外,戊申(1728)春,慎后聃曾对李翊卫提及,李瀷认同这样的命题。
所谓脑主知觉说,即“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李瀷《星湖僿学类选》的《西国医》以汤若望《主制群征》(1629年刊行)为依据,论述了“脑囊为知与觉的中枢”这一观点,将西医的脑主知觉说与东医的心主知觉说予以折衷,认为在人类的两大精神作用中,“感觉与知觉的作用在脑,思考与理性的作用在心”(“觉在脑而知在心”)。另外他还主张一身流行的形气粗大,主思的心气(心脏之气)则极其细微,而它们的大小也各不相同。
至于三魂论,这是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灵魂论,认为草木只有生魂(生长之心,anima vegetabilis),禽兽有生魂(生长之心)和觉魂(知觉之心,anima senseitiva),人有生魂(生长之心)、觉魂(知觉之心)和灵魂(理义之心,anima rationalis)。若将《星湖全集》卷四十一《心说》、卷五十四《跋荀子》以及《星湖僿说类选》的《荀子》合而观之,毫无疑问,李瀷所说的三魂论的论据与《灵言蠡酌》、《天主实义》的灵魂论以及《荀子·王制篇》的“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亦有义”非常相似。

李瀷对于西欧数理科学的称赞在《纪闻篇》以外的很多材料中也都可以看到。比如根据安鼎福《天学问答》附录,李瀷指出西欧的“天文推步、制造器皿、算数等术,非中夏之所及也”。尤其称赞“今时宪历法,可谓百代无弊”,“西国历法,非尧时历之可比也”。*据《星湖僿说类选·技艺门》的算学,李瀷引用徐光启之说:“徐光启有言曰:‘算学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盖欲心思细密而已。’此说极是。”强调作为学术理论与实用技术之基础的算学的作用。但是,徐光启的话引自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的《几何原本》中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杂议》,确切而言,并没有说到一般算学有如此的重要性。原文为:“此书(《几何原本》)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这不过是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做出的评价。李瀷将算学作为学问的基础予以很高的评价,这并不仅仅是援引而已,而是高度抽象化后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命题。按星湖的直觉,他将西欧文明的本质之一的数学所重视的逻辑思维很好地纳入自己的视野中。
3. 星湖的四端七情论
李瀷的心情论、四端七情论是退溪以来朝鲜朱子学内在发展的优秀成果*四端七情论是代表朝鲜朱子学的重要理论。张志渊在《朝鲜儒学渊源》中指出:“吾东儒教性理之学,自丽季郑圃隐(郑梦周,1337~1392)始倡,而历数百年……其遗言微旨,多不传于世。惟退陶(李滉)先生深究性理之源,始有四七理气之发明,而于是诸家异同之论起矣。”所谓四端七情论,“四端”指人所具备的道德情感。《孟子·公孙丑上》中所说“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义之端”的“羞恶之心”,“礼之端”的“辞让之心”和“智之端”的“是非之心”。“七情”指《礼记·礼运》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的特征都是“不学而能”的。,但同时必须承认其性理学的命题中也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李瀷的四端七情论,虽说是沿袭李滉以来的理气范式,但是吸收了奇大升(1527~1572)开始倡导而由李珥(1536~1584)集大成的理气不离的基本原理,并借此重新解释李滉主理的理气互发说(主张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是,具体到心情论所讨论的心之机能与构造的问题,李滉以宋代张载“心统性情”为理论根基,从“性”、“情”观点出发论心,而李珥受元代胡炳文“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大学章句大全·经一章》小注)的启发,与性、情一样重“意”。对此,李瀷则在性、情、意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觉”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到论点的变化以及论题的扩大。这与朝鲜朱子学的不断扩大进而发生质变的发展趋向是吻合的。
(1) 三魂论的影响
李瀷为了证明李滉的理气互发的合理性*蔡济恭所撰《墓碣铭》(《星湖全书》文集附录卷一)就此问题指出:李瀷“患退翁以后,四七理气之说,与朱子所解‘道心发于义理,人心发于形气’,《语类》所载‘四理、七气’有所抵牾,撰《四七新编》,发挥朱子之旨,羽翼退陶之说。”(译者按,退翁、退陶,均指李滉)。,提出了严格区分知觉与思考的公私二情论,即将人心(七情归)属于“知觉之心”(私情),而将道心(四端)归属于“理义之心”(公情)。另外,为了论证源自公私的人心道心说的合理性,通过对草木之心、禽兽之心与人类之心的对比,来分析人所具备的心之构造。*李瀷将自己的四端七情论说成是对李滉的理气互发说的转化,然而实质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论。因此我们不得不高度评价李瀷的才华。
在《心说》一文中,李瀷认为虽然土石是无心的,然而“人者,较之于草木而均有生长之心,较之于禽兽而有知觉之心。其义理之心,则彼草木禽兽所未有也”。又说:“至于人,其有生长及知觉之心,固与禽兽同,而又有所谓理义之心者。”在星湖看来,植物、动物与人类之心具有如下的分层构造:
草木仅有生长之心
禽兽有生长之心与知觉之心
人有生长之心、知觉之心与理义(义理)之心
在李瀷看来,知觉之心为人心,即人情,而理义之心则是道心,即四端。
李瀷所说的草木、禽兽、人类的进化分层的心论,其构造非常独特。显而易见,与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在内容或构造上都基本相同。另外如前所述,李瀷曾经通过《灵言蠡酌》与《天主实义》学习了欧洲哲学的心情论(三魂论)。由此可以断定,李瀷的公私心学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2) 脑囊论(大气小气说)的影响
李瀷在其四端七情论中,论述了心情的发现路径与感应路径,其发现路径由道心(四端)的理发(理直发)与人心(七情)的气发(形气发)的互发二路所构成;相对于此,感应路径则是伴随发现路径而来,两者都属于理气共发的“理发气随”一路。
李瀷指出,首先,性“感物而动”,此时生发作为“性之欲”的情(《礼记·乐记》),四端、七情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吾性感于外物而动,而不与吾形气相干者,属之理发。外物触吾形气而后吾性始感而动者,属之气发。”(《四七新编·第八》)“四端不因形气而直发,故属之理发。七情理因形气发,则属之气发。”(《四七新编·重跋》)在李瀷看来,理发意味着理的直接发动,与此相对,情的发动即气发是外物触及形气即身体,从而产生身体感觉(由外部刺激而产生的身体感觉),再传达至心,最后理(或者思考、理性)发动(可参见成于李瀷之手的《四端七情图》,即下图)。李瀷所说的气发,由触及形气(身体)而生发,故以此命名,但是从发生的主体来看,则依然是理发而已。
在李瀷看来,心的发现路径虽然有理发(理直发)与气发(形气发)两路,但是紧随发现路径而来的感应路径则只有理发气随(理应气随)一路。他说:“理发气随,四七同然。而若七情,则理发上面更有一层苗脉。所谓形气之私是也。”(《四七新编·重跋》)“心之感应,只有理发气随一路而已。四七何尝有异哉!”(《答李汝谦庚申》)关于星湖心学的“心发”构造,可以表示如下:
四端=道心(道德的情感)理发气随
七情=人心(由知觉而生的情感)生于形气之私→理发气随
须注意的是,在李瀷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的心发说当中,就发现而言,讲的是理气互发;就感应而言,讲的则是理气共发。表面看来,这似乎有理论上的矛盾,实际并非如此。李瀷指出,七情气发之气是指形气,与理发气随之气并不相同;所谓七情之气发,是指理发气随的知觉依形气而发。他说:“气有大小。形气之气属之身,气随之气属之心。形大而心小也。”(《答慎耳老辛酉》)这是说,形气(一身混沦之气)与心气(神明之气)有大小差异以及灵妙上的不同,而其作用也是根本不同的。
如前所述,李瀷通过分析《主制群征》所说的西洋医学知识,了解到气有大小粗细,而大小不同则导致各自机能的差异;断定感觉与思考是来自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上述两个命题,都与星湖的人心道心论非常吻合。星湖在建构其公私心学之际,很有可能是援用了这两个命题,以此作为其思想的前提。这是因为心发的发现二路与感应一路之模型,即“知觉之心”的一身流行的形气为大,“理义之心”的心气为小,同时感觉与思考是来自不同作用部位的精神能力,这完全可以对应于西欧的医学理论。
4. 中西会通与西学的理论优势
李瀷作为朱子学者,他坚信儒学在整体上的正确性(“无谬性”),同时作为西学者,他所追求的是在更高层次上统一中西两学,即17~18世纪西学研究者共同的理想“中西会通”。因此在他的论述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即从东亚视角出发,来实现东西理论的无矛盾统一,并以经学理论为优的立场来加以整合或折衷。在上述四端七情论及其论文《天行健》和《跋职方外纪》当中,我们便能看到这样的主题。
(1) 《天行健》
《星湖僿说·天地门》中的论文《天行健》根据《易经·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说明西欧传来的天动说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此天动说认为,月轮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轮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三垣二十八宿天、宗动天等等,都是围绕宇宙中心的不动的地球而公转的。
李瀷认为,《广雅》载“天之距地二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则说“五亿三千三百七十八里有奇”。两种说法,何者为是,尽管今天难以确定,但是两说都主张天是巨大的物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天既然是巨大的物体,因此不可能一日一循环(“一日一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中国战国时代的庄周即对“天动”提出疑问,其曰“天其运乎?地其处乎?”(《庄子·天运》)因为在理论上,即便是“地动”说,也能很好地说明天文现象。
但是,中国宋代朱子对于同样的问题,指出“亦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而转耶?”即天一日一转,地亦随之而转,而不及天运一度*《星湖僿说·天随地转》中指出:“朱子曰:‘亦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而转耶。’其意若曰:‘天一日一转,地随而转,不及天一度也。’”这是天地两动说。,最后说“今坐于地,但知地之不动”(《朱子语类》卷八十六)。*《朱子语类》卷八十六载:“想是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李瀷的引用,则将语句倒了过来。无疑地朱子认为“天与地俱转”。但是,对于朱子的天地两动说,李瀷指出“天与地俱转,地亦坠下矣”,以此证明朱子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朱子的观点(据星湖,特别是对“地动”说的否定)亦须深入思考。
进而言之,圣人著述的《易经·乾卦·大象》中有“天行健”之说。据此,由于“圣人无所不知”,因而所谓“天行健”,即指天之自动而不容怀疑,李瀷指出:“可信且从之”。
清华大学法学院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法律顾问王晨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最近这三年,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业内肯定,这为提升药品行业的生态环境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要看到,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药品临床试验和注册上市的监管方面。他说,改革应当进一步扩展到药品生产、经营、使用方面的全生命周期监管。
要之,李瀷根据经书中“天行健”一句来驳斥科学命题的“地动”说*《易经疾书》就《乾卦·大象》中的说法,指出“地圆九万里,一日一周,已是难矣”,明确否定地动说。,竭力宣扬当时已成西学定论的“天动”说。
(2) 《跋职方外纪》
《星湖全集》卷五十五《跋职方外纪》,以《中庸》的子思语为根据,主张地圆说的合理性,也提出了同样的论述。《职方外纪》是由意大利人耶稣会士艾儒略增译、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1557~1626)所汇编的五卷本世界地理书,完成于明天启三年(1623),收于明末天主教三柱石的另外一人李之藻(1565~1630)编纂的《天学初函·理编》。
李瀷的《跋职方外纪》,开首便引用了《中庸》第26章的“地,振河海而不泄”。*《中庸章句》注曰:“振,收也。”李瀷指出,子思的说法(前半部分)意味着,并非海洋在陆地中漂浮,而是陆地纳大海于自身。即便在溟海或渤海之外,海洋必然有底,其底部皆为陆地所构成。这与西洋人详细论证的说法相契合,没有丝毫差异。
大地将海洋收于其中而海水不外泄,这是因为大地处于天圆的中心位置。由于天由东向西一日一周,所以处于天之运转中的物体,势必因其向心力的作用,而不得不向中心集中。即所谓“在天之内者,其势莫不辏以向中”。地既不下坠也不上升,上下四周皆以地为下、以天为上,其原因是一样的。*李瀷亦指出,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但近海而不往下流注,北海未尝干涸,南海未尝增益,这是因为海洋都处于地之上而且皆以天为上的缘故。
由海洋是附着于陆地的观点,便不难推出“地圆”的命题。因为若向西航行至极,终究将再次进入东海(即所谓“航海穷西,毕竟复出东洋”)。而且,如果在航海的途中观察星象,由于观测地点的不同,天顶亦各有差异,因为南界星可以在低纬度看见,而无法在高纬度看见。
《职方外纪》记录了西洋人真实的航海记录。例如其中记录了阁龙(哥伦布)寻找到东方大地(实际是美洲,卷四“亚墨利加总说”),墨瓦兰(麦哲伦)由东洋(实际是美洲)到达中国大陆(实际是亚细亚的马鲁古),绕地球一周(卷四“墨瓦蜡尼加总说”)等等。了解到麦哲伦环球一周的事实,则“子思之指,由此遂明。西士周流救世之意,不可谓无助矣”。
李瀷根据子思的话,否定了“天地载水而浮”(张衡《浑天仪》)的传统浑天说/天圆地方说,由此展开论述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但是,李瀷的理论也有含糊之处。因为如果反过来看李瀷的说明,也许以下的说法反而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即以源自欧洲的地圆说为依据,来揭示《中庸》第26章中的一句话里所隐含的意思,以此否定了传统的浑天说/天圆地方说。《中庸》第26章的这句话只是说“地振河海而不泄”,然而根据李瀷的观点,所谓“地振河海而不泄”就是指“地圆”,这一理论相比“天行健”即“天动”的说法,更是一种强辩而已。
(3) 西学优越说
李瀷在进行东西科学理论比较研究之际,虽以实现两者的无矛盾统一、以经学理论为优的融合/折衷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并没有将儒学/朱子学作为审视标准而让其发挥强烈作用。当他面对异端的西欧科学理论的绝对优越性之际,他承认传统科学存在缺陷,并向本国的知识人简要说明了西欧科学的内容及其先进性。例如阐释日月蚀发生原因的《日月蚀辨》以及说明东西岁差、南北岁差的《跋天问略》等便是此类著作。
李瀷特别赞赏传到东方的欧洲星历象数之学,主张西欧科学确实优于东亚的传统科学。例如除《日月蚀辨》、《跋天问略》等以外,他在《星湖僿说·天地门》的《中西历三元》中指出:“西国之历,中国殆不及也。泰西为最,回回次之。”同样,在《历象》中,他也指出:“今行时宪历,即西洋人汤若望所造。于是乎,历道之极矣。日月交蚀,未有差谬。圣人复生,必从之矣。”这些说法都表明了他的西学优越说。另外,在他的论述中,虽然没有明言西学的优越,但是以其优越性为前提的论述其实也非常多。例如《北极高下说》、《论周礼土圭》、《地毬》等等都是如此。
从西学优越说的立场来看,笼统、含糊地主张东西一致,其实这种主张无非是一方面承认西学的相对优越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儒学/朱子学当中也有类似之说。在李瀷的科学论当中,西学优越性是默认的逻辑前提,而以李瀷为代表的东亚西学研究者的中西会通论则应理解为这样的理念或思想潮流的结果,即18世纪以来显著的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的宏观宇宙论乃至范式转换所带来的结果。
二、 洪大容的学术
洪大容字德保,号湛轩,祖籍为京畿道南阳,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实学家之一。*本部分原为川原秀城《朝鲜数学史——朱子学的展开及其终结》(《朝鮮数学史—朱子学的な展開とその終焉—》,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第4章“3.洪大容の价值相对主义”中有关朱子学与社会思想的论述,在此略作补充。关于具体的科学知识,亦可参见此书。
1. 燕行与思想革命
洪大容生于朝鲜朝英祖七年(1731),比李瀷大约晚50年。两人不仅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环境,甚至教育环境都不相同。与李瀷出身南人名门不同,洪大容出身老论世家。另外,洪大容于英祖十八年(1742),有志于“古六艺之学”,列入栗谷李珥→沙溪金长生(1548~1631)→尤庵宋时烈一系的金元行(1702~1772)之门下,属于朝鲜朱子学两大学派——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中的栗谷学派,这意味着他是以李珥为楷模来从事朱子学研究的。
洪大容自英祖三十五年(1759)到三十八年(1762)左右,制作了浑天仪。英祖四十一年(1765),随冬至使节赴中国清朝的京师(燕都)。第二年,访南天主堂,与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会谈,还与杭州读书人严诚、潘庭筠、陆飞进行了学术交流。回国后,提出“应向中国(从北方)学习”(北学)的主张,朴趾源等人也表示认同。英祖五十年(1774),荫补为世孙翊卫司侍直官。后历任泰仁县监、永州郡守等职。正祖七年(1783)去世,享年53岁。
(1) 洪大容与朱子学
洪大容的实学思想即燕行后的思想,看上去是与朝鲜两班思想不同的价值相对主义,富有批判精神,较诸李瀷更进一步地摆脱朱子学的束缚,从其规范当中释放出来而获得了自由。但是燕行前,洪大容则完全固执于看似老论领袖宋时烈等人的以朱子学为独尊的立场。
例如,根据《湛轩集》外集卷三《乾净衕笔谈》1766年2月23日的记载,洪大容面对王阳明同乡的中国知识人,断然指出:
愚未见陆集,未知其学之浅深,不敢妄论。惟朱子之学,则窃以为中正无偏,真是孔孟正脉。子静如真有差异,则后学之公论,无怪其摈斥。
可见,他对于陆学及阳明学等所采取的似乎是不屑一顾的态度。
但是燕行之后,这种固陋的想法变得隐晦起来。根据《湛轩集》内集卷二《桂坊日记》1775年2月18日的记载,东宫(后来的正祖)对于洪大容思想中不受学统之拘限的富有弹性的理气之解表示了赞赏:
桂坊(洪大容)之言甚确,观此言则桂坊似不为固滞之论。*问答如下:“令曰:‘然。性理最难言。吾意果主于不相离,而乃云兼知觉为性,则不免语病矣。若理气先后,当云何如?’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则是气先理后否?春坊或言气先,或言理先。臣曰:理气先后,自来儒者各有主见,而若《中庸》注说,亦非谓成形而后理乃赋焉。臣则以为有则俱有,本不可分先后。盖天下无无理之物,非物则理亦无依着也。’笑令曰:‘其言甚好。如是看最无弊。’顾春坊而再三称之。臣曰:‘此非臣之创见,即朱子说也。’令曰:‘虽然,理气说虽讲之烂熳,于身心日用,终未见切实。’臣曰:‘睿教甚当。日用当行之事,切问而近思,随事体行,则性理亦非别物,即散在于日用。及其知行并进,则一原大本,性与天道,可以豁然贯通。初学之坐谈性命,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令曰:‘此言极是。以子贡之颖悟,晩年始闻性道,则初学尽不可躐等。桂坊之言甚当。观此言则桂坊似不为固滞之论。’”
这表明洪大容在燕行之后,其思想信念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思想革命
洪大容燕行前后思想信念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要指出其变化的具体内容则并不容易。因此,本文将分析的重点,集中于《诗经·小序》与朱子《诗集传》解释的关系,看一看经过与杭州读书人的讨论,洪大容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洪大容燕行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与耶稣会传教士鲍友菅的笔谈。耶稣会士引起的思想革命,详见川原秀城:《朝鲜数学史——朱子学的展开及其终结》。
以下的分析意在表明,通过与思想信念不同的浙人笔谈,洪大容对于构成自己思想基础的朱子学产生了一些怀疑。
根据《湛轩集》外集卷二和卷三《乾净衕笔谈》的记载,洪大容与浙人围绕朱子《诗集传》究竟应如何评价进行了讨论,这场讨论始见于2月8日严诚(字力闇)的记录:
力闇曰:“朱子好背《小序》。今观《小序》甚是可遵,故学者不能无疑于朱子。本朝朱竹坨(朱彝尊)著《经义考》二百卷,亦辟朱子之非是,而自来之论,亦谓朱子好改《小序》,殆出于门人之手。”
严诚吸收了当时清朝知识人的朱子学批判,主张应当重视《诗经·小序》(诗序),并批评朱子在编撰《诗集传》(修订本,即今本)时,取郑樵之说,以为《小序》为乱经之元凶而将其删除。这是对拘泥于《诗集传》的攻序派而进行的批判。
对此,洪大容于2月10日写了反驳严诚的书信(《与力闇书》):
其破小序拘系之见,因文顺理,活泼释去。……乃其深得乎诗人之意,发前人所未发也。……至若《小序》之说,则愚亦略见之矣。……全不成文理,此则朱子辨说备矣。盖其踏袭剽窃,强意立言,试依其言而读之,如嚼木头,全无余韵。其自欺而欺人也,亦太甚矣。……若以《集注》谓非朱子手笔而出于门人之手,则去朱子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先辈之世,讲明若烛照,虽为此说者,岂不知其为朱子亲迹,而特以举世尊之,强弱不敌,乃游辞伪尊,软地插木,为阳扶阴抑之术也。
不过,严诚回应2月10日的《与力闇书》是在2月23日。严诚对于洪大容的反驳,仅冷淡地吐露一句:“《小序》决不可废,朱子于诗注实多蹈驳,不敢从同也。”而且潘庭筠也站在严诚一边,指出:“朱子废《小序》,多本郑渔仲。”此外,陆飞也指出:“老弟宗朱,极是。然废《小序》,必不能强解也。”并在介绍马端临的说法之同时,指出朱子《诗集传》的不足,而且作出如下结论:“鄙意朱子注书甚多,或不无门人手作。”三人的主张都是基于当时新兴的清朝考据学的成果,并无丝毫过激之处,然而洪大容却回应道:“此不可以口舌争。请归而详览诸教。或有妄见,当以奉复也。”表示无法认同这样的主张。
到了2月26日,洪大容用预先准备好的文章来展开自己的观点,不过跟以前一样,他反复强调:“诗之扫去《小序》,为其最得意处,而大有功于圣门矣。及闻兄辈之论,不觉爽然,而自失矣。”严诚等三人对洪大容的反驳又进行了再反驳,据说是“酬酢颇多”。
但是,论战的结果却是洪大容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失败,向三人表示了自己内心想法的变化:
东国知止有朱注,未知其他。弟之所陈,亦岂敢自以为不易之论耶。至于《小序》,一读而弃之,不复精究。当于归后,更熟看之。
据《乾净衕笔谈》的记录,论战获得圆满结束,据称“诸人皆有喜色”。
洪大容通过与中国清朝知识人的笔谈,接触到新学问的一角,引发了自己的思想革命,开始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作为自己思想基础的朱子学,尽管只是局部的批判。
这类批判在《毉山问答》一书中有显著的表现。虽然他还奉行老论一系的朱子学,然而另一方面他对朱子学末流之弊表明了对决的姿态,并企图加以改革,此即燕行后洪大容的思想立场。这也就是为何在他的思想主张中,并没有朱子学者常见的那种道学式的固执与独断的毛病。
换言之,持价值相对主义立场的洪大容的思想就是在信奉朱子(宗朱)与批判朱子(攻朱)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的基础上而得以成立的。
2. 基本思想
洪大容的基本思想即燕行后的思想与李瀷相同,其特征是在宗朱与攻朱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若对其思想特征进行归纳的话,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批判形式化、空洞化的朝鲜朱子学,立足于朝鲜的现实,主张实用的实际学问(实学)的必要性;
第二,支持中国清朝的善邻对外开放政策,主张必须积极地吸收清朝先进的文物学术(北学);
第三,提出“以天视物”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
(1) 实学
不过,上列第一的“实学”观,很有可能是受其恩师金元行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是因为根据《湛轩集》内集卷四《祭渼湖金先生文》(1772)的记载,洪大容曾经得到金元行的如下教诲:
问学在实心,施为在实事,以实心做实事,过可寡而业可成。
另外,《湛轩集》外集卷一《答朱郎斋文藻书》(1779)中则提到:
吾儒实学,自来如此。若必开门授徒,排辟异己,阴逞胜心,傲然有惟我独存之意者,近世道学矩度,诚甚可厌。惟其实心实事日踏实地。先有此真实本领,然后凡主敬致知修己治人之术,方有所措置,而不归于虚影。
可见,洪大容的实学观并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为了追求真正的朱子学。
(2) 北学
上列第二的“北学”即主张必须积极地学习清朝先进的文物学术,重视清朝文化。洪大容通过自身的燕行经历,将此主张付诸实践。从其实践的事实来看,或许与其个人的资质有很大的关联。例如洪大容学习掌握了中国语(北京话)的会话,尽管可能并非十分熟练;另外,他与那些从朱子学(名分论)的立场出发而对辫发感到羞耻的汉族知识人也有深入的交流。
洪大容所追求的与异民族的宽和交往,其结果正呼应了中国清朝的善邻对外开放政策。批判了基于朝鲜朝老论的朱子学(华夷论)的非现实的清朝敌视政策(北伐论),这就意味着宋时烈所提倡的固陋狭隘的自尊自大之政策的失败。归国以后,老论主流派的北伐论者(金钟厚等)批评洪大容与清人的交往乃是违反了朱子学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交友方式,若从当时两国外交的形势来看,这类批评可以说是必然的反应。
(3) 以天视物
关于第三点,即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毉山问答》与《林下经纶》当中。其中,洪大容阐发了自己的基本观点:
以人视物,人贵而物贱。以物视人,物贵而人贱。自天而视之,人与物均也。(《毉山问答》)
主张人类中心的价值观是不足取的,而构成其“人物均论”的基础则无非是“以天视物”这一观点。所谓人物均论,与其所属的老论、洛论的人物性同论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且不论他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不过正如以往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应当承认他的人物均论确是受到了人物性同论的影响。
此外,洪大容并没有将“以天视物”设定为人与禽兽草木的本质差别,而是将其价值相对主义观点应用于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理论,其因在于他拥有“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的观点。他的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
孔子周人也。王室日卑,诸侯衰弱,吴楚滑夏,寇贼无厌。春秋者周书也,内外之严,不亦宜乎。虽然,使孔子浮于海,居九夷,用夏变夷,兴周道于域外,则内外之分、尊攘之义,自当有域外春秋。此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这是主张从华夷论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批判歧视异民族,此即所谓“域外春秋说”。此外,洪大容由这样的观点出发,梦想建立基于能力而没有身份制的万民皆劳的社会(《林下经纶》)。
3. 价值相对主义与西学知识
燕行后的洪大容,就生活在思想与现实或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矛盾纠结中,并在趋向不同的两种张力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可以推断此即洪大容价值相对主义得以形成的缘由。不过,《毉山问答》一书所披露的价值相对主义,并不是消极的、脆弱的,而是充满着倡导实学以及全面否定虚学的毫不动摇的自信。其充满自信的原因在于,他的思想主张有着坚实的理论依据。
(1) 地球说与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
据洪大容《毉山问答》,若要问人类社会之当为与价值相对主义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何在,则无外乎起源于欧洲的科学知识*洪大容先于他人吸收了西欧科学知识并应用于自己的社会思想,但是其科学理论本身基本没有独创性的见解。朴星来在《洪大容〈湛轩书〉中的西方科学之发现》一文中指出:“严格地说,他的主张几乎没有独创性”(韩国《震壇学报》79,1995年)。,即地圆说与第谷·布拉赫的宇宙体系。这是因为“人物之生,本于天地”。
洪大容认为大地是由球形所构成的:
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
另外,他以第谷的宇宙体系思想为依据,指出:
满天星宿,无非界也。自星界观之,地界亦星也。无量之界,散处空界。惟此地界,巧居正中,无有是理。
这是说,不能将地球看作宇宙的中心(“空界之正中”)。
(2) 价值相对的社会理想与天地的相对性
洪大容利用西欧的科学知识,揭示了天地的相对性,进而提到“人物之本”、“古今之变”、“华夷之分”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地球也非宇宙的中心。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没有必要以中华为贵,也没有必要遵从华夷秩序。
毫无疑问,洪大容坚信本国未来遥远的前途、提倡价值相对主义的社会理想,他的这种心情定能超越时代传达给读者。价值的相对化是必然的。
若对以上所述用命题化的方式作一归纳,那么可以这样说,诱发出洪大容的价值相对主义社会思想,是由于跟中国知识人的真心交流,但是其理论支撑则是传播到东亚的崭新的欧洲数理科学知识。
三、 小结
李瀷与洪大容,将倭乱、胡乱之后显现的朱子学相对化推向极致,是朝鲜朝后期代表性的实学家。可以说他们在学术上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将朱子学与西学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若要对朝鲜朝后期实学思想的展开作一推断,无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朝鲜实学不仅与朱子学的学统相关,而且他们个人也是发自内心地尊敬朱子的学德,并以李滉或李珥为楷模,来从事朱子学研究。与此同时,又受到朱子学改革主义的影响,或者因燕行而发生思想革命,导致他们开始对朱子学作一番相对化的尝试。而引发相对化的无疑是理义。在尹东奎所撰的《星湖行状》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瀷)如其义安则不规规于人己,理得则不切切于毁誉。勇往直前,不顾傍人是非。”这个说法生动地描绘出李瀷等实学家重视理义的研究态度。无疑地,实学家一方面要注意不能大幅度地越出朱子学的架构,另一方面又乐于追随理义而自由地思索。
其次,在追求理义的过程中,他们与西学相遇,这就极大地扩展了实学的视野。与擅长于实用与逻辑的西欧科学的邂逅,其影响尤其之大。实学家经历了由西学东渐而导致的18世纪东亚的宏观宇宙论(cosmology)的转换/变化,并受到西学魅力的影响而开始了真正的西学研究。在西学当中,西欧科学之实用性且又精致的理论,使得这些实学家自觉到自己视野的狭窄,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刺激。通过热心地研究西学,其结果使得实学家获得了新的学问路径以及新的知识世界。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异端持宽容态度的反朱子学的研究方法:即便是异端,只要其中有可学习之处,便应毫不犹豫地加以学习;也是强调中西会通,即强调经学理论为优的朱子学与实学以及西学之间的理论整合与折衷。实学家在西欧科学由微至细的学习/刺激之下,对传统学风进行修正,从而建构起自己的学问构架。
(申绪璐译,吴震校)
[责任编辑晓诚]
A Study of Pragmatists’ Zhuxi Learning in Late Joseon
Kawahara Hideki
(TokyoUniversity,Japan)
Abstract:In the aftermath of Japan and Qing invasion in the late Joseon Kingdom, two kinds of thought in the Zhuxi learning with the two representatives of Joseon pragmatists Yi Ik (1681-1763) and Hong Dae-yong (1731-1783)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On the one hand, the “Zhuxians” were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ir intense sense of orthodox ideology and being intolerant toward heres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ctively studied the heresies from the West and incorporated them into the system of Zhuxi learning. In fact, the West learning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Joseon pragmatism. Yi Ik changed the narration of “four sprouts and seven kinds of feelings” via both the Aristotelian tripartite division of the soul and the European medical doctrine which took the brain as the thinking organ. He also tried to combine all the doctrines of Zhu Xi and the Western theories consistently.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the earth being round and the Tycho system of the cosmos, Hong Dae-yong challenged the China-centered or earth-centered Zhuxian doctrines and developed his relativist theory of value. The relativization of late Joseon pragmatists revealed the changes in cosmology due to the 18thcentury Western expansion of knowledge into the East.
Key words:late Joseon; pragmatism; Yi Ik; Hong Dae-yong; value relativism
[作者简介]川原秀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