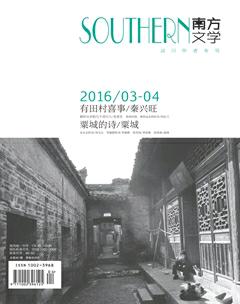我所认识的几个灵川人
毛荣生
桂林十二县,我到得最多的一个县就是灵川。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灵川离桂林市区最近,很方便的,若开车去,半小时就到了。二是灵川的狗肉好吃,好吃的东西别说近,就是很远的地方我们也会想方设法找了去。前些年,我们几乎是隔三岔五就要去一次灵川,不为别的,就只是去吃狗肉。
灵川去得多,认识的灵川人也多,林林总总,各行各业,或官或民,或老或少,都打过一些交道,都有些印象。要为《灵川文艺》写篇东西,一时不知写什么,就写几个我所认识的灵川人吧。
一
说到灵川自然要说狗肉,说到狗肉,就自然想起我认识的一个灵川人,原来灵风餐馆的苏老前辈。我最早去灵川吃狗肉,就是慕名到灵风餐馆,而且不是别人请我去,是自己找着去的。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那时我在《桂林日报》副刊当编辑,我们开了个栏目叫做《好吃轩》,由我负责编辑。这个介绍美食、餐馆的栏目,在那些年很有些影响,我自己就写过好些这方面的稿子。听人说——具体说是听苏理立老师说的,说灵川有个狗肉店叫灵风餐馆的,做的狗肉很地道,自然就想到要去品尝一下。
记得那是个初冬的早上,我和我们副刊的李超英编辑一起,坐着公交车到了灵川,找到了灵风餐馆。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苏老前辈,坐下来就先点了两斤狗肉。等了一阵子,见一瘦高个的老者过来,满面笑容,主动和我们聊起天来。就晓得了他姓苏,这个店是他开的,也晓得了最近店里生意很火,每天食客都是坐得满满的。聊起狗肉经,他很有心得,讲起来一板一板的。说了灵川狗肉的特点,说了他所烹制的狗肉的特点,包括狗肉应该怎么吃才更有味道,甚至包括他对灵川狗肉经营的理念。苏老板很能侃,讲得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我和超英有时不得不把筷子放下来听他讲。在聊天时我们也晓得了苏老板是国家干部,好像早年曾参加过什么军政大学的学习,也算是个老干部了。
那天回去后我就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来一锅狗肉,去几分烦忧》。稿子见报后应该对灵风餐馆的生意很有好处,光是我和超英的朋友,就有很多人向我们打听这个店,说要请人去吃狗肉。虽然写了这篇稿子,但说句实话,那天我们吃的狗肉,餐费和路费都还是自己出的,而且为此我们还自费请过一些朋友去那里。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苏老前辈也已不在,但当年那个初冬我和超英在灵风餐馆时,他对于狗肉津津乐道的样子,现在都还记得。在这里不对苏老板作任何评价,其实我和苏老板的接触,也是缘于狗肉,止于狗肉的,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在此也不对灵风餐馆作什么评价,因为灵川的狗肉经营业名店百出,我不是此道中人,无从说什么。只是记得苏老板对于狗肉的热忱和执著,也记得灵风餐馆当时火过一阵子,这一点我的印象一直很深。从那以后,我看到灵风餐馆一步步做起来,在灵川县城开过一个很大的店,后来又在桂林市区的依仁路开过一个店,再后来好像就是他的儿子开的一个什么店,我不太了解,印象就渐渐淡漠了。
桂林有很多朋友都因为狗肉而认识苏老板,现在还经常有人聊起他,聊起灵风餐馆。记得那一年苏老板病重,住在市中医院,我还去医院看过他。在病房里他仍然谈狗肉,还是很执著的样子。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苏老板,是想说以苏老板的经历,在那个年纪做一个转身,而且做得那么执著,那么热忱,是十分不易的。我认识灵川很多朋友,有做大事的,也有毕生只做小事的,但都很执著,很热忱,这种执著和热忱,体现在只做小事的人身上,尤其难能可贵,这也就是我对苏老前辈的一个评价吧。
二
在我所认识的灵川人之中,我最为敬重的一位就是廖江老先生。我和廖老,认识很多年了,但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见面的原由,一是他到报社来送稿子,二是他到报社来找其他的同事,三是我到灵川参加一些活动遇到。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要聊上一阵子,而且每次聊天,我还都有所受教,有所收益,听到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了解到一些原来不了解的东西。
我对廖江老的印象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变,我觉得这是一位学养丰厚,勤勉严谨,宽和厚道,为人谦恭,颇有长者风范的人。说不上很了解,看过或编过他写的一些文章,大多是写灵川的,人文风物,历史沿革,传说掌故,乡土人情,掌握的资料都很丰富,很厚重,有些甚至是第一手的资料,这就很了不起。写这一类文章,资料第一重要,这大家都懂,但二手的资料或大路货的资料,往往给别人用过,甚而一用再用,写出来至少就没那么新鲜了。而廖江老所写的东西,好像每一次都有很新鲜的材料,就凭着这些新鲜的材料,人们就会想读这篇文章。关键是廖江老在对这些资料作研判、取舍、铺陈、点染时,所取的态度始终是严谨而细致的,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但我从那些篇什和字里行间中,还是可以看出廖江老的深厚学养,也看得出他对历史、对乡土,对乡亲、对后学者所端出来的一副负责任的态度。廖江老的文字厚实而干净、活泛而平实,但就在这看似平实的文字中,我每每感到作者对所写东西的钟爱和热情,这一类文字的出彩,资料是骨架,考证和推衍是经络,叙述和描写是血肉,而其中的灵魂却是作者的一副赤诚之心,这才是最能感召读者的关键所在。能对自己所写的每一篇文字负责任,不敷衍、不取巧、不虚张声势,不以讹传讹,这样的文字才能留存下去。个人认为,廖江老的文字就是这样的文字。
实话实说,我对灵川的作者群说不上了解,也没有大量地研读过廖江老所写的东西,这些看法,全是零零星星地积累下来,又很随意地写出来的。不过,每当有人说起灵川甚至桂林,说需要了解某些方面的东西时,我总是会顺口推荐,说找廖江老先生问问最合适了。我不想把“活地图”、泰斗、专家这样的桂冠戴到廖江老的头上,这是个很低调的老人,维护低调老者的低调,是后生晚辈对其最大的尊重。
我和廖江老接触不多,其敬重的感觉除了来自人们说起他时所取的态度外,更多的是从每一次的见面或交谈中得来。我当副刊编辑多年,廖江老也为我所编辑的副刊写过很多稿子,其实稿子邮寄过来就行了,但他常常是亲自从灵川过来送稿子,而且每次见面,无论是聊天还是具体谈到稿件,他都是十分认真,十分谦恭的样子,这让我每每感到承受不起。尤其感到惶恐的是,他总是称呼我为“毛老师”,为此我郑重地纠正过多次,说廖老您千万别这样称呼,我一个后生晚辈,承受不起的。但没有用,他还是称我为“毛老师”。廖江老的谦恭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位长者的敬重,在认识老先生的这些年里,这种敬重一以贯之。
我现在也已渐渐成为一个老者,我并不是一个很摆谱的老者,但我真的不敢肯定,自己在后生晚辈面前,是不是能够始终持一种谦恭的态度。其实,对生活谦恭、对天地谦恭、对所有人谦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持有的一种人生态度。始终能够谦恭做人,做到老了仍不改其宗,这样的长者才担得起后生晚辈的敬重。
三
吕兄金华,灵川人氏,学的是艺术,做的是新闻,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县里当过文化局长,他说那几年整天带队催粮抓赌搞计生,有点烦了,所以漓江日报社成立时,他就弃官而去,当了一名副刊编辑。后来“官”却不弃他,先是主任,后是桂林日报社副总编辑,现为报社调研员。
大家都懂得,新闻官不易做,有很多纪律,所谓“无冕之王”,无冕可以确定,但是否为“王”还两说。吕兄毕竟是“老革命”,当了新闻官,还是很守纪律的,总是能保持一致,讲政治,顾大局,负责任。但他毕竟是学艺术的,一颗艺术之心时时澎湃。他分管了几年《桂林日报》要闻稿件的审签工作,做的虽是“如履薄冰”的差事,他讲话却常常显得与众不同,花样常新,既遵守了纪律,又张扬了个性,往往赢得一片笑声,觉得有道理,更觉得有趣。
举一个例。有一次有个破案的稿子,案件说不上有什么离奇,破案的过程也算不得很有特点,但标题却做得有些“大”,记得是“公安民警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之类。其实这样写也无可厚非,破案肯定是要花些心思和劳力的,吕兄却不这样看,他在稿子上顺手写下一个评语:“既无智,又不勇,何来斗智斗勇?”就把稿子退了回去。这篇稿子本来我是没注意看的,但听了吕兄的这个评语,觉得十分有趣,看过后觉得确实评得有理。
那几年他负责每天评报(将报纸挂上墙,直接在上面评点),对一些假大空的东西他深恶痛绝。记得有一天二版见报了一张图片,是某单位集体到一个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的照片,几十个人笑眯眯地站成整整齐齐的三排,他一看就来气,大笔一挥,写道:“看图片是纪念照,看说明是喊口号,如此红色旅游,还是少发为妙!”像这样犀利而有趣、入木三分的评报,成就了吕兄评报的独特风格,也成了记者编辑们每天必看的趣味节目。
吕兄工作多年,他的能力、业绩都不是我等可以去评价的。他的画和硬笔书法颇佳,出过集子,在此也不细评。这里只说他在坊间流传的一些“经典语言”。搞艺术的人都生性幽默,吕兄也如此,和他相处,说话不用遮掩,可开的玩笑没有边界(当然底线还是有的),说过也就说过了,无伤大雅,哈哈一笑,风吹过了。只是有些故事却没有被风吹过,吕兄的有些话,就在坊间流传开来。
话说本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哥,年轻时眼睛近视,但一直没见他戴眼镜。有一次吕兄和他一起去安徽凤阳开会,那天下午站在桥上看风景,老大哥这次戴了一副眼镜。吕兄看见,无意识地取过来往自己鼻梁上一戴,突然脸都青了,只听他一声大吼:“哇,这世界哪这么清楚的!”接着感慨道:“总以为天地那样浑沌,却原来世界如此清楚!”这一刻,吕兄才知道自己多年来一直近视,于是,三步并作两步急冲下桥,到菜市边眼镜摊上花8元购得眼镜一副,从那以后就戴上了眼镜。“原来世界如此清楚”也成为朋友们经常调侃吕兄的话。
每年年终的述职从来都是很重要、很严肃的事情,有一定的程序和格式,语言一般都比较规范。但在我的记忆中,我这一辈子所听过的最有特点、最不规范、最不靠谱,或者说最出彩、最有新意、最好玩的述职,就是吕兄的述职。述职的文本结构新、所举例子新、语言表述新,至今不能忘记。那天,吕兄从容登台,拿出文稿,很淡然地望望台下200多位员工,缓缓开口说道:“很惭愧,因为工作忙,一年来没有读过一篇马列著作……”此语一出,四座皆惊,接下来是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不得不说,这笑声和掌声也是不规范的,包括我自己的笑声和掌声。还有一年述职,他说,因为一年365天,天天看稿审稿,就像验钞机,工作没有新意,我拿的这《述职报告》就像是去年的“重稿”。吕兄的述职被认为是述职会上的一朵奇葩,他这样的述职我们听了几年。只是后来,规范多了,大家不免有点遗憾和想念。
吕兄在酒桌上有“话比酒多“之名声,有人这样形容他来敬酒时的样子:举着大半杯酒晃过来,话过一巡,已泼掉三分之一;和人碰杯后,有意无意又泼掉三分之一;如果再想起一句什么精彩的话,做个夸张动作,手上杯子偷偷一歪,酒杯里是否还剩三分之一就难说了。有一次他带队去湖南学习,当地报社请我们吃饭,中午喝完晚上又喝,楚地之人十分了得,我们一行实在不能抵挡,人人自危,自然就没人帮领队的吕兄挡酒或代酒。在过不了这个坎时,吕兄无奈地仰头长叹:“领导就是拿来出卖的。如此不团结,一盘散沙,队伍难带啊!”
大家都说吕总是个好玩的人,绝对的性情中人。他并不耍贫嘴,却幽默、风趣、信马由缰,不拘一格。所以尽管他“话比酒多”,大家还是很喜欢和他喝酒。
人生几十年,认识的人很多,认识的灵川人也很多,信手写来,很随意的,没什么考虑,就写了这几位。写完想想,其实灵川可写的东西很多啊,让能者去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