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之子与光的暴力
——《夜颂》与灵知主义( 上)
胡继华
忧郁之子与光的暴力
——《夜颂》与灵知主义( 上)
胡继华
奇异,诡异与灵异——《夜颂》印象
诺瓦利斯(Novalis,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的《夜颂》(Hymnen an die Nacht)以诗艺开启了人类心灵上达之道,又指点了人类生命下行之途,更是预示着灵知的回归之路。用著名“超心理学”理论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的专门术语,我们不妨说,《夜颂》上溯空性(evolution),下及万有(involution),①将缥缈无形而威力无比的“灵知”写入浪漫化的象征体系之中。两个多世纪以来,《夜颂》令人一读觉得“奇异”,二读觉得“诡异”,再读觉得“灵异”。“奇异”之处在于,《夜颂》不仅代表诗人哈登伯格诗艺的巅峰,而且为浪漫主义抒情诗提供了难以逾越的诗艺范本。“诡异”之处则无所不在,诗人将黑夜作为歌咏的对象,将死亡作为抒情的至境,在黑暗与光明交替的节奏中安置个体心灵和人类精神。诗人以自然象征主义为手段,重构了“进化的宇宙诗”:从物性到生命,从生命到心灵,从心灵历史,从历史到灵知,渐渐进化,永无止境,诗兴流韵。至于诗篇的“灵异”因素,归根到底要溯源至诺瓦利斯以及德国浪漫派的“灵知”。为了了解人类灵性的深度,浪漫主义诗哲沿着一条神秘的路,通向了内心。内心乃是灵知的寓所,因为灵知本来就不是格物而致之“知识”,而是返身而诚之“灵见”。
黑塞所言极是:“诺瓦利斯……因为一种创造性的虔敬,使他能够蔑视死亡。”②《夜颂》启示读者,唯有遭遇黑暗才有可能获得拯救的灵知,唯有虔诚地面对死亡才能蔑视死亡,从而通过死亡返观生命,引领生命走出死荫的幽谷,而亲近柔情似水的神圣(the divine of motherly water)。创作《夜颂》的诺瓦利斯向理性发起了近乎绝望的冲击,他不住地追问:在启蒙后的世代,能否建构“浪漫的新宗教”,能否复活“理性的新神话”?
然而,有一道灵知主义的缘光笼罩着诗人的呼吸,诗句的断续,修辞的节奏,意象的隐显,境界的开阖。那么,诗人的灵性,以及浪漫的灵知,来自何处呢?
一、 放逐异邦的忧郁之子——《夜颂》之灵知渊源
诺瓦利斯诗艺中的灵知,最早最明确的表达,是在《致蒂克》一诗中。诗中写到,一个“极端忧郁之子被放逐到异邦”。放逐异邦的忧郁之子探寻自我的道路,正是蓝花少年奥夫特丁根追梦还乡的道路,也就是现代灵知主义者追寻灵知的道路。德国16、17世纪之交的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Jacob Böhme,1575-1624)对诺瓦利斯后期创作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通过波墨的《曙光女神或朝霞》(“Aurora oder Die Morgenröte in Anfang”),诺瓦利斯接受了灵知主义的洗礼,而担负起复活灵知、复兴信仰和传承秘教的使命。波墨深信,原始的宗教体验蕴涵着强大的解放潜能,足以把陷入绝望与忧郁之中的人解救出来。波墨还瞩望,通过宁静泰然的新生,生命即可拥有一种灵知(gnosis),藉以揭示所有的奥秘,洞穿实在的不同层次,对历史过程提供一种澄澈的观照。波墨在后宗教改革的氛围中复兴灵知,传承密教,而他的思想被誉为“现代性最具有弥漫性的象征体系”③。史家断言,波墨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史,乃是欧洲精神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④
灵知主义的重音同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构成一种完美的应和关系。蓝花少年的矿山探险以及对自然的爱恋,说到底都是在灵知的引领下追寻隐秘的神圣奥秘。《夜颂》也是如此,诗人从光明下转于黑暗,从世俗幸福而上达神圣启示,超越个体意识而融入历史与神话,以至最后返回故乡,陶醉于神婚之中而瞻仰终极的神圣。灵知引领诗人上达与下行,远游与还乡,分离与融合,一切都是为了开启那隐秘的神圣奥秘。1800年2月23日,诺瓦利斯欣喜若狂,给挚友蒂克写信,将波墨的学说描绘为温馨而强大的春天:“那是一团充满神秘欲望和神奇生命的纯粹混沌,一个不断自我分化的真实宇宙。”那一缕预示着黄金时代回归的温馨而强大的春光,柔情似水而无孔不入地渗透在诺瓦利斯的诗魂艺魄之中。
灵知主义认为,从个体到历史,从历史到神性,每一个阶段上都发生着“融汇,区分以及整合”,渗透着一种诡异非人而上善若水的灵知。灵知将慈悲风调播撒在放逐异邦的忧郁之子的还乡路上,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生命上溯空性而沐浴着神圣之爱(agape),下及万有而享受血气之爱(eros)。两爱交融而大爱无疆,这是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及其所涵养的灵知主义所持有的共同信念。⑤通过奥古斯丁、狄奥尼修斯的默观冥证,这种
灵知主义的信念润物无声地渗透了整个基督教。故此,灵知主义和基督教兴衰交替,构成了欧洲思想史的辩证节奏。布鲁门伯格断言,作为一个思想史范畴与方法,“现代”乃是继奥古斯丁之后第二度“对灵知的超克”(Überwindung der Gnosis)。⑥在中世纪开端,第一度对灵知主义的征战无功而返,但灵知主义不仅没有摧毁古代秩序,而且将这种秩序变成了暴政。沃格林针锋相对地断言,“现代”乃是灵知主义对上帝的谋杀,或者说是灵知主义的自觉生长。“现代概念紧随中世纪降临,本身乃是灵知运动所创造的象征之一。”⑦按照这一逻辑,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以及浪漫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运动,都是灵知主义的复活、涌流、激荡以及反抗的历史运动。
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德国文化语境中,早期浪漫主义凸显了灵知主义的三个要素:善恶对立、光暗交织的精神结构二元论,异化与复归的生命辩证法,以及不断趋向于终极实在传递隐秘真理的终末论。德国观念论和浪漫派重构了灵知主义的“神话逻各斯”,描述了人与宇宙整体断裂的灾异图景。这幅整体断裂的灾异图景覆盖了神祇与世界,上帝与世界,永恒的神圣与终殁的生命,生命的内在和外在。灾异渗透之处,只见断简残篇,不见圆满和谐,一切都撅为两半,表征生命陷于绝境,一种悲剧绝对主义成为观念论的基元,成为浪漫派的元音。
浪漫主义者遥远地回应保罗:诗是造物的叹息。造物为何叹息?因为离弃了灵知,失落了整体,远离了家园,羁留于异邦。瓦伦廷灵知主义者绝望的沉思表明,宇宙的进程乃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灵知从自身分离出来,释放出一道光亮,而愈来愈沉沦到堕落的物质世界。堕落的灵知可能沉溺于物质,也可能思念已经疏远了的家园。前者乃是“下及万有”,而后者却是“上溯空性”。生命在灵知的召唤和引领下,朝着虚灵而又真实的“天光”奋力上行,则预留着一种救赎的希望。这种救赎的希望,乃是终末论的希望(eschatological expectation)。因为,堕落于物质世界而沉沦在血肉之躯的黑暗之中,灵知只有不幸,而不可能有家园感。陶伯斯(Jakob Taubes)印证古代灵知主义文献残篇,论证异化与复性的“转型神秘主义”:觉醒了的乡愁标志着已开始的复归故里。⑧
灵知把“灵”的苦难史昭示为悲剧,昭示为一位遥远的超越的造物主上帝以及陌生的完全异在的上帝的悲剧。我们不难从浪漫诗文中读出方生方死、出死入生的悲剧纠结。诺瓦利斯的《夜颂》又堪称这种绝对悲剧的典范之作。诗人在生命的极限返观生命,以死观生,将死亡视为生者朝向真正自我迈进的救恩之必然环节。作为真正自我意识的灵知,就不是理性所能澄明的思维,而是一种半明半昧的内省,一种自律接受他律的拯救行为。再度唤醒灵知,而生命因灵知的觉醒而改变,世界也因生命的更新而淑易,这就是《夜颂》以诗艺开启的“转型的神秘主义”(transformative mysticism)。诗中,一位“庄严的陌生者”穿越光与夜交织的宇宙,上行而下达,远游又复归,亲近死亡而渴望永生,让亡灵的烈火燃尽肉身,经历圣父-圣子-圣灵三约国,最后返回故乡,温柔地长眠于神圣。异乡人悲壮还乡,忧郁之子传递无限奥秘,这是《夜颂》的整体抒情架构。那么,诺瓦利斯选择何种文类形式来担负这转型的神秘主义,及其秘传的浪漫宗教呢?
二、 “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颂诗体源流略考
诺瓦利斯将他其抒情诗的巅峰之作命名为“夜颂”,这是他对于文类形式的选择。媒介就是信息,而文类形式同诗兴逸韵水乳交融,不可以人为区隔。从可以掌握到的史料看,诺瓦利斯对文类进行了悉心的比较,在所读经典之中最后选择了“颂体”,将他要传递的无限神圣奥秘托付给了这一媒介。少小习颂古典文学,尤其长于修辞与诗学,诺瓦利斯很早就将目光投射到了远古:
远古的进程柔和而伟大:一道神圣的面纱将远古掩蔽起来,使凡俗人不得窥见,可是命运从源泉的缓缓流淌中造就了凡俗人的灵魂,这灵魂凭借魔镜看见远古在神性的美丽中。⑨
这是他的断章补遗之中看似随手写下的一则笔记。仔细辨析,“魔镜”这个意象却来自秘传宗教仪式上的魔术,据称炼金术和灵知主义都利用魔镜来窥见生命的终极真实。在神秘主义者和神智论者波墨的思辨体系之中,魔镜是一个圆融的象征,人们藉着它可以窥透深渊,瞥视圆满。而人的生命也是这么一面魔镜,“上帝在哪儿凝视自己,并像在天使身上和天国领域一样,在人类身上获得他全部的光辉和能力”⑩。那么,诺瓦利斯这位自觉放逐异邦的忧郁之子,如何传递在魔镜之中窥见的神圣光源和巨大能力呢?

这三年间的阅读史也同样支配着诺瓦利斯的诗学形式决断。波墨的神秘主义作品,赫姆斯特惠斯(Franz Hemsterhuis)的新柏拉图主义,德国虔诚派宗教文学的圣歌,它们不仅滋养了诺瓦利斯的宗教情怀和神秘倾向,而且涵养了他对象征形式和隐微修辞的高度敏感。英国诗人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的名篇《静夜思》(NightThoughts),通过博德默尔、克洛普斯托克和施莱格尔的翻译在德国广为传颂,对诺瓦利斯决断诗学主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黑夜、少女、母亲、基督之间的奇异关联,还来自于15世纪以来在德国普遍流行甚至妇孺皆知的墓园吊歌和宗教赞歌。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赫尔德的《神话断章》,让·保尔(Jean Paul)的小说《无形教会》(UnsichtbarLoge),席勒的《希腊众神》,也融入到诺瓦利斯的思辨与构想之中。诺瓦利斯独到的诗学形式决断则表现在,他挪用了神秘主义的象征体系,营造墓园吊歌和宗教赞歌的氛围,吸纳了哀歌的凄艳华美,表现了贯穿生死的悲剧意蕴,而将观念论和浪漫派的“感性宗教”、“理性神话”推至极端。其诗学决断的终极成就,就是《夜颂》——以“颂”为载体,传递“夜”的无限奥秘,将观念论和浪漫的“新神话”实现在一种仅对神圣奉献丽词雅意的文体之中。“颂”体平易而又神圣,古朴而又雄奇,空灵的宗教意识化为缱绻的诗兴流韵。



《夜颂》严格遵循近代颂歌的基本模型而完成其内在结构:六首颂歌,三个阶段以及二元对位。以赞美黑夜为题的六首颂歌,描述心灵之旅上行下达的三个阶段,而相邻的两首诗对位成篇,互文足义。整个诗篇由结构模式基本相同的三组诗构成。而每组诗的第一首都预演整体三个阶段:从光明王国的尘世生活转入黑暗王国,通过主动遭遇黑暗,体验痛苦,享受爱意,而获取灵知,最后上达神圣的永夜,实现终极救赎。每组诗的第二首都抒情地呈现异邦人回归的渴念:从灵魂出窍的永夜幻觉之中醒觉,表达从光明世界返回永夜的渴望。于是,诗人,表白者,在整个诗篇中往返于光明与黑暗之间,藉着“质的强化”而渐渐加深对黑夜的体验,将历史与神话融入灵知,将对未来的期盼寓于对现实的灵知体验之中。
三、 形上暴力中一袭温柔
《夜颂》从对光的狂暴赞美开始,一种形而上的暴力逾越时空蔓延,无休无止,所向披靡。石头、植物、动物、生物以及灵长生命依次登场,再现了无中生有的创世行为。“面对自己周围的辽阔空间的一切神奇现象,哪个有活力、有感觉天赋的人不爱最赏心悦目的光——连同它的色彩、它的辐射和波动?它那柔和的无所不在,即唤醒的白昼。”开篇不是赞颂黑夜,也非对黑夜倾诉情怀。将一切变成表象,诗人在表象之中开始表白,真实无欺,诚实无伪。从这第一个句子以降,颂歌之中的表白者就一直是对光抒怀。光不是表象(Erscheinung),而是展开在“一切神奇现象”面前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光造就了一切可能的奇观。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夜颂》开篇不仅赞美表象,而且更是赞美藉着表象并作为表象而呈现出来的一切。



在第一组颂歌之开篇诗章中,“光”的意象突兀而又霸气。诺瓦利斯以诗学方式再现更深化了对于哲学“表象”问题的迷恋。这种对表象的迷恋早就体现在他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研究之中。作为德意志观念论的重要缔造者,这两位哲人都对表象及其所寄寓的空间展开了超验的沉思。“表象”、“空间”、“灵魂”甚至还有隐而不显的“时间”都秘写在《夜颂》的第一首颂诗之中。第一行就赋予了“光”相对于一切“表象”的优越地位。霸气浩荡的光,一直可以溯源到万物之起源,是它开创了一切表象生成的可能性。“光”为万“象”奠基,流射于宇间万物,如同月映万川。不仅如此,它还允许界域分封,光照之处,万物各正性命,一如《易经》所说“保合太和”,“正位凝命”。“犹如尘寰的一位君王,光令每种力量呈现无穷变化,结成并解散无数的联盟,让自己那天堂般的形象笼罩一切尘世之物。”这是凸显光的形而上学暴力的诗句。显然,“光”绝对不是诺瓦利斯歌咏的主题,而是他所歌咏的“夜”之反题。质言之,“光”的形而上暴力是他绝望地逃避的对象。


第一首颂诗的结句将超验的沉思之诗化表达推至极点,读起来几乎就是用现象学的术语先行呼召德里达的解构事业:“唯独它的亲在展示世间各王国的美景奇观。”“亲在”(Gegenwart)是一个经典的现象学概念,诺瓦利斯不仅先行灵悟,而且在隐喻意义上用它来写照“光”的独一无二威权。光的“亲在”仅仅是隐喻的:它事实上没有形体,也不会现身,只不过是“让自己那天堂般的形象笼罩一切尘世之物”,将自己无所不在的威力高悬在万物之上而已。结句呼应首句,首句之中被赋予“光”的恐怖威仪也不是明说而是隐喻。一个像陈述又像疑问的句子——“哪个有活力、有感觉天赋的人不爱最赏心悦目的光”,预示着第一组颂歌第二首颂诗对“光的否定”。对光的赞美显得像是矫揉造作,言不由衷。《夜颂》马上急转直下,朗如白昼地表明,它非赞美“光”本身,而是以“光”设喻的修辞手法——明喻、比拟或隐喻:是“唤醒的白昼”,如“生命最内在的灵魂”,像“尘寰的一位君王”。不错,太阳像君王被顶礼膜拜,但众多的君王却非太阳,而是喻涉某些隐于其后或位于其上的某些属灵的东西。第一首颂诗的庄严赞词预示着一场突转,接下来表白者立即就剥夺了“光”的赫赫威仪,摧毁了“表象”的充足根据。
第一组颂歌的第二首颂诗实现了这场突转。置身在“光”之中而感受到无休无止的形而上暴力,表白者充满焦虑地“朝下转向神圣、隐秘、难以名状的夜”。下转就是内转,内转就是“下及万有”。“我”——表白者——通过遭遇神圣隐秘难以名状的黑夜而奋力获取灵知。下转、内转,就是离弃“表象”,进入荒凉而寂寞的地盘,奋力建构一种与“光”的暴力对立的话语。表面是下转,隐秘是内转,无论如何转都是一场及物而必须有后果的灵魂运动。一方面,灵魂下转之时仍然维护了“光”的传统至上性。另一方面,灵魂内转暗示着一种更深沉、更低沉、更深邃的渊源,从而削弱了“光”的形而上威权。曾几何时,光不再是表象的充足根据,而在形而上被“去势”了。这就立即颠倒二极等级关系:“这世界很偏僻——沉在一个深渊里。”“偏僻”(fernab)之中“ab”重复了首句“朝下”(abwärts)之中的“ab”,这个表示方向的小品词指示距离和深度,从而完成了光与夜之间的翻转。这种翻转属于空间,但表白者忧心如焚,渴望这种颠转。诗篇开始合乎传统,将“夜”置于“光”之下,随即却以“夜”为视角将“光的世界”描写为“沉沦的世界”,从而彻底翻转了空间关系。

表白者彻底离弃了表象,而真正感受到了黑暗的一袭温柔。同时,颂诗彻底完成了空间翻转,而把“光”包孕于“夜”中。穿越黑夜之中的“光”,亲近“光”中黑夜的唯一法门,就是直接变成黑夜。“你竟然喜欢我们,幽暗的夜?”称谓变了,第二人称将幽暗之夜变成了一个可亲的对象。将第一人称单数换成第一人称复数,则更是凸显幽暗之夜的无边温柔。它所笼罩之处,不止孤独的诗人,还有诗人的族类。表象在幽暗笼罩之所凄然退潮,随之而来的是汹涌的情潮。“情”先于“理”,“理”难节“情”,此乃诺瓦利斯研读费希特哲学得到的启示。“情潮”对表白者构成的威压,丝毫不逊于“光流”对表白者的窒息。幽暗之夜涌动的温柔“情潮”托举着心灵的沉重翅膀。当他窥见到一张端庄的脸孔,于无限缠绵的卷发之中看到母亲青春的妩媚,表白者幼稚的恐惧与焦虑平息了。他继续在黑夜里巡视,感到了白昼的贫乏与幼稚,领纳着幽暗的万能与恩惠。沉入幽暗而下及万有,看到了黑夜在广袤的空间播下的闪亮星球。黑夜在我们内部开启无限的眼睛,比闪耀的星辰更美妙。黑夜开启的眼睛,当然是灵知的器官,是灵视的装置,所以表白者无需光照即可望穿一颗挚爱心灵的深渊。这灵知的目光,以不可言说的情欲充满了一个更高的空间。于是,下及万物同时也上溯空性,表白者满怀情欲,开始赞美宇宙的君王。
第一组颂歌的第三首颂诗,尽情地歌咏了幽暗之夜那一袭拯救的温柔。表白者从完全“丧我”的忧惧之中复性归真。表象在幽暗的围剿之中化为苍茫无有。幽暗之夜开始仿佛是以死亡胁迫幼稚的“自我”,但立即发生翻转,展露出解放潜能,倒反衬得白昼“贫乏与幼稚”。追忆血脉相连的母亲及其妩媚青春,表白者再度获得了自我感——他独一无二的“自我”意识。珍贵的香膏从暗夜之中滴落,给他带来一束迷人的罂粟花,表白者就开始超越孤独,而体验到拓展的自我。他称幽暗之夜为“宇宙的君王”,“神圣世界的崇高的报告者”,“极乐的爱的守护者”,“温柔的爱人”,“黑夜迷人的太阳”。表白者醒来,灵悟到“自我”与黑夜互相归属,彼此合一。与黑夜的圆融,诗人真正成为人。他希望延续这亲密的圆融,让永结同心之夜延续到永远。
如果说光是形而上的暴力,那么夜就是超验的温柔。《夜颂》第一组颂诗就在暴力和温柔的消长节奏之中展开了浪漫化运动。上溯空性,庄严的陌生人置身于无休无止的形而上暴力之中,奋力地在空间之中挣扎,意欲“向后”、“向上”、“向前”,渴望反身而诚,触摸生命最内在的灵魂。下及万有,庄严的陌生人下转到神圣隐秘难以名状的夜,忧郁地在时间之中浮沉,纠结在回忆、心愿、梦幻、欢乐、希望的悲情复合体中,最后与一袭幽暗的温柔圆融合一。在一个同样不可言说的他者空间,上溯空性与下及万有合二为一,光与夜圆融于“黑夜的迷人的太阳”。如果说,形而上的暴力之光象征着圣父时代的霸气浩荡的正义,那么,超验的温柔之夜则象征着圣子时代万分荣耀的恩典,且预示着圣灵时代脆弱柔美的爱心。第一组颂诗的结句中,表白者呼吁亡灵之火燃尽他的肉身,在亲密的圆融之中将新婚之夜延续到永恒。光与夜终于合一,温柔收服了暴力,幽暗就获得了囊括万有和化育万物的神圣伟力。这是《夜颂》以诗学形式呈现的一个典型的灵知主义命题,用哲人黑格尔的话说:


❶ 威尔伯:《意识光谱》,杜伟华,苏健译,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版。“上溯空性”,是指心灵铺展、展开、开显出真实的灵知维度(化用佛教术语则曰“空性”),而“下及万有”,是指心灵牵涉、纠缠、深陷,失落于表象世界,隐微而不得开显。威尔伯写道:“‘回溯’,下及万有,意味着‘牵涉’、‘纠缠’、‘深陷’。而这样说来,‘回溯’即灵性‘陷入’表象世界,并‘失落’或者‘卷入’其间。在回溯的过程中,灵性从自性中脱离出来,与自身疏离,产生了充满他者(otherness)与万物的表象世界,变成幻觉世界之中的纠缠与牵绊。接着,灵性开始以灵性的方式回归于灵性;它成长、演化并发展起来,从物质到肉体到心智到灵魂再到自性。这样的运动就应该称为‘上溯’了:灵性,就是从你我之分的幻觉中觉醒。”(XIII-XIV)。
❷ 转引自魏尔:《诺瓦利斯及其隐微诗文》,刘小枫编《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❸ 汉拉第:《灵知派与神秘主义》,张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❹ 汉拉第:《灵知派与神秘主义》,张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❺ 参见威尔伯:《性,生态,灵性》,李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354页。
❻ Hans Blumenberg,DieLegitimitätderNeuzeit, Frankfo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138.
❼ Eric Vögelin,TheNewScienceofPolitic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133.
❽ Jacob Taubes,AbendländischeEschatologie, Mattes & Seitz Berlin, 1995, 26.
❾ 刘小枫编《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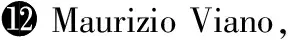




















编辑/张定浩
- 上海文化(新批评)的其它文章
- 文以载车
——民国火车考( 下) - 诗人与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