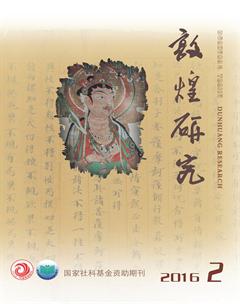归义军政权对徭役影庇的限制
赵大旺

内容摘要:官斋劳动是归义军时期敦煌百姓承担的杂役,官员、衙前子弟、色役人等出现于官斋劳动中表明其本身虽免杂役,但不能影庇户内其他丁男。这种对徭役影庇的限制与中原地区的政策是一致的,归义军时期官员等政府服务人员出现于官斋及其他杂役中,显示其限制政策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落实。
关键词:归义军;官斋劳动;徭役;蠲免;影庇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2-0079-07
Abstrac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Gui-yi-jun regime, a program of “assorted labor”was impressed upon the people of Dunhuang. The officers, official service workers, and other official labor service employees took part in cooking work, including cooking for local Buddhist monks, showing that they had little privilege to protect their families from“assorted labor”tasks. This policy showed an obvious similarity to the policies enact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officials took part in cooking and other common tasks under the force of the Gui-yi-jun regime,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restrictiv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Gui-yi-jun regime were well implemented.
Keywords: Gui-yi-jun regime; official labors which provide food to Buddhist monks; labor; exclusion of labors; privilege to protect a whole family from labor.
关于归义军时期的徭役制度,学界已有一些论述,其中雷绍锋、刘进宝等先生在著作中研究了归义军的赋役蠲免政策。笔者通过对P.3231(11)《平康乡官斋籍》的考察,发现一些本该享受免役特权的人参与了官斋劳动,从而表明其免役权有限,不能影庇户下徭役。《平康乡官斋籍》成于曹氏归义军时期,记载了癸酉年至丙子年(973—976)平康乡百姓参与官斋劳动的情况。雷绍锋曾撰写《〈癸酉年至丙子年敦煌县平康乡官斋籍〉之研究》一文,对其反映的劳动性质做了研究[1]。笔者以为,这件文书与赋役制度的关系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故撰此文,求教方家。
一 文书反映的劳役性质
雷绍锋先生曾针对《平康乡官斋籍》认为斋僧具有力役性质,并引《北梦琐言》“程贺以乡役充厅仆”作为类比,认为官斋劳动是真正意义的“乡役”。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尙可商榷。首先,对于唐代的“乡役”,学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张泽咸认为“乡役”即“邑役”,是地方性的乡里之役,也是色役,又称“乡村色役”[2]。从这个角度讲,官斋劳动很难说是“色役”。其次,厅子役在归义军时期也广泛存在,Дx2149《欠柴人名目》记载欠柴的石富通,即标注为“厅子”,表明担任厅子在赋役上有一定的优待,而参加官斋劳动的平康乡百姓并不享有这个待遇,显然二者的劳役性质并不具有可比性。
需要指出的是,百姓被官府征发从事造食劳动不止斋僧一项,规模较大的官方宴设、供顿,都是由百姓承担造食之役的。如北魏崔光在灵太后打算幸嵩高时上谏称“供顿候迎,公私扰费”[3];隋炀帝幸辽东到燕郡时,检校燕郡事的柳謇之因为“供顿不给”配戍岭南[4]。玄宗时期,将作大匠韦凑说:“一万行人,诣六千余里,咸给递驼,并供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5]。永泰年间,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特诏宰臣、百僚、六军将军送上,“京兆府造食”[5]4764。永泰二年(766)行释奠礼,“宰相、常参官、军将尽会于讲堂,京兆府置食”[5]923。元稹的《连昌宫词》有:“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6]之句,唐懿宗制书也称:“顿递供承,动多差配”[5]656,都反映了政府征发百姓从事造食之役。归义军时期也有征发百姓为官府造食的记载。S.1366《年代不明(980—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载:“赏设司女人、汉七人各中次一份,十乡老面二斗、油一升,计用面五十三石三斗九升七合,油一石七斗三升四合四勺。”[7]从制作食品的量来看,归义军的寒食宴会规模很大,仅靠“设司女人、汉七人”远远不够,因此,也要征发百姓参与造食劳动,支出“十乡老面二斗、油一升”,就是用来款待组织劳动的乡官的。
这种供顿之役应该是属于杂徭,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东封泰山,诏:“其行过州县,供顿劬劳,并帖顿百姓,有杂差科并车马夫役者,并免一年租赋。”[8]自洛阳回京诏称:“其供顿州应缘夫役差科,并免今年地税。”[9]这里面的杂差科、夫役差科都是指的杂徭。在唐前期,官斋这样的造食劳动也应该属于杂徭性质。唐前期的徭役包括正役、杂徭和色役。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10],其后《贞元改元大赦制》再次强调:“自诸道州府,除两税外,应有权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11]。似乎已经不再有无偿的力役差使了。但其实并非如此,陈明光指出两税法改革并未将地方性的杂徭“转化为征收代役金的形式,因而是合法的采取现役形态的徭役”[12]。张泽咸也列举出两税法时期存在杂徭征发的例证[2]326-328。因此,作为杂徭的官斋劳动出现在归义军统治下的敦煌地区是正常的。唐五代时期,正役普遍采取雇役的形式[13],杂徭与色役成为百姓的主要负担,但正因为如此,区别于“正役”的“杂徭”之名也渐渐消失。张泽咸曾指出,“唐后期的力役征发,往往与差役、差科、杂徭等互相混淆,有时很难加以区分”[2]292,“杂徭与力役逐渐趋向合流……宋、元、明之世,‘杂徭之名已很罕见”[2]329。到了南宋,法律上就有“夫役谓科差丁夫役使”[14]的表述,即用“夫役”指代徭役劳动。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也常常以“役夫”、“诸杂差遣”、“知杂役次”等指称百姓的劳役负担。P.3155
背《唐光化三年(900)前后神沙乡令狐贤威状(稿)》中令狐贤威因土地被大河漂没,而呈牒:“昨蒙仆射阿郎给免地税,伏乞与后给免所着地子、布、草、役夫等”[15],其中便将徭役负担总括为“役夫”。另外,P.3324背《唐天复四年(904)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是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因对徭役差发不满而上的状文:
(前略)前使后使见有文凭,复令衙前军将子弟随身等,判下文字,若有户内别居兄弟者,则不喜(许)霑裨。如若一身,余(除)却官布、地子、烽子、官柴草等大礼(例),余者知杂役次,并总矜免,不喜(许)差遣。文状见在。见今又乡司差遣车牛刈芦茭者,伏乞司空阿郎仁恩照察,伏请公凭,裁下处分。[15]450
文状涉及的徭役负担包括“烽子”和“知杂役次”,而乡司差遣“刈芦茭”属于“知杂役次”的范畴。P.3257《甲午年(934)二月十九日索义成分付与兄怀义佃种凭》记载索义成“身着瓜州”期间,“所着官司诸杂、烽子、官柴草等大小税役,并总兄怀义应判,一任施功佃种。”[15]29也将徭役负担概括为“烽子”和“官司诸杂”。笔者认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百姓承担的徭役负担中,像“刈芦茭”这样的“诸杂役次”,可以将其称为“杂役”,渠河口作、枝夫等应当都属于杂役,其特点是劳役较轻,不耽误农业生产。与之相对的应该就是如烽子这样的“重役”,如S.4654号背《(946)前后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百姓王盈子兄弟四人状(稿)》就有:“更兼盈进今岁次着重役”[15]300。杂役与重役都是一般的劳役,只是从其劳动强度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的角度来进行区分,而非像唐前期杂徭与正役那样有不同的征发制度。
根据上面的叙述,笔者认为官斋劳动与乡司差遣的“刈芦茭”一样,属于敦煌百姓承担的杂役,亦即所谓的“知杂役次”,是归义军政权对敦煌百姓的力役征发,且属于较轻的力役。
二 归义军时期的徭役蠲免
通过对《平康乡官斋籍》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些官斋劳动者的身份值得注意,现将其列表,见表1。
通过对此表的分析,我们发现,参加官斋劳动的人中,目前可知有18人身份较为特殊,其中1人为都头,1人为都衙,6人为押衙,2人为服务于官府的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1人为官健,6人为服务于政府的色役人,1人为都头之子。将其分为四大类:都头、都衙等官员,押衙、衙前子弟、官健等服务于政府人员,色役人,官员家属。都衙,即都押衙,据冯培红研究,归义军时期的都头已经阶官化,常以兼职、加官的形式出现,甚至有的都头显然地位不高[16]。P.3412《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都头安再胜、都衙赵再成等牒》中都衙赵再成与都头安再胜等联名上报敌情,表明他的“都衙”绝非虚衔。宋保定出现在《己卯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目断官员》表明身份是官员。杜幸德主持州司仓库,可见其也是服务于官府,并非普通百姓带押衙衔。令狐瘦儿、张富昌出现在P.3146《辛巳年(981)八月三日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等留残袛衙人数》中,也表明其服务于官府的身份。刘进宝先生指出由于P.4525《官布籍》中的“都头”、“牧子”、“吹角”等人正服务于官府,因此可以免纳赋税[17]。但这些人又出现于《平康乡官斋籍》,表明其参与了官斋劳动这样的杂役。
首先看官员,《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载:“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其下注云:“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已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18],点明官员中五品以上者,免除该户课役。《天圣令》卷22《赋役令》附唐令第16条载“诸文武职事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父子,若除名未叙人及庶人年五十以上,若宗姓,并免役输庸。其应输庸者,亦不在杂徭及点防之限。”[19]可见法律规定唐前期的官员及其父子均有免除杂徭的特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在敦煌地区,低级官员享受到的免役权应该较为有限,堀敏一据P.2592《天宝六载籍》中武骑尉(从七品)程思楚户、队副(从九品)曹思礼户,以及P.3669《大足元年籍》中果毅(从六品)张楚琛户均标注为“课户”,认为官员本身虽然不课,但户内还有其他课口[20]。可见这些官员没有影庇户下课役的特权。两税法时期更是如此,大中六年(852)三月,宣宗敕令“先赐郑光鄠县及云阳县庄各一所,府县所有两税及差科色役,并特宜放。”而中书门下奏:“伏以郑光是陛下元舅,宠待固合异等,然而据地出税,天下皆同;随户杂徭,久已成例。将务致治,实为本根。”[10]1544-1545宣宗即位,郑光“拜诸卫将军,迁累平卢军节度使,徙河中、凤翔”,直到大中七年来朝,留为右羽林统军兼太子太保[21]。可见两税法时期的“随户杂徭”,郑光作为皇室外戚,又位居节度使之职,其家也不能免除。此外,
P.3418背《唐年次未详沙州乡欠枝夫人户名目》中,包括县丞、长使、丞等官吏都被记录为“欠枝夫人户”,雷绍锋指出这些官员是享有减免待遇的,并且其减免特权扩大到某些人的“子弟”中,如“郎君”等[22]。笔者注意到,该文书中身份为官员的还有第20行的“令狐参军”,第92行“押衙曹保忠”,第102行的“平水杨他粪”[15]427-436。此外,第172行“阴仁贵”欠枝三十一束,在整个文书中仅次于郎君李弘定三十三束,根据归义军赋税征收以土地为据的原则[16]180。可能是由于其占有土地较多,他应该就是《龙泉神剑歌》中的“当锋直入阴仁贵”[23]。还有,第169行张怀政在896年以前位居“归义军马步都虞候”,第174行曹子盈在899—901年是“悬泉镇使”。[22]108这些人中,令狐参军被列在“纳半欠半人名目”中,表明其缴纳了一部分枝,如果这些人是合法享受免枝夫的特权,为何令狐参军要缴纳一部分枝呢?此外,平水杨他粪“都欠十六束”,也是整篇文书中仅见的表达,说明他是多次累计欠枝达十六束,这些都说明对这些官员的欠枝登记绝非仅做在账面上,而是要实际予以征收的。笔者以为,如果某户合法享受蠲免特权,各乡就不必计算其需纳枝数量,更不会有欠枝若干束的说法,而是会像文书第36行“葛学敢有忧”或第191行“李再盈全免枝夫”那样,说明免纳即可。因此,这里登记的欠枝应该都是要征收的,也就是说这些官员没有免除户下枝夫杂役的特权。
从以上可知,对于官员来说,可能本身是免徭役的,但该户仍然有其他丁男要承担“枝夫”这样的杂役,且仍然以该户户主为单位进行征收。可见官员不能免除户下徭役。赵再成等人可能就是由于其户下还有其他丁男,因此官斋劳役仍然会征派到该户,这时候赵再成就可能代表该户服役,当然也可能是户内别的家属代表该户参加劳动,如“都头之子”梁阿婆子。
再看其他押衙、子弟等,据上引P.3324背《唐天复四年(904)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他们免除“知杂役次”的前提是“一身”,亦即没有“户内别居兄弟”,如果不符合该条件,则“不喜霑裨”,该户仍然要承担杂役。这与唐政府相关规定是一致的,长庆元年(821)册尊号敕:“一户之内,除已属军、使,余父兄子弟,据令式年几合入色役者,并令京兆府明立簿籍,普同百姓一例差遣”[24]。另外,会昌五年(845)正月三日南郊赦文有“计户内丁数多少,充诸司尽称子弟,致令乡县所由无人差役”[8]2173,也可以看出,只有户内丁数全部成为诸司“子弟”,才能免除该户差役,唐政府还专门有限制户内入军丁数的政策,贞元十年(794),“京兆尹杨于陵奏,诸军影占编户,无以别白,请置挟名敕,每五丁者,得两人入军,四丁三丁者,差以条限。从之”[10]1295。因此,《官斋籍》中出现的这些服务于官府的押衙、衙前子弟等人,由于户内还有别的男丁,所以户内徭役没有免除,当征派该户从事官斋劳动时,他们便代表该户参加劳役。
归义军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官府服务人员参与的记载,如张定千,S.4643《甲午年五月十五日阴家婢子小娘子荣亲客目(三)》中标记为“都头”[25],但也仍然多次出现在渠人转帖中,表明其代表该户承担了修渠之役[26]。
表格中“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也需要作些说明。“翻头”是归义军使府中级别较低的军将,排位在将头、队头之下[27]。P.3146将袛衙人分为三翻,“每翻各三日三夜”,那么此处“翻头”可能仅指每一翻的负责人,而非军将职衔。再看子弟,唐代史料中“子弟”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是《贞元改元大赦制》称:“诸道非临寇贼州县,自冬已来新点召官健子弟,并宜放散”[8]2134,此处“子弟”与“官健”连称,两者性质相近。另有一种是杜甫在《东西两川说》所描述的:“今富儿非不缘子弟职掌,尽在节度衙府州县官长手下哉”[28],这是指服务于政府部门的“子弟”,上引会昌五年敕文说的“充诸司尽称子弟”即属此类。那么令狐瘦儿、张富昌具体身份为何?P.3146中的张住子又出现于P.4063《丙寅年四月十六日官健社春座局席转帖》[26]182,表明其身份是“官健”,那么,令狐瘦儿、张富昌的身份也应该是官健。此外,张住子又出现在罗振玉旧藏《年代未详沙州白刺头枝头名簿》中,并担任白刺头[15]437,表明其虽为官健,也参与刈白刺这样的杂役。再如张闰子、唐瘦儿二人,也在P.3146《辛巳年(981)八月三日衙前子弟州司及翻头等留残袛衙人数》中出现,但他们还同时出现在P.3721《庚辰年(980)三月廿二日平康乡堤上见点得人》[25]162,表明他们也要承担修堤劳役。唐代的兵役“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29],李汇当泾原节度使时,“罢军中杂徭”[21]4590,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平徐州制》有:“如行营人,并免差科色役”[5]671,表明行营将士原未免杂役,所以才有恩制予以蠲免。《官斋籍》出现官健承担造食杂役,可见归义军时期是继承这一制度的。此外,S.6272《行人转贴》还记载:“已上行人,僧统刈麦一日”[30],也反映出士兵参与杂役的情况。
再看牧子、吹角等色役人。P.4525(8)《官布籍》显示张憨儿、赵阿朵、李富德三人在972年为牧子,而P.2484《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7]590中张憨儿也作为“知驼官”出现,可见其长期为归义军政权放牧,因此,当张憨儿等人在973年参加官斋劳动时,其身份应该仍是归义军的“牧子”。可见“牧子”可以免除纳布,但该户却没能免除杂役。唐前期的诸牧,据《天圣令》卷24《厩牧令》所附唐令第1、2条规定:每群置一名牧长,四名牧子[19]294。该令文中的“牧子”恐怕与归义军时期的牧子张憨儿、邓富通、李富德等人不同。P.2484《戊辰年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现行籍》[7]590-595是归义军政权对牧群进行算会的记载,其中张憨儿等知驼官每人负责一群,其地位和职掌应该是相当于唐前期的牧长,这可能也是他们被称为“知驼官”、“知马官”的原因。据《天圣令》卷22《赋役令》所附唐令第15条记载享受“并免课役”待遇的就包括“牧长”[19]392。但张憨儿等牧子出现在官斋劳动中,表明其虽免自身课役,但户内杂役仍然没有免除。另外,P.2155号背《归义军曹元忠时期驼马牛羊皮等领得历》[7]596中还有一人张再庆,其身份也是“牧子”,他也出现于上引罗振玉旧藏《年代未详沙州白刺头枝头名簿》,表明他所在户也没有因其“牧子”身份得到免除杂役。
吹角,刘进宝先生撰文指出史籍中的“吹角”都是“吹大角”者,“并且是军队中专有者,在军队训练及战斗中使用,而P.4525(8)中的‘吹角,应该不是军队中‘吹大角者,而是娱乐场所的‘吹角者,与音声相似,属专门的艺人。”[31]这种说法亦有道理,但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吹角”属于军中吹角者的可能性。吐鲁番文书中即出现了普通百姓担任军中“吹角”的情况,阿斯塔纳501号墓出土的《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记载:“一人大角手:沮渠足住;二人虞侯:魏辰欢、尉毛爽”[32],此处“虞侯”一职属于军中职务,那么与其并列的“大角手”也应当是服役于军中的吹角者。这种“吹角”未必只在战斗、训练中使用,归义军政权仪卫队伍中也有吹角者,据《唐六典》卷14“鼓吹署” 条载,“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其下注云:“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袴。其鼓吹主帅服与大角同”[18]407,说明天子出行的仪仗中就有吹角者,归义军节度使出行,也有这样的前后鼓吹的仪仗队随行,敦煌莫高窟第156窟有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其仪仗中包括一支乐队,其中就画有吹角者[33]。据会昌二年(842)四月二十三日《上尊号敕文》载:“京畿诸县太常乐人及金吾角子,皆是富饶之户,其数至多,今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今日已后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8]2144这里面的金吾角子便是天子仪卫中使用的吹角者。可见,吹角役也与P.3324背《唐天复四年(904)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叙述的情况一样,若户内还有其他丁男,则不能免除该户杂役,这正是吹角氾富德出现在官斋劳动中的原因。
笔者以为P.4525(8)《官布籍》中的吹角还可能与农事有关。据唐末的韩鄂所编《四时纂要》记载当时种木棉的方法说:“七月十五日,于木棉田四隅掴金铮,终日吹角,则青桃不殒。”[34]韩鄂自序编此书是“删两氏之繁芜,撮诸家之术数”,即较多抄录前人农书,至于他所生活的唐末五代时期是否仍使用这个方法则不得而知,史籍也难印证,姑备于此,以待后考。此外,姜伯勤先生以为此处“吹角”是在沙州傩礼中的音声供奉[35]。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普通百姓所执“吹角”之役具体为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官斋劳动是归义军政权对百姓征发的杂役,而服务于官府的官员、押衙、子弟、官健以及牧子、吹角等人参与官斋以及其他杂役的情况,表明这些人依据其身份取得的免役特权是有限的,其所在户仍然要承担杂役。唐代中后期以来,赋役蠲免日益伪滥,投名影占现象十分严重,除官员影庇一户外,富人也通过各种方法免役,如前面所说的“充诸司尽称子弟”,或是“户内一人在军,其父兄子弟不受府县差役”[8]2142,最终的结果如前引会昌五年敕文所说,“致令乡县所由,无人差役”,又如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南郊敕》指斥的“致苦贫下”[24]402。为此唐政府多次出台政策,限制影庇。上引《乾符二年南郊敕》就有:“准会昌中敕,家有进士及第,方免差役,其余只庇一身。就中江南富人,多一武官便庇一户,致使贫者转更流亡,从今后并依百姓一例差遣,仍委方镇各下诸州,准此检点。”[24]402杨燮《复宫阙后上执政书》称:“且敕有进士及第,许免一门差徭,其余杂科,止于免一身而已。”[8]3442但是晚唐以来的限制政策在中原地区收效甚微,因此朝廷才会一再发布诏敕,三令五申,直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诏京百司人吏,并不得放免户下差徭、科配。户部旧有蠲符案,主百司人吏蠲免差配,给蠲符,自此废之。”[36]与此相对照,归义军时期的杂役征发也有免役只及一身、禁止影庇一户的限制政策,这与唐末以来的限制影庇是一致的。同时,与中原地区相比,敦煌文书所反映出归义军治下的相关限制政策落实得较好。
参考文献:
[1]雷绍锋.《癸酉年至丙子年敦煌县平康乡官斋籍》之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2):10-18.
[2]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M].北京:中华书局,1986:340.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97.
[4]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76.
[5]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88.
[6]元稹.元稹集[M].冀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271.
[7]唐耕藕,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285.
[8]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2149.
[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943.
[10]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1535.
[11]陆贽.陆贽集[M].王素,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46.
[12]陈明光.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3):13.
[13]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31.
[14]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M].戴建国,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667.
[15]唐耕藕,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二[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293.
[16]郑炳林,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中都头一职考辨[G]//郑炳林,冯培红.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83.
[17]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90-200.
[18]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77.
[19]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课题整理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392.
[20]堀敏一.均田制研究[M].韩国磐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232.
[2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853.
[22]雷绍锋.P.3418背《唐沙州诸乡欠枝夫人户名目》研究[J].敦煌研究,1998(2):111-112.
[23]颜廷亮.《龙泉神剑歌》新校并序[J].甘肃社会科学,1994(4):109.
[2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5.
[25]唐耕藕,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四[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13.
[26]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384,386,388,390,392.
[27]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外职军将研究[J].敦煌学辑刊,1997(1):52.
[28]杜甫.杜甫全集校注[M].萧涤非,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6480.
[2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753.
[30]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414.
[31]刘进宝.P.4525(8)《官布籍》所见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免征[G]//项楚,郑阿财.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302-303.
[32]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75.
[33]关友惠.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晚唐卷[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6.
[34]韩鄂.四时纂要校释[M].缪启愉,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107.
[35]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64.
[3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