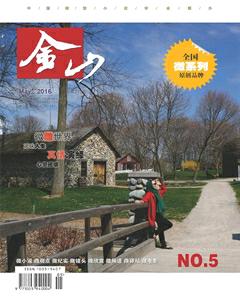匣子枪
卢帅任
零星的枪声也沉寂了,被硝烟涂抹的天空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几十个战士正忙着打扫战场。
炊事班长福叔早支好了锅,炊事员满兜正忙着添柴,锅里煮着掺了玉米面子的野菜。和敌人接连数日的缠斗让战士们急需营养,但炊事班能拿的出的就只有这个。
饭好了,衣衫褴褛的战士们依次打了野菜汤,指导员扶着受伤的连长从铁锅里取了一样的饭。满兜端着自己的破瓷碗,吸溜着汤,虽然刚做过饭,但手上一点油腥不见,这让他不觉想起之前的生活来。
半个月前,满兜所在的山寨被这个连队连锅端,大当家携着沉重的钱财被击毙,十几岁的满兜被那个称为指导员的年轻人带给一个老人,“福叔,这个娃就交给你了。”
自此,满兜便成为连队炊事班的一员。习惯了山寨里每天煮不尽的牛羊熟肉,连队里的清汤寡水还真让他不习惯。满兜也动过逃跑的念头,但福叔待他实在,最重的铁锅和柴火福叔从来都是自己背,只让他带点轻便的玉米面。自幼孤儿的满兜从未被人如此保护过,逃跑的事也就一拖再拖,只是这个想法从未消散。
“小子,想啥呢!”福叔取了锅里剩下的野菜汤,凑近满兜,“抓紧吃,今天还要赶路呢!”
满兜沉吟了一会,“福叔,天天急赶着走,啥时候是个头?”
“嘿!”福叔作势要打,“跟着我们走不会有错,不走你想干啥?”
“我想做山大王!” 一听这话满兜来劲了,他的眼里闪着亮光,“自立为王!像胡子王那样!” 胡子王是远近闻名的山寨主,和别的土匪不一样,胡子王除了打劫平民百姓,有时候也打劫路过的军队。
福叔却不说话了,他低头看了看瓷碗,“做啥不好,非当这种害人精。”
满兜看到福叔神色不好,知趣的把脑袋埋到碗里。
清淡的野菜汤很快就进了满兜的肚子里,福叔正想把自己的菜汤匀他一些,一声猛烈地炮响打破了难得的安宁。
闻声,远近的战士们立刻丢下碗,抄起身旁的短枪长矛,连长不顾伤,抓起枪就往炮声的方向跑去。指导员一把按下连长,扭头喊道:“党员跟我上!”
说话间,几十个武器简陋的战士便集结在指导员身后,满兜怔怔的看着炮火来处出现了成片的敌人。
“愣着干啥!帮忙收拾!”福叔催促道,手上收拾着炊具,眼睛却片刻不离已经交战起来的两拨人。
炊事班唯二的一老一小把铁锅用草绳扎好,又忙着把没用完的柴火捆起来,正忙着,福叔手上却停了。
满兜顺着福叔呆呆的目光看去,战斗中,指导员被几发子弹击倒在地。福叔脸皮猛地一抽,跌跌撞撞的窜了过去。
满兜跟着福叔跑过去时,指导员已经有进气没出气了,他颤抖着从腰间拿出一个包裹,递给福叔,“福叔,其实早该还你了,保护好大家……”
指导员的眼睛闭上了,福叔抹了把眼泪,打开包裹,一支磨得发亮的匣子枪赫然在目。
“我以炊事班班长的身份命令你,保护好连长和炊具,寸步不离!”福叔熟练的压弹上膛,严肃的对满兜说。
满兜慌不迭的点头,福叔已经奔向了战场。
满兜没看住连长,后者早加入了战斗。他只能守着炊具,看着远处的战斗。他从未见过如此骁勇的福叔,一支匣子枪出神入化,枪声必中,好似天兵下凡,以一己之力扭转胶着的战局。
满兜再看到福叔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连队再一次击退了敌人。福叔呼吸沉重的躺在地上,他的肺被打穿了,血泡沫从伤口里涌出。
满兜握住福叔逐渐冰凉的手,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福叔,我没看住连长,不过他没再受……”
福叔轻声制止:“你做的很好……别想太多,跟他们走下去,不会有错……”
沾血的匣子枪从福叔手里递到满兜手里,满兜也从连长口中了解到了真相:因为连长的口音分不清“胡”“福”,新加入红军的胡子王便成为了大家的福叔,福叔也乐呵呵接受了。厌倦了国民党鸦片团的欺凌,他上山称王;而这支装备落后却纪律严明的部队吸引了他,他解散山寨,加入了红军。福叔自知罪孽深重,把心爱的匣子枪交给指导员保管。
连同匣子枪一起,那口铁锅也背到了满兜身上,满兜拒绝了连长派人到炊事班的好意,他再也不会想逃跑了。满兜从未如此坚定,他一心一意的跟着连队走着,连同怀里那沉甸甸的匣子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