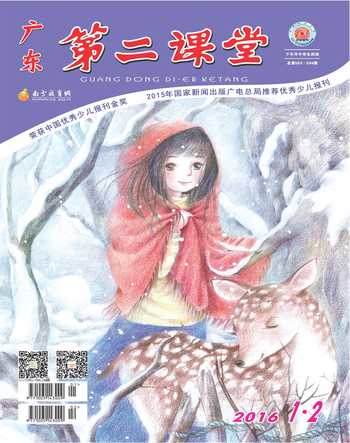好的散文源自生活
荐书:《给孩子的散文》
作者:老舍、沈从文等;编者:北岛、李坨
读书笔记:夏丽柠
作家汪曾祺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散文如同布帛麦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北岛和李陀将这句话引用在了他们选编的《给孩子的散文》的序言里,用以强调散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古往今来,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青少年的语文课上,记忆犹新的教诲便是“散文旨在形散而神不散”。所谓形散,与其说是语句及行文结构存在的状态,不如说是散落在生活里的人生片断。而神不散,意味着将这些细碎收集起来,汇集成一种情感以文字的形式发散出来。
本书共计46篇,按年代分,从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到80后作家李娟; 按地域分,从地道的北京人老舍到定居香港的西西; 按创作领域分,从诗人顾城到专栏作家毛尖……可见,选稿者的艰难抉择非比寻常,好稿很多,选是选不完的。
鲁迅的《好的故事》是首篇,的确有其惊艳之处。他说,“我在蒙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然而,他写下的竟然是一个“梦”。他所记载的梦,极其荡漾,宛若水波。场景从河心记录推移至河底,再从河底翻上岸来,充分体现了思绪里的“散”。可这一切被鲁迅比喻为“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待到小憩惊醒,他仍然记得“这一篇好的故事”。看似不着边际的描述与比拟,可读者却仿佛坠入生活的海洋,与鲁迅一起摸索生活的痕迹。
丰子恺的《野外理发处》和老舍的《四位先生》,是我最喜欢的两篇。选前者是因为丰子恺是将漫画和文章都描摹得栩栩如生的人,读他的散文就像看见了他的画面,而欣赏他的立轴就像融入了生活本身。剃头,这么一件小事儿,在他的笔下却生出那么多趣味,他以一个“被剃者”的口吻描述着“小人物”任人宰割的心态。本来为人服务的“剃头匠”反而成了高高在上的主宰。在生活里,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也许就是一个海阔天空的结局。其实,好的散文在生活里汇集、发酵,然后散发出春的气息!
所以我说,阅读散文的舒服之处就在于,散文家们呈现的都是读者特别熟悉的生活场景,而且以一种“自由”的状态呈现。相对于严肃文学,我觉得散文总体上来说是最有能力去呈现生活本身的状态的,它可以是优美的、短促的、深邃的和发人深思的。纵然生活万般苦,却也需要“正能量”。即便是萧红的《饿》,结尾也以“闭了灯,又满足又安适地睡了一夜”收住。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如毛尖的“痞”和李娟的“大咧咧”的文风也颇受读者欢迎。其实,仔细想想,她们与丰子恺和老舍神似一脉相承。这就是散文的魅力,它可以完美地呈现生活的无处不在。
书摘
1. 亲爱的年轻朋友:
谁小的时候没认过字?
谁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没上过作文课?
从小识字,写下自己的名字,写下父母的名字,写下草木江河和田野——然后上学读书,学习作文。这谁都经历过,可作文是什么意思?
其实,说得宽泛一点,那已经是在学着写散文。
一个人从小就要学习写散文,可见散文是多么重要。
作家汪曾祺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散文如同布帛麦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要是把汪曾祺的这句话延伸一下:散文不只是对文学,而是对于任何一个想让自己生命兴旺的人,它都是“如同布帛麦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这么说是不是过分?我们觉得一点儿也不过分,散文就是这么重要。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有着很长的传统,远在先秦时代就很成熟了。拿人们熟悉的《论语》来说,在《公冶长》一篇里,就有这么一段文字:“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这是一段多么生动活泼的散文!而且,子路回答老师的话,在今天看来,不是也“酷”得很吗?
读《庄子》,读《战国策》,读《史记》——古代的好散文太多了,犹如满天星斗,可是我们现在推荐给大家的这本《给孩子的散文》,内容不是古代散文,而是现代散文,也就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散文。
比起古汉语,现代汉语形成得很晚。在晚清,兴起了一股办“白话报”的热潮,目的是在文言文之外,实验用一种接近口语的“白话”写文章,那应该是现代汉语形成的最早阶段。从那个时候算起,现代汉语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算长,是一种很新的语言,甚至能把它看成是一种新发明的语言。但是,现代汉语的出现,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没有现代汉语,就没有现代中国。这个影响在文学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写作从此告别了文言文,形成了有近百年历史的现代散文的写作。这些散文既是现代汉语形成的见证,又是一座文学宝藏,其中有很多语言和文字的奇珍异品。因为有了它们,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今天还是一个散文大国。
我们编选的这本散文集,一共46篇文章,只是这座文学宝藏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也是实在不得已,考虑到整本书的篇幅不能太长,每篇文章不要超过五千字,读者又主要是年轻的朋友,很多好文字就不得不割舍。所以这个集子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窗口。不过,小小的窗口外面,是一个美妙瑰丽的世界。
在英文里,诗歌(poetry)、散文(essay)、小说(novel)的缩写,正好是pen(笔)。真巧了,这好比在诗歌和小说之间,存在着一个叫散文的语言空间,这个空间很大,海阔天空,山高水长,手里有一支笔,就如同抓住了一匹飞马的缰绳,写作可以升天入地,任意驰骋。
这个空间又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现代汉语被当作研究材料,被放在无数的散文写作的“烧瓶”里炼制,然后得到许许多多叫作散文的晶体。
可以说,散文写作和散文作品的丰富性,使它有一种其他文学形式不能比的斑斓光华。
散文的品种非常丰富,绝不是只有抒情和记事,无论文体、风格、样式,还是内容、题材、立意,都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什么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写作散文,可以典雅,可以朴素;可以修辞精致,在遣词造句上使劲用功,也可以朴实无华,文句不加多少修饰;可以有意让“白话文”融进一些文言因素,使文意间带点儿古意,也可以让文章更接近口语,“我手写我口”,简直就是我们日常里的大白话。总之,散文写作要自由。当然,散文绝不能只是自由的表达,散文世界后面还应该有更广阔的知识世界,其中有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也有现实人物、现实故事,它们在作家笔下栩栩如生,活龙活现,于是无论现实的还是历史的,都化作了生动的知识。我们认为,它们才是散文写作真正的意义所在。
年轻的朋友们,与青春做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拿起一本好书,读一篇好文章,就像和朋友一起轻快地穿越一片无边无际的田野,每向前一步,空气就更新鲜,视野也更开阔。
《给孩子的散文》将与你同行。
2. 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假若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
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否则就太不好意思了。一进门,我看见吴太太的脸比晚日还红。我心里一想,便想到了小花猪。假若小花猪丢了,或是出了别的毛病,组缃先生的阔绰便马上不存在了!一打听,果然是为了小花猪:它已绝食一天了。我很着急,急中生智,主张给它点奎宁吃,恐怕是打摆子。大家都不赞同我的主张。我又建议把它抱到床上盖上被子睡一觉,出点汗也许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这年月的猪比人还娇贵呀!大家还是不赞成。后来,把猪医生请来了。我颇兴奋,要看看猪怎么吃药。猪医生把一些草药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儿里,使小猪横衔着,两头向后束在脖子上:这样,药味与药汁便慢慢走入里边去。把药包儿束好,小花猪的口中好像生了两个翅膀,倒并不难看。
虽然吴宅有此骚动,我还是在那里吃了午饭,自然稍微的有点不得劲儿!
过了两天,我又去看小花猪——这回是专程探病,绝不为看别人;我知道现在猪的价值有多大——小花猪口中已无那个药包,而且也吃点东西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骗了顿饭吃,并且提出声明:到冬天,得分给我几斤腊肉。组缃先生与太太没加任何考虑便答应了。吴太太说:“几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听罢,都出了冷汗!
3. 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饭,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
来重庆,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书屋。有的说也罢,没的说也罢,他总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假若不是别人都困得不出一声了,他还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着他谈,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里两点钟。表、月亮、太阳,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时间。
比如说吧,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宗融兄,不是三点有会吗?该走了吧?”有人这样提醒他,他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走。“七点吃饭,早回来呀!”大家告诉他。他回答一声“一定回来”,便匆匆地走出去。
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即使不是这样,他在五点以前也不会走到观音岩。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谈,至少有十分钟的话。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过去解劝,还许把别人劝开,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遇上某处起火,他得帮着去救。有人追赶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看见某种新东西,他得过去问问价钱,不管买与不买。看到戏报子,马上他去借电话,问还有票没有……这样,他从白象街到观音岩,可以走一天,幸而他记得开会那件事,所以只走两三个钟头,到了开会的地方,即使大家已经散了会,他也得坐两点钟,他跟谁都谈得来,都谈得有趣,很亲切,很细腻。有人刚买一条绳子,他马上拿过来练习跳绳。五十岁了啊!
七点,他想起来回白象街吃饭,归路上,又照样的劝架,救火,追贼,问物价,打电话……至早,他在八点半左右走到目的地。满头大汗,三步当作两步走的。他走了进来,饭早已开过了。
所以,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若说随便什么时间,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不出门,你哪时来也可以,我们便说“马宗融的时间”吧!
4.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围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闻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责任编辑 张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