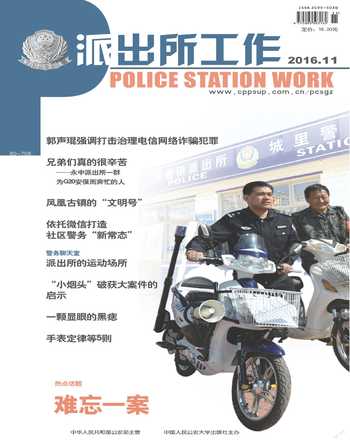沉重的录取通知书
王礼祥
20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个夏天,年轻的我调到一个区派出所。因所里无房,暂住在供销社院内的宿舍。一天早晨,因晚上加班,我睡得正香,忽然听到一阵轻轻的读书声。我起床走出一看,只见梧桐树下,一个短发的女孩正倚树读书。她蓝衣衫、黑布裙,薄薄晨雾之中,宛若电影里民国时期的女生。此后,经常见她手拿着书在院子里姗姗走过。我想,她应该是附近中学的老师或学生。
一天晚上,我正在所里整理材料,门廊的灯光一晃,一个身影闪了进来,我起身一看,正是她。我忙着让坐,她站着有些支吾地说,你是学法的,请教一个问题,女方退婚时,收下的彩礼要退吗?我说,一般情况,是要退的。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声谢谢,就快步离开了。后来,她又去我的宿舍,向我借阅《警探》《啄木鸟》之类的法制刊物。有借有还的,渐渐地也熟悉了,知道她叫小丽,家在邻县的农村,有个姐姐、一个上小学的弟弟。母亲身患骨癌去世,在这个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又患肺结核回老家疗养。高考过后的她过来这边,一边代替父亲的工作,一边等着分数。
她绝对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炎热而又焦灼的暑假,改变了她的人生。
8月初的一个夜里,供销社百货门市部在有人值守的情况下被盗手表13块和没有及时缴存的营业款800多元。现场门窗完好,没有翻动的迹象,虽然没能提取指纹、脚印等证据,但我们还是发现门市部北山墙顶端的那口气窗有翻越的痕迹,同时,在气窗的砖棱上提取了几根紫红色的纤维。由此断定,作案者是从这个离地面近3米的高气窗翻越过来的。
隔壁农资门市部有两位营业员,一位是即将退休的女职工,另一位就是临时代替父亲上岗的小丽了。年迈的女职工,不可能爬窗入室;柔弱可人的小丽,也不可能钻窗作案。而那个晚上,恰又是小丽值班。犹如电石火花,猛然,我想起了他!谁?小丽的弟弟。我见过他,黑黑的、瘦瘦的,手拿着弹弓,整日捉鸟爬树的,“猴气”得很。我在兴奋的同时,心底里隐隐有一丝担忧。然而,这种担忧,因为小丽的投案兑现了。
案子是她和弟弟作下的。她说,她需要钱,不,是姐姐需要钱——两年前,急于给患癌症的母亲筹钱治病,漂亮的姐姐以3000元的彩礼,和村干部的儿子订了婚。那个青年一身的“痞气”,姐姐十分反感,因此婚期一拖再拖。她曾劝姐姐退婚,姐姐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她心里明白,为给母亲治病,这个家已退不出姐姐的“彩礼”了。过了这个中秋节,姐姐最后的婚期就到了,她为绝望的姐姐抓狂。但当她看到隔壁百货门店里生意红火,当她得知那个四十多岁的承包主是一位在事故中双耳失聪的退伍工程兵,当她看到山墙上那个不大通气窗,她猛然看到一缕希望和曙光。这希望和曙光像火焰一样在她心底愈燃愈烈,最后融化成姐姐身上婚姻的枷锁。于是,那个晚上,她叫上弟弟,用门市部里出售的梯耙和绳索,让弟弟钻了过去……
送她去看守所时,一副锃亮的手铐铐在她洁白细嫩的手腕上。她低着头,身子战栗着,长长的睫毛挂着泪珠,让人不敢凝视。她抽泣着问,如果我考上大学,还能上吗?警车里一片沉默。
一个月后,当她哭哭啼啼的姐姐把一份师专的录取通知书放在我的桌上时,心里的那份沉重和惋惜,让我怎么也拿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