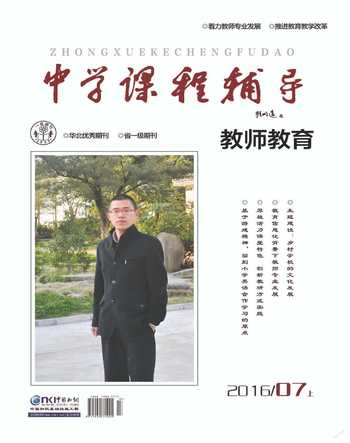仇恨的恶之花中的悲壮美
佘长欢
摘 要:现代悲剧大师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不仅是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安排上取材于古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从复仇这一主题来看,更是这一主题在二十世纪的悲剧作品中的最为壮美、最为有力的回响。
关键词:奥尼尔;埃斯库罗斯;《悲悼》;《俄瑞斯忒斯》;复仇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13-087-2
奥尼尔的悲剧《悲悼》三部曲可谓是奥尼尔20到30年代一部重要的戏剧代表作,这部作品体现了奥尼尔在这一创作阶段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一部具有古典美的现代意识剧作。《悲悼》三部曲是以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为蓝本改编的。奥尼尔的这三部剧本的每一部都同一部古希腊剧本相应。
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由《阿伽门农》、《祭酒人》、《复仇神》组成。主要叙述主人公饿瑞斯忒斯为父报仇的故事。特洛伊战争爆发后,阿伽门农统率希腊大军准备出征,出征前把自己的大女儿伊斐格尼亚作为贡品以祭神,十年后,阿伽门农带着女俘虏凯旋而归。凯旋之夜,其妻克吕泰涅斯特拉伙同情人埃葵斯托斯杀死了阿伽门农,以报女儿被杀之仇。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得到阿波罗神谕,叫他为父报仇。在姐姐厄勒克特拉的协助下,就在昔日阿伽门农被杀之地杀死了其母及其奸夫,复仇神立刻出现,追逐俄瑞斯忒斯,俄瑞斯忒斯四处奔逃,最后在雅典娜女神的庇护下,被宣告无罪,复仇的冲突得以和解。
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包括《归家》、《猎》和《祟》,故事发生于新英格兰一座海滨小城里的孟南家族中。艾拉斯·孟南从战场凯旋而归,其妻克莉丝汀厌弃他的冷漠虚伪,爱上了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飞艇号”船长卜兰特。凯旋之夜,克莉丝汀与卜兰特密谋毒死了艾斯拉。女儿莱维尼亚发现了母亲及其奸夫的奸情和罪行,发誓要报仇。(莱维尼亚的仇恨即源于对父亲的爱,她有恋父情结;又源于对母亲的嫉妒,她也爱着卜兰特;后又因爱成恨。)儿子奥林从战场上归来,维尼向他告发了母亲的奸情(奥林具有恋母情结),经证实,奥林相信了这一切,并枪杀了卜兰特,克莉丝汀也因绝望而自杀。在完成了对母亲的复仇之后,为了使奥林与自己精神恢复,与奥林同游了东方海岛,回来后,他们越来越深的陷入家族的影响之中,更像自己的父母了。更体现出孟南家族的特征,他们的感情冲突进一步深化。最后,奥林在忏悔中自杀,莱维尼亚孑然一身将自己封锁在孟南家的大房子里,以此来赎孟南家的罪。
显然,从叙述结构的角度来看,两个悲剧都具有同一个追逐——复仇的神话故事原型;两位剧作家都将主人公置于一种爱恨情仇的情感极端状态;都成功刻画出人处于种种极端状态中所呈现的粗犷、悲壮的古希腊悲剧中的古典之美。而在对复仇这一极端的人类情感的展示上,可以说奥尼尔达到了古希腊悲剧同样的高度。从荣格的阴影理论来分析这两部戏剧作品就可得出以上结论。
阴影理论是荣格的原型理论中所论述的每个人的人格中所具有的四种原型之一。他认为,阴影是人的心灵中遗传的最黑暗、最深沉的邪恶倾向。它是恶,是道德的负面价值,它同样寻求投射,为防止这种投射造成灾害,荣格认为要通过“个性化”,让意识的阳光照亮潜意识的阴影。《俄瑞斯忒斯》和《悲悼》这两部悲剧是追逐——复仇的悲剧,剧中人物往往有不可遏止的激情,让自我心灵中的恶之花充分的绽放,让无意识的阴影笼罩着不可避免的可怕命运。他们像《拉奥孔》群像一样,永远凝定在最惨烈痛苦的一刻,而这最惨烈痛苦的一刻恰恰是最具有悲壮之美的。《俄瑞斯忒斯》中的克吕泰涅斯特拉从来就是一个光辉耀目的伪善者,为了报复阿伽门农的杀女之仇,居然伙同自己的情夫在丈夫凯旋之夜,亲手杀死了阿伽门农。在这里我们领略了阴影的狂暴之力如何使一个弱女子具有了男性的钢铁般的力量。《悲悼》中克莉丝汀厌弃丈夫的冷漠、刻板、虚伪,爱上了具有浪漫气质的卜兰特,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不惜铤而走险,伙同卜兰特毒死亲夫。阴影的狂暴激情使克莉丝汀一反天使的温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恶魔。该剧中最动人也是最具有阴影气质的形象就是莱维尼亚了。她具有强烈的本能欲望,但又受着清教主义思想的影响,本能使她抛弃一切禁忌,而清教观念使他摆脱不了罪恶感,从而各种极端的人类情感在她身上点燃了焕彩炫目的生命之光。在莱维尼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爱与恨的激情迸发,她的性格不仅是罕见的,而且是闪闪发光的。她爱她的父亲,恨她的母亲。对卜兰特,她始爱终恨;对奥林,她又爱又怕;对彼得,她忍痛牺牲。她在爱与恨中挣扎,迸发出耀目的激情。她由于爱而不得,最终成恨,受挫的欲望本能使她心灵中的阴影急剧地膨胀起来,像可怕的影子一样时刻追随着她的母亲,她胆大心细,机警沉着。一开始,面对卜兰特和克莉丝汀的联合攻势,她屈居下风,但很快就先发制人,转败为胜。在爱与恨的战场上,她像将军一样,指挥若定。奥尼尔天才般刻画了一个更为熠熠生辉的充满生命激情的女性形象,她对母亲的所给予的逼迫让人感到恐怖,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奇怪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对于把生活当作一场战争,只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才能成为英雄的人们来说,她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复仇的阴影毕竟是一种恶的驱使力,可怕的恶的阴影在她心中的膨胀又使她紧紧地控制住因对母亲之死抱有负罪感而精神崩溃的弟弟奥林,不断用清教意识强化他的信念,却最终也因软弱走向了自杀。这使得莱维尼亚最终清醒的面对了复仇这一恶的阴影的命运,家族的命运中的可怕的毁灭性。她最中也在无尽的忏悔与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复仇烈焰燃烧下的莱维尼亚就像复仇女神与智慧女生的结合体,用她高大的阴影控制着整个家族命运的最后导向。
从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到奥尼尔的复仇悲剧《悲悼》三部曲,为什么一条复仇的线索绵延不绝呢?从拉康的“欲望”理论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欲望来源于匮乏,匮乏是一种最古老的、也是最持久的动力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阴影驱使他们延绵不尽的复仇,而复仇又可溯源于一种爱的匮乏和缺失。爱情的种子被洒在贫瘠贪婪的土地上之后,再加上嫉妒这一毒液的浇灌只能开出仇恨的花朵,结出死亡的果实。
从《俄瑞斯忒斯》和《悲悼》这两部剧的总体上来看,它们都被仇恨所笼罩,这就使得作品中的仇恨就有了如命运一样的本体论特性。两部戏剧中仇恨就像命运一样左右着剧中人物的行为,因为古希腊悲剧一向以命运悲剧著称。埃斯库罗斯等悲剧大师最善于呈现人与命运厮杀搏斗中的所产生的悲壮的古典美。奥尼尔的悲剧也达到了这种悲壮美,并且走的更为深远。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命运是被神所左右的。同样仇恨也由神来左右。像在《俄瑞斯忒斯》中阿伽门农家族的仇恨是由于阿特柔斯被众神所诅咒引起的,可以说仇恨发端于众神之手。而俄瑞斯忒斯的具体的复仇行为也是听从了太阳神阿波罗的指引开始的。最终俄瑞斯忒斯被复仇神追杀也是女神雅典娜将他赦免的。可见仇恨的结束也是神所操纵的。然而,在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中的仇恨即人物命运的走向却是来自同一个方向——人内心的欲望。孟南整个家族所笼罩的仇恨的幽灵就是孟南家族中每个人的因爱而不得后产生的恨的欲望。对于仇恨这一人类的极端情感奥尼尔运用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在剧中给予诠释。奥尼尔自己也写到:“命运是由这家人家的内部因素所造成的这种现代心理学的观点,近似于命运是由外部力量,超自然的力量所造成的这种希腊人的观点。”[1]
总之,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还是奥尼尔的《悲悼》都表现了复仇这一主题下的个人生命力的迸发。通过剧中人物在仇恨的恶之阴影下所做出的惨烈而痛苦的厮杀都使他们的悲剧产生了一种粗犷的、悲壮的古典美,对仇恨这一人类的极端心理状况的诠释,他们也都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参考文献]
[1]尤金·奥尼尔的剧本.(美)弗洛伊德(Floyd,Virginia)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