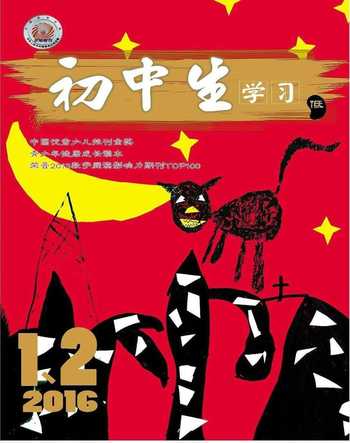心灵感应存在吗?
刘晓峰
那些心灵感应的故事
一对生活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双胞胎,一出生就被不同的家庭收养,40 多年后二人重逢时发现他们的生活惊人地相似。兄弟俩的名字都叫“詹姆士”,都在机械和木工工艺方面具有天赋。二人都有过两次婚姻,他们的前妻都叫琳达,而现任妻子的名字又都是贝蒂。他们各有两个儿子,分别名叫詹姆士·艾伦和詹姆士·艾兰。
很多人看到这些惊人的相似都感到太神奇了,这难道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心灵感应”吗?不过还有比这更神奇的故事。
里克和罗恩是美国的一对双胞胎。1995年1月,里克从休斯敦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非洲安哥拉的一家石油公司审核账目。在安哥拉起初的几天很平静,但5月31日凌晨4点钟,里克被腹部剧烈的疼痛惊醒。他立即去了医院,医生为里克做了全身检查,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直到4个小时之后,里克身上的疼痛才逐渐消失。
但坏消息却在当天夜里降临,里克的双胞胎哥哥罗恩,前一天夜里在美国家里被杀。验尸报告表明罗恩的死亡时间是美国中部时间晚上10点30分,正是里克在安哥拉夜里因腹部疼痛惊醒的时间。里克相信他感应到了哥哥被杀时的剧烈疼痛。
双胞胎之间到底有没有“心灵感应”?美国《双胞胎世界》的编辑勃兰特说,他听说过许多与里克的经历相似的故事,并且相信双胞胎之间存在一种超自然的沟通方式。
不仅双胞胎之间,夫妻之间也有心灵感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位名叫珍妮的女子收到了美国军方签发的丈夫的死亡通知书。此后,珍妮多次梦到丈夫在一个迷雾笼罩中的庄园里呼唤自己。于是,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之路。辗转数年后,终于在法国的一个废弃庄园里找到了和她梦中一样堆满尸骨的地窖。其中一具遗骸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刻着J&M的戒指,这戒指正是她丈夫莫林的。
心灵感应的理论依据
心灵感应是否真实存在?主流科学家都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心灵感应都是些不靠谱的传说,无法进行科学验证。但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鲁伯特·谢尔德雷克20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科学实验,以证明人类的心灵感应和预感等现象可以从生物学角度得到解释。
当我们想念某个朋友的时候,他正好就打来电话;当我们感觉有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就会回过头去,那人果然在那里。谢尔德雷克认为,这是正常的动物行为,是动物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演变,为适应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是什么促使谢尔德雷克做出这样新颖的结论呢?谢尔德雷克认为,人类的心灵是受外部环境影响的,但同时也在周围环境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与电磁场的存在一样,心灵也有自己的场域,或曰“形态共鸣场”。人体与心灵的信息就随着形态场四处流动,理论上就跟电磁场一样,可以传播到无限远,其细微的痕迹有可能被任何人捕捉。
但是,一般情况下,只有自己最亲的人才有可能与你在形态场里发生心灵上的共鸣。这其中的道理是其如同电磁场一样无处不在,但若需要接收特定的电磁信息,必须有对应的工具。我们必须用电视机接收电视台发出的电磁波,用手机接收别人拨打的电话。因此,对于人体的“形态共鸣场”,最有可能捕捉到这种心灵痕迹的是自己的亲人。心灵感应现象基本只在亲朋好友之间发生。
正统的生物学理论认为原子构成分子、分子构成细胞、细胞构成器官,生命就像机器一样,由零件组装而成。而所有的生命现象都被认为原则上可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进行说明。例如生命的遗传都是通过基因来完成的,因此现在生物学界最重大的使命就是破译基因密码。
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意识到,除基因遗传程序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在有机体中起作用,这就是生命的“形态共鸣场”。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说明生物体发育成长的过程,就有生物学家引入了“形态共鸣场”的概念。有一种扁体蠕虫,当它被切成两半时,每一半都会发育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一些科学家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这种再生是受一个特殊的生物场支配的,正像一根磁铁被截成两半时会形成两根新的磁铁,每一根磁铁都有自己的完整的磁性一样,当扁体蠕虫被一分为二时,它的形态共鸣场就分裂为两个完全相同的场。
到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家伊纽欣认为,对人类而言,“形态共鸣场”附属于人脑,当这个场从人脑不断散发开去,与另一个人的大脑产生共振效应时,就有可能产生心灵感应现象。
用实验证明这微弱的效应
这种“形态共鸣场”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呢?谢尔德雷克声称,我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就受形态共鸣场的支配。科学家的实验证实,如果一只老鼠学习到一种新的行为方式,那么后来的老鼠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学习到这种行为方式。学习完成这种任务的老鼠越多,则后来的老鼠就越容易学习这种本领。因此,若第一批有上千只老鼠在实验室里被训练学习进行一种新的操作,那么第二批老鼠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学到这种本领。
为什么后来的老鼠学习新事物的速度要比前面的老鼠快呢?这就是“形态共鸣场”在发挥作用,在一个实验室里,当越来越多的老鼠掌握了一种行为方式时,实验室里就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形态共鸣场”,让后来的老鼠产生心灵感应,使它们学习这种新行为方式来得更容易些。
我们人类身上也有这种“形态共鸣场”效应。几年前,英国一家电视台对“形态共鸣”效应进行了实验。电视台准备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不仔细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不过有很多颜色夹杂其中罢了。但其实画中有画,其中一幅是一个戴帽子的女性,另一幅是一个蓄着胡子的男性。
接着,电视台找来第一批志愿者,让他们辨认画中隐藏的图像,然后对第一批志愿者揭晓答案。再接下来,电视台找来第二批志愿者辨认画中隐藏的图像,结果是第二批志愿者辨认出来的比例,竟然比第一批志愿者高了三倍。
这个结果正说明,第一批志愿者已经知道了答案,这给了那些素昧平生的第二批志愿者某种暗示。这种暗示在实验室里产生“形态共鸣场”,从而使第二批志愿者答案的准确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心灵感应处处见
毋庸置疑,对于普通人来说,生物的这种“形态共鸣”效应是极其微弱的,就像电磁场处处充满我们的空间,但如果没有专门的仪器,我们根本不可能意识到它的存在一样。但心灵感应在我们理性的遮蔽下显得神秘和不可思议,而且得不到主流科学家的承认。
但事实上,心灵感应现象在动物界却普遍存在、屡见不鲜。
如果你仔细观察鸟类的飞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它们为什么在飞行时好像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乱飞?这类奇特的动物现象还有很多:鲑鱼等鱼类每年往返于河流与海洋之间,候鸟每年迁徙数千公里,它们是如何知道飞行或游动路线的呢?
人们用自组织理论来解释飞鸟的整体行为,又用磁场理论来解释飞鸟的迁徙行为,又用基因程序设计来解释鱼类洄游行为,但这类解释却没有抓住动物行为的本质,事实上它们的这种群体行为更像是彼此之间的心灵感应。
动物间发生心灵感应,是“形态共鸣场”在发挥作用。当成群的鱼或鸟聚集在一起时,这个“形态共鸣场”产生了共振现象,动物之间的心灵感应就发生了。
其实,在人类文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很常见。20 世纪30年代,悉尼大学人类学家埃尔金教授在对澳大利亚原住民长期调查后发现,原住民之间心灵感应经常发生,比如有一个原住民在距离家乡相当远的地方工作,突然有一天他对同事说自己的父亲过世了,而他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他急急火火赶回家去,一看果然是这样。在埃尔金教授的调查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心灵感应对遗传的作用
人类的心灵感应是无法被扼杀的,它只是被压制在人类的潜意识之中。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生来怕黑、怕蛇,却对花有着留恋?这是因为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的反应通过一代代遗传存留在人类的种族记忆中,成为人类普遍拥有的集体潜意识。
问题是,这种有关集体潜意识的记忆是如何在我们出生时就在我们大脑中打下烙印的呢?又是留存在我们大脑的哪一部分呢?
生物学中一个未解之谜便是记忆本身。我们如何记住昨天的事情,又如何辨认周围的人,等等,所有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记忆的确颇为神秘。通常人们认为,记忆在大脑中肯定是有一些物质基础的,就像计算机中的存储芯片一样。但直到现在,并没有人真正发现大脑中哪个部分是记忆所在,包括那些利用老鼠和猴子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研究人类记忆的科学家,也一无所获。
谢尔德雷克由此指出,当我们努力寻找大脑中的记忆物质时,其实是走错了方向,我们的大脑根本不是记忆的存储之地,它更像是个跟电视机一样的调频接收系统,通过“形态场”共鸣的方式找到我们各自的记忆。
正是这样的调频接收系统,使我们在意识的最深处接收到了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的记忆,这就是集体潜意识的由来。这种集体潜意识在动物身上也存在,例如蜜蜂的舞蹈语言、鸟类的筑巢及歌唱等本能,也都是它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
我们通常说遗传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有形的基因怎么能决定这些无形的东西呢?基因只是指导了蛋白质的合成,决定了蛋白质中氨基酸的种类、数目、排列顺序等等,它没办法遗传人类或者动物的群体本能。因此,从遗传角度来说,基因的作用也许被高估了,而正是因为心灵感应遗传了更多的信息给后代,才由此塑造了不同的动物风貌。
当然,在如今这个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机械式科学时代,“心灵感应”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幻想,从不会进入主流科学家的视野。因此当谢尔德雷克在20多年前推出自己的理论时,很多科学家把他的理论视为胡言乱语。
的确,谢尔德雷克教授的论点不仅奇特,还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所能理解的科学范畴。然而,我们知道,在量子物理学中,粒子之间有一种幽灵般的“超距感应”,两个具有关联的粒子,无论它们相互间的距离多么遥远,其中一个状态发生变化,另一个也会即刻发生相应的状态变化。既然小小的粒子都有幽灵般的感应,那么动物之间、人类之间存在心灵感应有什么奇怪呢?
编辑/佟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