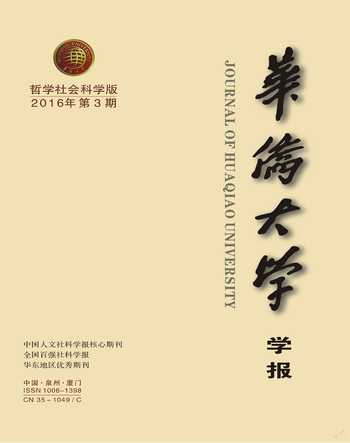“非印学因素”与篆刻史研究范围的拓展
赵洋 乌东峰
摘要:篆刻史的研究范围并不仅仅是对篆刻作品字法、刀法、章法等“印学因素”的考察,同时篆刻艺术历史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由“印学因素”的传承而推动的,在构建完整真实的篆刻史时要求我们注意到“非印学因素”。“非印学因素”是指除去篆刻艺术本体内容之外的其他要素,诸如篆刻活动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赞助人参与、地域因素、社会文艺思想等内容。“非印学因素”的变动往往会改变篆刻史的写作模式、叙事方式、研究内容等。
关键词:“非印学因素”;篆刻史;篆刻艺术;研究范围
中图分类号:J05-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3-0134-11
一“非印学因素”与篆刻史的研究范畴
为所研究的领域划出清晰的界限,是所有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努力的工作。对某一学科的研究范畴作出界定,能够使得该学科的研究方向更为清晰,但是,研究方向越是清晰明确,往往该学科的研究目标越具有方向性与针对性,对于一些看似不属于这个学科的东西也会有意无意地遗失掉。事实上,很多“界限”的划分都是徒劳无益的。针对人文学科在研究中“划界限”的做法,法国著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
今天它们正在比以往更为繁忙地阐释它们各自的目标、方法和优越性——这样做既不冒险,也不费力。它们争先恐后地为边界线进行诡辩,而那些边界线有的把它们区分开来,有的并没有区分它们。[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当代篆刻研究者为了构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也努力梳理划分篆刻学应该有的研究内容,其大致的研究范畴有三个大方面。第一个大方面是篆刻学之“史”的部分,包括古代玺印史、流派篆刻史、明清印论史及其文献资料;第二个大方面是篆刻学之“论”的部分,包括篆刻美学原理、篆刻技法原理、篆刻创作原理、篆刻赏评原理;第三个大方面是篆刻学之“实践”的部分,包括篆刻技法训练、篆刻创作指导、篆刻批评指导、篆刻教育与教学研究。这三个部分对构成篆刻学这门学科的整体完整性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然而,作为篆刻艺术的研究对象,上述这
收稿日期:2016-04-20三个部分似乎稍显单薄。当代篆刻史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对名作、名家的叙述,这在明清流派篆刻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按照印人、印作的编年,进行顺序叙述仍然是当今篆刻史研究的主流。如此正好陷入了一个无法继续深入研究的陷阱,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论述文学史时所指出的一样:
应当承认,大多数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90页。
当代篆刻史研究如何突破“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篆刻作品的印象和评价”的现象,是篆刻史研究者不得不重新面对的难题。在篆刻史研究过程中,除却上述所说的“史”“论”“技法实践”这三个部分,篆刻学的研究是否还包含其他内容?尤其是在篆刻史的研究过程,我们能否还仅仅着眼于篆刻家的介绍和作品的罗列?贡布里希在论艺术史时曾谈到:
艺术史是生活这件无缝之衣的一根丝线,不可能把它与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或者体制史这些丝线离析之后不留下若干松散的线头。而从何处着手离析,又如何组织叙述,这对于艺术史家就象对于任何其他史学家一样,既取决于他想知道什么,也取决于他认为可以作何发现。因为,尽管我说是无缝之衣,可是传到我们手里的却是一堆零乱的五花八门的知识。[英]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范景中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篆刻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它与整个社会史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史中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动都有可能在篆刻史中得到反馈,这就不得不提示我们关注篆刻史这根“丝线”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以及它们的交叉地带。为篆刻史划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剪断了篆刻史这根“丝线”与其他“丝线”的联系。
上文所谈到的,构建篆刻学的三个大的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篆刻的“印学因素”,因为它们全部发生于篆刻艺术的本身范围之内。
除却这些因素,篆刻艺术的研究是否会与其他各门学科发生关联,如同贡布里希所说的那些“零乱的五花八门的知识”是否参与了篆刻史的构建,是值得思考的。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因素,篆刻家的交往对象,乃至其生活的地域、作品传播的方式等非直接、非显著的因素同样影响到篆刻史的前进过程与方向,像这样的非显著因素,我们可以称之为影响篆刻艺术发展的“非印学因素”。
如果将篆刻史比喻成一座城堡,那么“印学因素”是构成这座城堡的建筑、人口、物产、社会制度等,但是这座城堡有着严密的围墙,它如此顽固的约束着人们观察这座城堡的视线,而“非印学因素”则是这座城堡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土壤酸碱度等,这些也是构成城堡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这座“城堡”规模大小、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非印学因素”对篆刻史的写作模式、叙事手法、研究范围与内容的影响如同气候环境等对城堡的影响一样重大,要想改变当代篆刻史的研究现状,“非印学因素”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切入口。
在“非印学因素”理念的影响下,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地域等因素被纳入到篆刻史考察的范围之内。此外,在“非印学因素”的影响下,传统的对篆刻家生平的简单介绍也应该逐渐深入到篆刻家周围的人与事件。总之,社会历史中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因为这些看似与篆刻漫无联系的动向,最后都可能导致印章风格的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篆刻史前进的轨迹。
二“赞助人”角度对篆刻史研究的意义
在艺术史研究中,“赞助人”角度作为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系统的从“赞助人”角度出发对艺术史进行研究,首推英国的艺术史学者哈斯克尔,他在著名的《赞助人与画家:巴洛克时代的艺术与社会之关系研究》(Patrons and Painters:A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Ar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Baroque)一书中运用从赞助人角度、而非艺术家角度切入到艺术史研究的方法,从而改变了人们以往看待艺术史的角度。关于哈斯克尔的介绍与成就可参阅曹意强《艺术与历史》附录1《哈斯克尔小传》,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近十年来,有学者将哈斯克尔的“赞助人角度”运用到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上,2003年,《荣宝斋》第一至五期连载了李铸晋等人“中国画家与赞助人”的系列论文,首次以“赞助人”为视角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史。虽然“中国画家与赞助人”系列文章存在一些偏颇,但是它们却为当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样也为篆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
明清流派篆刻史中是否存在“赞助人”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在篆刻史研究中,“赞助人”必须不是普通的受印者,他必须为篆刻家提供一定的金钱、生活物质保障,或者为篆刻家的声誉建立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赞助人”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篆刻修养,他的品味、爱好等又有能够影响到篆刻家作品的可能。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才有可能以“赞助人”的角度进行篆刻史的研究。这一现象早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存在,在明清时期,能够具备这样条件的人有很多,这就为我们能够采用“赞助人”这个角度研究篆刻史提供可行性。
我们可以将明清时期篆刻“赞助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直接为篆刻家提供金钱、生活物质保障的直接“赞助人”;二是为篆刻家的声誉建立起到至关重要的“赞助人”,尽管后一类的赞助现象不像第一类那么明显,但在篆刻家的生活中,其意义并不比第一类低。
关于第一类的“赞助人”,其主要特征即是为篆刻家提供金钱或物质资助。最显著一个例子是林皋与他的赞助人吴晋。林皋,字鹤田,又字鹤颠,福建莆田人,是清代初期江南一带颇具盛名的篆刻家,常年客居常熟,擅长篆刻工稳规矩一路的印章,著有《宝砚斋印谱》。在林皋的篆刻生涯中,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扮演着“赞助人”的身份,此人即是吴晋。吴晋,字介兹,江南江宁人,尝从著名文人周亮工游,对篆刻有着独立的见解,吴晋《宝砚斋印谱序》中言:
今天下藏印之多,无如栎园周司农矣。当司农盛时,四方操是艺来者履常满。予从游司农之门,首尾殆二十年,因尽得见天下印人,又有印癖,颇寻讨古今论印本原及奇正美恶。[清]吴晋:《宝砚斋印谱序》,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538页。
吴晋本人能够“尽得见天下印人”,同时“又有印癖”,对篆刻的“奇正美恶”自有判断。吴晋论印喜好平正规矩一脉,对晚明至清初的篆刻家曾作出过评价:
自文国博、何主臣而外,若金一甫、朱修能、邱令和、江皜臣,故为印之正灯……他若陈师黄、丁秋屏,非不刻画古人,第好奇立异,间以隶法杂入,近于妖妄。[清]吴晋:《宝砚斋印谱序》,第538页。
吴晋上述言论清楚明确的表明了他反对“好奇立异”的印学观点,而林皋工整端庄的篆刻风格正好为其欣赏。林皋曾经寓居吴晋的住所,吴晋为其提供生活保障,林皋则为吴晋刻印多达三四百方,吴晋《宝砚斋印谱序》云:
海虞林子鹤田,与余友钱湘灵先生善,昨秋同遇秣陵,因留余一砚斋四馀月,前后所作印不下三四百枚。[清]吴晋:《宝砚斋印谱序》,第538页。
我们今天还能见到林皋为其作的三四百方印中的一部分,也完全是工整平稳一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相对较为工整平稳的作品应该是林皋在吴晋的授意下创作的,吴晋喜好平稳工整印风的观点参与了林皋篆刻创作的过程。
印谱的辑录与刊行耗时费财,一般印人往往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刊行印谱,这就使得明清时期众多印人求助于“赞助人”出资刊行印谱。这些“赞助人”多是地方官长或富甲一方的商人,出于对风雅的追求,往往会无偿出资为印人刊行印谱。这种看似无偿的行为,实际上隐藏着“赞助人”和印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印人需要“赞助人”的人力物力财力刊行印谱,另一方面“赞助人”也需要印人的艺术作品为其装点门面,从而博得雅好文艺的名声。这种微妙的关系导致了明清时期篆刻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即“赞助人”在为印人刊行印谱时,印谱的冠名权转移到了“赞助人”手中。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清代初期如皋印人许容与其赞助人胡介祉的赞助例子。许容(约1665—1696),字实父,号默公,是清代初期十分著名的印人,他曾有过短暂的仕宦生涯,但是其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落魄失意中度过的,刊行印谱这样耗费财力的事情对于许容来讲多少有些困难。康熙十九年(1680),许容人生中第一本印谱问世,此时他客居北京,得到胡介祉的赏识。胡介祉,字茨村,一字存仁,号循斋,直隶大兴人,官至河南按察使。康熙十九年,许容曾在胡介祉家长住,生活得到胡介祉照拂。在胡介祉的授意下,许容历经七个月为胡介祉创作了数百方印章作品,这些印章多是胡介祉之姓名印、斋馆印等,最后这本印谱的命名更是以胡介祉之园林“谷园”为名,命名为《谷园印谱》。七年之后,许容复至北京,在胡介祉家逗留数月,在三个月的时间内,许容又为胡介祉创作了百余方印章。这些印章由胡介祉出资刊印成谱,这次的命名依然是以胡介祉园林“谷园”为名,七年前所刊印之印谱成为《谷园印谱》卷一,此次刊行的印谱成为《谷园印谱》的第二卷。到这里,这两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许容又为胡介祉篆刻了一百余印章,取名《韫光楼印谱》,这本印谱名字中的“韫光楼”依然是胡介祉的斋馆名称。
从康熙十九年到康熙二十八年,许容多次客居胡介祉家,一直追随胡介祉左右,胡氏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学习条件,并出资为其刊印印谱,而许容则按照胡介祉的授意,为胡介祉篆刻了数百方印章,并以胡介祉斋馆名称作为自己印谱之名,以此作为对胡介祉的回报。通过许容和其“赞助人”胡介祉之间微妙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赞助人”,胡介祉的影响渗透到许容篆刻创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从印章内容,到印谱命名,胡介祉的影响无处不在。尤为值得注意的,胡介祉身居高官,其好异尚奇,追求炫目的诉求,在《谷园印谱》和《韫光楼印谱》中也有所表现。在上述这两本印谱中,许容的印风颇为杂芜,各种技法、多种风格并存,力求全面。作为“赞助人”的胡介祉,其个人品味是导致许容印风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如同胡介祉与许容这样的关系,在篆刻史中还有很多,像胡介祉这样的“赞助人”是如何参与到篆刻史的构建,如何影响印章风格的转变,是我们一般篆刻史研究者所忽略的。
而第二类的“赞助人”,其主要特征则是通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为印人的声誉建立与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清代初期,周亮工一直扮演着这类“赞助人”的角色。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陶庵、减斋、栎园等,原籍河南祥符,后迁居南京。周亮工其人虽为贰臣,其著作在清初又受到禁毁,但是其在诗文、篆刻、仕宦经历中积攒了较好的社会声誉,他一生广为提携后进,为众多诗人、印人提供过赞助与庇护,这些印人也因为周亮工的扬誉而名满海内。清顺治四年(1647)周亮工擢升福建按察使,入闽就职,其在闽八年,福建一地的篆刻创作队伍有了显著提升,众多本来默默无闻的印人因其赞助提携而名扬海内。周亮工本身对篆刻有着出色地见解,同时自己也能够刻印,故而闽中印人也多前往拜访,在这一交流过程中,福建印人逐渐在明清之际的印坛上崭露头角。福建侯官印人薛居瑄就是通过周亮工的赞助与扬誉而著名。薛居瑄,字宏璧,本晋江人,后迁居侯官,一生落魄不得志,生活堪忧,周亮工记载:
(薛居瑄)间尝过予节松堂,泫然泣下,曰:“瑄老矣。工此技垂四十余年,顾无人一人知瑄者。家贫无从得食,藉以此饱妻孥,日坐开元寺肆中,为不知何氏之人奏技。来者率计字以偿,多则十馀钱,少则三数钱一字,体不少正,尚命刓之,如此垂数十年。不意今得之公。”语毕复泣下,点点沾所镌印上。[清]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印晓峰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周亮工在遇见薛居瑄时,薛居瑄已经年过七十,其名尚不能出乡里。周亮工感其篆刻之精,将其名列《印人传》一书中,经过周亮工的扬誉,薛居瑄声名渐起,影响逐渐超出福建一地。清代初期,福建一地的印人大多数像薛居瑄一样,影响范围有限,正是因为周亮工在闽为官,又将这批福建印人写入《印人传》中,这批印人的生平、艺术才能够流传至今。假设没有周亮工的提携,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福建篆刻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周亮工本人对于发现并提携福建印人十分自得,曾言:“闽人以弘璧之遇予,如会城之江瑶柱得予而显。”“江瑶柱”为周亮工在福建期间不遗余力推崇的海珍,由于周氏的推崇,江瑶柱在其朋友间颇为知名。周亮工也颇为自得的认为薛居瑄的成名与其扬誉密不可分,所以才有上述之说。像周亮工这样通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为印人的声誉的建立起到关键作用的“赞助人”虽然不像直接提供金钱的“赞助人”在赞助活动中直截了当,但是其对篆刻史的影响同样重大。以周亮工为例,其在闽八年,通过他的这种“赞助”,使得清初福建印坛发生了重要转折,众多印人开始出现在世人的视野范围之内,从而直接改变了清初福建篆刻史的发展。
在篆刻史的发展过程中,不论上述哪种赞助方式,对篆刻史的发展路线都起到一定的影响。“赞助人”因素作为“非印学因素”之一,其对篆刻史构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提示我们的研究者,篆刻史的内容远不止机械的将每个印人排列出来、介绍其作品这么简单。作为“非印学因素”之一的“赞助人”角度,对拓展篆刻史的研究范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经济因素对篆刻史研究的意义
经济因素是篆刻创作活动中不可避免的因素之一,而以往的篆刻史研究者对此的关注程度并不高。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极具稳定性,即在传统的四民结构与儒家“志于道”而后“游于艺”的影响下,从事书法篆刻的人大多对金钱的态度比较隐晦,造成在留存至今的史料文献中经济因素的记载并不显著,而篆刻史的研究者也并未强调经济因素对篆刻史的影响。
事实上,在篆刻活动中,经济因素直接参与到篆刻史的发展中。在研究明清流派篆刻史时,我们发现经济因素会对篆刻史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相对繁荣的的篆刻市场;二是篆刻家在面对生计问题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对其身份构成造成影响;三是在经济的诱惑下,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混迹于篆刻圈中,并以此谋生,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为当时印坛带来了低俗的风气。
关于篆刻市场的记载明代末期周应愿在《印说》中曾提到:
今有不识字人刻印,如苏集阊门,杭集朝天门,京师尤盛;上焉者,略看印谱一二册,便自号能篆,印哪得佳?[明]周应愿:《印说》,明万历刻本,常熟市图书馆藏。
明代晚期,苏州的阊门、杭州的朝天门,以及北京都是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又加之这些城市与地区有着相当数量的篆刻受众,所以在这些地区形成初步的篆刻市场是顺理成章的。而在清代初中期,扬州地区因为盐商富贾数量激增,这些富贾为附庸风雅,将大量财力投入到艺术市场,导致扬州地区书画篆刻人才聚集,从而形成了异常繁荣的篆刻市场。从清代初期著名的印人程邃开始,到清代中期的丁敬、邓石如等,无不在扬州展开篆刻活动谋求生计。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丁敬在扬州的篆刻作品市场价格更是高达“白镪十金,为镌一字”。篆刻市场的繁荣必然会带动篆刻家队伍的壮大,并且提升他们的“市场竞争力”,无意中促进了篆刻的传承与繁荣。
篆刻家在面对经济问题时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从而对其身份构成造成直接影响。例如一类篆刻家专门以四处鬻印为生,他们并不排除以篆刻作为谋生手段,这部分人可以称之为“职业的篆刻家”;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类篆刻家则坚决排斥任何方式的金钱与篆刻作品的交换,他们恪守儒家传统的“游艺”心态,将篆刻视为文人之馀事,而非治生之工具,对于这部分篆刻家,我们就不可将其视为“职业篆刻家”;还有一类篆刻家虽然不鬻印,不直接以作品换取金钱,但是却以篆刻作品与他人作相当经济条件的交换。从行为学上来看,篆刻家对于篆刻是否能作为“商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他们身份的划分。
第一类“职业篆刻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何震。何震(1522—1604),字主臣、长卿,号雪渔,徽州婺源人,后长期寓居南京。何震是晚明最负盛名的篆刻家之一,与文彭并称“文何”。明代末年何震通过安徽同乡汪道昆的介绍游艺至塞外,周旋于戚继光及其同僚周边展开鬻印行为,为自己赢得了较好的市场条件,所谓“名重一时,缙绅硕彦,千里走币,珍逾拱璧焉”[明]彭源:《印存跋》,郁重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橐金且满”,塞外之行使得他的经济状况到了很大的改善,成为晚明典型的“职业篆刻家”。
第二类人坚决排斥在篆刻中有任何的经济行为,典型的例子可以以周亮工《印人传》中的大量传主为例,如清初歙县篆刻家郑基相“贫且老,不能以此技(篆刻)奔走显贵之门,向人亦绝口不言……以故贫益甚”,他最后宁可依靠贩卖古玩糊口,也不曾以篆刻博得显贵的垂爱。[清]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第44页。在篆刻活动中,郑基相对金钱所持有的态度决定了他有别于“职业篆刻家”的身份。
第三类篆刻家如安徽印人郑旼,其《拜经斋日记》云:康熙十二年二月“三日,其贞过话,自有篆刻数方未竟,聊遣闲耳。予久欲谢此不为,奈世缘未断,我虽不为,而人又争购我矣……”康熙十二年十月“十日,为采南牙章三方,诣之,其润资许响我以粟二……”黄涌泉:《郑旼〈拜经斋日记〉初探》,《美术研究》1984年第3期,第49页。
像郑旼这样本欲以篆刻“聊遣闲耳”,但是“奈世缘未断,我虽不为,而人又争购我矣”,他的篆刻作品在更多的时候却以生活必需物品如粟米等来作交换。这些对待篆刻过程中经济因素不同态度的篆刻家在构成篆刻史时,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自然也不应该千篇一律。
同样,经济因素也可能在篆刻史发展过程中造成一些弊端。如在明清二代,都存在一些并无多少文化素养的人开始以篆刻谋生,在诱人的经济利益驱使下,造成篆刻作品格调的低俗,一味炫耀无中生有的技巧,形成了一股在篆刻过程中唯利是图的风气,万历末年的邹迪光曾记载:
今之人不能辨古书帖,识周、秦彝鼎,天禄辟邪诸物,则托于印章之好者,亦十而九。好者博名,而习者博糈;好者以耳食,而习者以目论。至使一丁不识之夫,取象玉金珉,信手切割,弃之无用;又使一丁不识之夫椟而藏之,举此无用之物,椟而藏之,袭以锦绣,缠以彩缯,奉为天宝。噫!亦可恨甚矣![明]邹迪光:《金一甫印选序》,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第460页。
这些让人“可恨甚矣”的篆刻从事者,依靠欺人耳目博得金钱,然而一些真正有水平的篆刻家却无法与之相比,如朱继祚《印鼎序》:
今雪渔往矣,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甚至假托钟鼎,借形鱼鸟,以欺掩尘饭土羹之痴儿,其所售偏易就,而精六书者,几不能与之争下驷。[明]朱继祚:《印鼎序》,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第502页。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于在篆刻活动中经济因素的态度也能够对篆刻史造成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周亮工对不同印人的评价,如他对活跃于南京的扬州篆刻家梁袠、梁年二兄弟的评价,就因为他们所涉经济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梁袠其人曾鬻印四方,篆刻活动中的经济追求较为明显,故周亮工对其颇有微词,称其“粟吏贩夫,以及逆党仇正辈,或以金钱,或恃显贵,人人可入镌矣”。与此相反,周亮工对梁袠之弟梁年的“平生不奔走权贵”表现出颇为赞赏的态度。这就导致我们今天评价梁氏二兄弟时,除了他们本身的篆刻成就,还不得不关注他们二人对待经济利益的反应。
篆刻史是一部鲜活的历史,并非仅仅是由一批篆刻家、几部印谱的堆积罗列而成的名单,在研究篆刻史时,像经济因素这样的“非印学因素”始终伴随在篆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四地域与印风
一个地域相对于其他地域来说,在文化形态上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反应在篆刻史中,即是不同地域的篆刻家,在篆刻活动中的行为方式、作品面目等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例如在明代晚期,福建地区出现了众多比较知名的篆刻家,这些篆刻家多分布在侯官、莆田等地,相对较为集中。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为群山所环绕,交通不甚便利,与江浙等篆刻发达地区的交流相对较少,这就能够使得福建地区的篆刻风貌相对江浙等地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根据文献记载,福建地区的篆刻家多为雕刻玉印、水晶、象牙印的能手,这一传统从明代后期一直保持到清代,从众多文献记载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如周亮工《印人传》卷三《书林晋白印谱前》云:“林晋,字晋白,闽莆田人……晋白善镌晶章。”[清]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第55页。又《印人传》卷二《书江皜臣印谱前》云:“独皜臣真能切玉者。”[清]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第36页。又有江皜臣的学生,晋江陶碧也多镌刻玉印。此外,明代末期的杨士修在《印母》中还谈到:“其象牙但可令闽人刻作虫鸟人兽之形,供妇女孺子玩弄耳。”[明]杨士修:《印母》,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第88页。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感受到在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篆刻家在篆刻过程中多偏向于工艺性质。这与福建地区整体的文化氛围相关,首先福建地区不像江苏、浙江两地一样从元代开始就有较为深厚的篆刻传统,其次在经济上也无法和江浙匹敌,自然无法吸引篆刻高手来此展开印学活动,故而福建地区在篆刻发展过程中即显示出其独具特色的风格。
地域对于印章风格的传承与流布具有关键影响。某个地域内部或者相近的地域之间,在印章风格的传承与流布过程中具有先天的优势。苏州一地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即是文人篆刻发生与发展的一个中心点,以苏州为中心,其周边的无锡、常州、南京等地为辐射带一直引导着明代晚期到清代初期江南一带的篆刻风格。在晚明苏州诞生了文人篆刻的先驱文彭,由于地缘条件的便利,文彭印风逐渐扩散流布到其周边地区,以至于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内,江南地区都笼罩在文彭古朴典雅的印风中。苏州作为文彭印风的中心,向四周延伸,其印风的影响逐步递减,最终变得微乎其微。在这一过程中,地缘的远近实际上成为文彭印风传承过程中强弱变化的要素。我们若果不能体察到这一点,盲目的认为在晚明文彭印风的影响范围无所不在,这就有失事实。梳理某个地域或相近的地域之间的印风联系,对于我们还原真实的篆刻史不无益处。
地域对篆刻的影响除了上述两个方面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即地域因素同时还促使新的篆刻家群体的出现。人们历来在研究徽州篆刻史时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徽州篆刻家的流动性,并将这种流动性归结于徽州地区的“地狭人稠”。耕地的缺少致使人们不能按照传统的农耕模式进行劳作,转而促使人们寻求新的谋生技艺,从明代晚期开始,篆刻便成为徽州士人所青睐的谋生手段了。徽州篆刻家有徽商一样走南闯北的行为习惯,他们多前往经济发达的扬州、南京、苏州等地从事篆刻活动,交流与碰撞即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徽州地区本身的局限性促使一个新的篆刻家群体的产生,同时经济发达的江南一带又将这批篆刻家吸引过来,并且成为推动自身内部篆刻发展的一股新力军。地域环境的不同间接影响了徽州篆刻家的活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代晚期徽州篆刻史的发展。
在篆刻史上,不同地区有着不同印风的传承,这不仅仅是具体师生关系下印风的传承,更多的是受到这一地区文化结构的影响。如何对待这种现象,梳理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才是正确认识地域与印风关系的关键。基于此点,我们可以拓展到清代初期山东青州、江苏如皋、浙江杭州等地篆刻史发生与发展的内在脉络。
五社会文艺思想与篆刻的相关性
作为“非印学因素”的社会文艺思想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参与到篆刻史的发展中。从文人篆刻史的萌芽时期元代开始,篆刻的发展即受到社会文艺思想的影响。元代赵孟頫多才多艺,诗书画印无不精通,其成就最大的地方在于绘画与书法。在书画实践中,赵孟頫特别强调“复古”的重要性,如其在绘画中强调“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在书法中也特别强调恢复魏晋二王之古法,赵氏一生不遗余力的身体力行,他的这种努力,直接影响了整个元代书画艺术的发展,使得元代近百年的文艺都向“古”靠拢。赵孟頫在书画实践中的“复古”与“好古”自然渗透到篆刻艺术中。赵孟頫曾撰有《印史》一文,在《印史》中,赵孟頫云:
谂于好古之士,固应当于其心,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乎。[元]赵孟頫:《印史序》,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420页。
赵孟頫“复古”“好古”的文艺思想经由吾邱衍的进一步阐释在元明篆刻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往后发展,到明代,文艺思潮对篆刻的影响更为明显和重要。明清之际的周亮工在《赖古堂印人传》一书《书黄济叔印谱前》中最早直接了当地提出文学思想与篆刻艺术的关系:
间尝谓此道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始可继唐;唐、宋、元无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继汉。[清]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第28页。
周亮工将篆刻艺术同历代诗歌发展的规律比较,认为一定时期篆刻的兴衰同诗文一样,在此文中周亮工又言道“明诗数变,而印章从之”。明代篆刻的发展正如周亮工所言,社会中一种文学思想或理论的产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影响到篆刻。
明代的诗歌在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是以“复古”为主要旗帜的。以李攀龙、何景明、李梦阳、王世贞为代表的文人强调诗歌的拟古主义,如李梦阳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将明代诗歌的复古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这是明代诗歌领域中的第一次显著的变化。与此相对应,在明代的篆刻艺术中也形成了一股“印宗秦汉”的复古主义风气,其代表性事件是上海顾从德于隆庆六年(1572)编辑刊印《集古印谱》。《集古印谱》收录秦汉印章近二千方,成为当时篆刻家最为重要的学习对象。万历三年(1675),顾从德将《集古印谱》摹刻于木板之上,重新定名为《印薮》,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制。随着《印薮》的快速流布,当时的篆刻家无不以《印薮》为师,《印薮》的刊印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篆刻拟古之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稚登曾讲到:“《印薮》未出,而刻者拘今,《印薮》既出,而刻者泥古。”[明]王稚登:《金一甫印谱序》,韩天衡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第459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宗秦汉”的思想笼罩了江南的印坛。
时间降至万历中期,明代诗文中拟古思想逐渐式微,前后七子的影响也逐渐减弱,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人们开始思考拟古主义的弊端。此时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性灵派”逐渐接过拟古、复古的旗帜,主张诗文创作中独抒性灵的重要性。袁宏道在论述袁中道之诗时称其“大都独标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15页。。这是明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第二个显著的变化。“独标性灵,不拘格套”成为万历中期文艺思想的主流,篆刻艺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体而言,即对于万历前期印坛上复古、拟古、摹古思想的批判与反思,尤其是对《印薮》一书的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万历三十年(1602),梁溪印人程远有摹古印谱《古今印则》问世,是书的刊行目的之一即是针对当时印坛拟古、摹古的现象作出调整,张纳陛《古今印则序》有言:
夫汉印存世者,剥蚀之余耳。摹印并其剥蚀,以为汉法,非法也。《薮》存,而印之事集;《薮》行,而印之理亡。[明]张纳陛:《古今印则序》,郁重今编:《历代印谱序跋汇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张纳陛认为正是《印薮》一书的刊行,致使篆刻之理法消亡,其说虽有夸大之嫌,但是足能代表万历中期士人对由《印薮》流行而带来的印坛一味摹古的反感与批判。
受到“独标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的影响,在万历中期至后期,出现了众多敢于变革的篆刻家。福建漳浦的黄枢、黄炳猷父子是这一时期最为激进的篆刻家,黄氏父子精研金石文字学,黄枢有《款识录印谱》行世,以古文字入印,打破了以汉代缪篆入印的传统。以黄枢父子等人为代表的篆刻家在入印文字上的变革,顺应了篆刻艺术的发展规律,突破了万历中期印坛的摹古之风,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周亮工将黄枢父子在篆刻中的变革与这一时期的诗文相比较,称其为印坛的“公安派”。周亮工论印一直主张创新与变化,反对墨守成规,在《印人传》卷一《书黄济叔印谱前》一文中,周亮工用了大量笔墨站在篆刻艺术发展的角度,讨论篆刻发展过程中的变革,最后总结道“明诗数变,而印章从之”,周亮工讲到:
文三桥(文彭)力能追古,然未脱宋、元之习;何主臣(何震)力能自振,终未免太涉之拟议。世共谓三桥之启主臣,如陈涉之启汉高,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尽俯首敛迹,不敢毫有异同,勿论势有不能,恐亦数见不鲜。故漳海黄子环、沈鹤生出,以《款识录》矫之,刘渔仲、程穆倩复合《款识录》、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欲以推到一世。虽时为之欤,亦势有不能不然者。三桥、主臣历下,子环、鹤生其公安欤?渔仲、穆倩实竟陵矣!明诗数变,而印章从之。[清]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第28页。
在明清二代,篆刻家的身份多为文人士大夫,这样的身份特征能够更容易使他们的篆刻理念受到当时文艺思想的影响。文艺思想虽然不是篆刻史的研究范畴,但其在篆刻发展过程中稳定而持久的影响,却不能不引起注意。文艺思想作为“非印学因素”之一的原因,除了它对篆刻理念的发展起到引导作用,还因为篆刻理论本身即作为文人篆刻家文艺思想的一部分。梳理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清晰认识篆刻家的印学理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是如此,我们的篆刻史研究自然无法绕开这一环节。
六“非印学因素”在篆刻史研究中的可行性与潜在危险
篆刻艺术是由实用的印章逐渐转化而来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众多因素都参与到其中。例如战国玺印中文字的不统一性是由于各国使用汉字的随意性造成的,而汉字的随意性又是由于各国的政治军事等原因造成的,那么在研究战国玺印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通过这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字等层面来深入地看待战国玺印的多样性。同样,隋唐官印文字的盘曲处理是在印章制度与钤印方式的转化下逐渐演变的。秦汉时期的印章多为作封缄之用,印章直接在泥土之上钤盖,形成封泥,用作凭信的工具。到隋唐时期,印章逐步由在泥土之上钤盖转变到直接蘸取朱砂在纸张上钤印,印章的这一使用方式的转变,促使了印章由阴文向阳文的转变。纸张的广泛使用又是这一转变的促成条件,政府主导的印章制度的变革也影响了这一转变。由此而观之,从秦汉到隋唐印章的变革是受到制度、造纸科技等因素的影响。这也提示我们,系统研究印章制度、熟悉科技发展史等“非印学因素”对于篆刻史研究的重要性。此外,元代篆刻发展中出现的“印宗秦汉”与“复古主义”与这时的书法风气关系密切,提示我们书法思潮的变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篆刻史的发展,事实上,不仅仅是书法思潮,其他文艺理论都会对篆刻理论的构建与篆刻史的发展产生影响。晚清的“印外求印”说同样也是与诸多“非印学因素”相关,“印外求印”所涉及的文字来源、风格形成等梳理都为我们以“非印学因素”研究篆刻史开拓了范围。
受西方艺术理论及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绘画、书法的研究已经开始出现转向,从社会学、心态学、接受学等方面入手的研究已经逐渐兴起,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而篆刻史的研究范围却还是依旧围绕大家名作展开。“非印学因素”的提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
当然,过度夸大“非印学因素”对篆刻史的影响,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危险。首先是在篆刻史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视角的太过多元化容易造成研究内容的过度分化,造成对篆刻史本身的漠视;其次,“非印学因素”只是参与了篆刻史的发展,对于“非印学因素”的过分强调可能会造成篆刻史研究范围的支离破碎。
“非印学因素”的提出并非要求篆刻史研究者急切的套用西方各种文艺理念来研究篆刻史,而是能够在研究篆刻史时采用一种多元叙事方式、开阔的研究视野以及丰富的研究角度。方旭红、张清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发展中的“生活化”开发》,《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8-44页。篆刻史的研究目的一方面是梳理篆刻的发生与发展史,同时也是我们当代篆刻艺术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车之鉴,“非印学因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结语
篆刻史并非大家与名作的历史,篆刻史的研究范围也不仅仅是大家与名作简单的排列。什么样的篆刻史才是完整的篆刻史?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重构完整而真实的篆刻史,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努力没有用,当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具体的刀法、字法、章法等层面的分析时,完整的篆刻却离我们越来越远。“非印学因素”是深入篆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提示我们,在构建相对完整的篆刻史时,社会史中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波及到我们篆刻史的范围。如何摆脱固有的研究视角,拓展篆刻史的研究内容,这也许是今后篆刻史研究者不得不关注的内容。
“Non-printing Factors” and the Seal Cutting History Research Scope
ZHAO Yang,WU Dong-feng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seal is not only to study the seal cutting works words,knife,composition “seal”,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al cutting art history is not only motivated by the inheritance of “printing factors” ofWhen constructing a complete and true history of seal require,we are supposed to pay attention to “non-printing factors”“Non-printing factors” refer to other elements except the ontology content of the seal cutting art,such as economic factors,patrons participation,geographical factors,and thought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process of carving activities“Non-printing factors” changes will tend to change the history of seal writing pattern,narrative style and research contents,etc
Key words:“non-printing factors”;seal cutting history;seal cutting art;research scope
【责任编辑程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