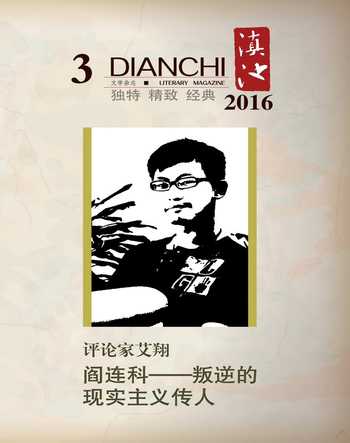花朵并不总与芬芳有关
蒋在 霍俊明
霍俊明:蒋在你好!知道你是一个 90后诗人,实际上关于给你做这次专辑我也是犹豫了许久。因为,我尽管阅读过一些 90后诗人的本文,也写过极其零碎的观感,但是我并没有对你们这一代更年轻的诗人有自己明确的观感和整体印象。而诗歌不仅是少数人终生的事业,而且诗歌天然是属于年轻人的。当我阅读完你诗歌的时候,我决定来完成这次对话的工作。由年轻的诗人,我想到的是诗歌的理想主义。可惜,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并没有在太多的更年轻的写作者这里看到这种所谓的理想主义甚至是情怀。是的,花朵并不总是与芬芳和好梦有关。
蒋在:谢谢霍老师。您说到花朵,我就想用一朵花来描述沙。事物的错位、逆向或反面,存在与对立,是诗歌语言的图景。将事物追踪到一个精神向面,是一个诗人应该完成的关于诗歌的内在构造,以此形成诗歌的脈络与质感。我喜欢事物不同的性状,物象情态间微小的距离,它是陌生又是贴近且错落的。这样的错综复杂,在任何一个角度,它的棱面都能发出光来,它有声音不绝于耳,有颜色或明丽或晦暗。诗歌的形状也承载着诗人与事物的形状、距离和精神的显现。在《花束献给死亡》这首诗里,我突然这样写道:“以不能描述的方式 /在沙漠和荒野中种了一朵花 /用来代表沙”,我说“突然”,我想是因为诗歌语言不是可以预设的,它的到来妙不可言。这就好比一种相遇,词语也好,事物也好,人也好,都需要恰当的相遇。那是一种隐秘的不期而遇,等待或寻找,都会使我们更快地接近相遇的瞬间。
霍俊明:接下来,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吧!被诗歌选中总是有特殊的原因的,说说为什么你最初选择了写诗?
蒋在:一首 80年代的老歌《小草》,竟然是我从倾听中感知到这个世界生命区分的最早启蒙。或者是从此我“被”发现了我的不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无法说清四岁的我,是否从中意识到了我与小草相似的卑微命运,从而感同身受地充满了悲伤、忧愁,却有了一个类似于哲学问题的悲悯思考:“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它却还要活着。”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在这个寻找的时间里,心与物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我无法明白的映射。我似乎懂得了一些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生长的不易。上小学五年级时,我开始手捧圣经诵读,最早是出于孤立的虚荣。我无法证明自身的坚实与不同,无法真正地从孤立的自我中找到存在着的强大理由,或者叫做战胜“同学们”和“老师们”的理由。从装模做样到每天完成课业之后必盘腿诵读,我完成了从中获取力量和慰藉的过程。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写诗。我 11岁开始写诗,是因为绝望。那是一个孩童看不到希望,类似于黑暗的绝望。幼年时我被长期寄放在姥姥家,像是一个物品颠簸了它存放的时空和位置,坠落或碎裂,即使落满灰尘,那也是别人家的灰尘,不属于自身。这样的感受一直到上小学三年级。“仿佛走到了尽头”,我告诉母亲这是绝望。写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诗。按照心中晦暗的形状,将感知的世界和事物描绘成形。那年我 11岁,母亲面对我的诗避讳用诗人两字,(也许她怕我把自己当做诗人,将所有未驯化的想象扭转成现实)但她却从不避讳对诗的陈述。
霍俊明:是的。诗歌就是将外在的事物放大或缩小最后内化为生命和语言的过程。由此,在你这里,诗歌写作的过程所呈现的是你和世界外物怎样的一种观察、体验和再造性的关系呢?
蒋在:大学里不分学科的广泛学习,打开了我对事物的理解和注视,生物界的一切现象令人惊异不已。一只水上飞舞的细小的蜻蜓,将尾翼扎入水中精准地扎破植物的茎皮,然后产卵繁殖生衍;一株生长在夹缝中的藤蔓,尽可能地将自己撑在空中,等待着与它相遇的风,然后倏然间缠住一棵树,接下来的时间是绕树而长,一直长到参天大树那么高;一株沙漠之花的种子经过远途跋涉,在陌生而遥远的沙地,偶遇水源扎根,开出茁壮而更加艳丽的花来。世间万物奇妙的瞬间,给了我们无尽而相似的生命期待。我喜欢在这些不可抵挡的相遇里的等待和寻找,然后将一切埋进事物内部。在沉静中慢慢靠近,这是我们在纷乱中获得与事物微妙距离的方式。是事物的姿态,同时也是我选择的姿态。在这样的距离里,时间变成孤独的个体,在静默中慢慢为我张开。一些人和一些事物变得触手可及。我在屋子里点上蜡烛,或者走进树林,光脚踩在苔藓上;将两只大蒜栽进杯子,看它们抽芽、生长,是我与这个世界孤立地相处和探寻,获得自我注视获得母语的方式。所有存在着的事物,都变成幻想。我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如此之近,因为寂静。把自己放到寂静里,或者将寂静放入内心,交错成诗境的道路。同样是寂静,却完全的不同。住在姥姥家的日子是寂静的,那种寂静让我害怕和恐惧,是外部的寂静被动的寂静。我时常爬到阳台上透过花盆往下看,盼望着有人走过、有人说话,漫长的午后,我总是在期待一种声音中寻找时间流逝的热闹。有时候,下面走过的只是一个人,他不会发出声音。我就从花盆里拣一块小土石扔下去,猫下身子躲在花盆后面,怀着恐惧和兴奋等待别人的吼叫声消磨掉寂静漫长的时间。内部的寂静是主动的,来自于需要。而外部的寂静则是被动的,让人心生畏惧。不过,喧嚣却是毁坏诗歌本质的利器。
霍俊明:像你这个阶段,写诗的过程中诗歌阅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你的阅读视野和写作练习中你如何认识诗歌的品质?
蒋在:好作品透出的气息,除了忧伤,还有优雅;除了直指人心的诉说,还有高贵和担当。
一个人与隐秘的世界建立了联系,她必然从中获得重生和救赎。在宇宙秘密路径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密码,通向那个广阔浩渺的瞬间。这是诗歌给予事物和诗人的生命光芒。诗人将视线投放在事物的速度流经的轨迹,与诗歌内在的联结的方式与搭建上。从一个物象到达另一个物象,再到达精神的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也许就是诗歌到达的时间。
人类,和其他的生物群种相仿,所有的生物殊途同归地为其寻找一种精准切合空间与时间的方式。诗歌更是如此。而我想在以后漫长的诗歌写作里,会不断地探寻那个准确的切口,力图寻求到精准无误地将事物剖析开的角度和切面。我们靠近世界与自然的速度,更接近了时间和事物的内部。所有事物在时间的轮廓下移动,呈现它的隐蔽纷呈的肌理组织。鸟的飞行,树叶的飘落,植物的闭合,都逃不掉自身速度的限定。诗歌的语言在多重速度的限定里,自我张合。
霍俊明:你一再提到的就是“寂静”这个词。这可能在精神内里上暗合了女性写作的某种本源性。而寂静是直接与时间性的生命体验以及回溯性的愿望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会说诗歌本质上就是“生命诗学”。
蒋在:“诗起源于沉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如同幻象显现或掩藏。伊斯坦布尔就是那个“沉静中的回忆”。写作《伊斯坦布尔》时,我还没有去伊斯坦布尔,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到伊斯坦布尔,更别说以怎样的方式去。现在我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旅店的阁楼里,与伊斯坦布尔如此亲近。伊斯坦布尔每天每时的神祷不绝于耳,日升日落时的圣钟响彻天空,都是关于生命每一次的重生的神圣启示。柏拉图说创造、发现就是回忆。那么“美景之美,在于忧伤”。诗歌里的忧伤相似于一个人的呼吸。“女人和鸽子/你睁开眼睛 /替他们 /睁开 /伊斯坦布尔的眼睛”《伊斯坦布尔》。这是“回忆”中的孤独与绝望,每个城市伤痕的流亡状态,都会聚拢在消散的时间里,供我们回忆与注视、等待和流逝。这是一次与时间、记忆有关的人类文明的流亡状态,不是个人的时间状态。而最终我们只能向神祈祷——回到迈锡尼文明最后阶段遥远的铜器时代,那个布满游吟诗人的街道,那个对神、对仪式、对海洋,对爱和离别仍存在念想和悲痛的年代。或许我只能选择“无论是哪一种审判 /我终身带着虔诚的荆冠 /无论是哪一种桎梏 /我叩首默许 /选择跪下”《与神对话》。这是我们获取通往的秘密所在,将自我放置在自我镜像之外,透过镜面的光上升或坠落。
霍俊明:诗歌最终呈现的必然是“语言事实”。而这一特殊的事实对我们一再强调的想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你怎么看到“语言现实”、“想象力”与“实有现实”之间的关系?
蒋在:“我从她的身体里看到一棵树”(《荷兰有风车》),16岁我写下这样的诗句时,同样没有去过荷兰。荷兰的风车被我隐藏在“乌黑的时间”、“鹅卵石”、“海鸥”、“雏菊”、“没有唱歌的船长”里面。去到荷兰时,我发现真实的荷兰同样充满了诗意,一个安静未知的荷兰与想象中的荷兰,无限回复到一个广阔的世界,本身就是诗歌。现实的荷兰即诗,或者诗亦即现实的世界。当我站在荷兰的街道上,荷兰和诗歌一起再次回到想象中,自由地将自己以及时间投向更远更幽秘的去处。从孤绝的缝隙里看到物质世界瞬息流转的光影,我想应该是诗人寻找的“诗从一个意象中渐渐诞生”的方式。一个永远的他乡异客深情的眼睛,满怀忧愁和哀伤。用精准清晰的方式准确无误地剖开事物的切口,在终极宇宙中找到齿轮切合的那一刻,我们就用人类的无尽丈量了自己,这是宇宙给予我们永恒的诗歌世界。
霍俊明:而诗歌在某一特殊的时期对应于不同阶段的写作者来说,其承担的功能和效用并不同。对于你这样一个年纪的写作者而言,诗歌可能更多承担了一种“梦想”。
蒋在:诗人抵达梦境时的瞬间显现,是梦境之中醒着的音色与孤独,给予了诗人独一无二的永恒的光辉和与之对视的可能,以及无法克制的冲动与绝望,以此成为宇宙、世界、人类的梦呓,而真正的诗人将注定深陷其中。诗人是往来于天地间的独语者,用心灵与宇宙建立关联的创造者,一座废弃的城市、一场战争、海湾、雕塑、歌者、人群、爱、离别,当这一切驻足在诗歌与世隔绝的想象里,一个更加广阔的宇宙世界正悄然来临时,诗歌会穿过所有的秘密,变得柔软可信。诗歌所包藏的终极意义,才能无限地为我们展开。一颗高到天上,低到尘埃里去的心,是属于诗人的。体察万物同心而注,让细小的纹理凸显其充盈明亮,让每一次相遇都有温情和体温,都“准许 /我们在黑夜里许下一个愿望:/准许永远饱含深情 /采下世界上所有的花朵”《夜晚用哀求挖了一个洞》,然后邂逅远道而来的一切。将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搁浅在昨日未知的岸滩,潮汛带来的或带走的每一粒细沙,都将会成为诗人心里醒着的梦境。
霍俊明:我发现无论是安静、恐惧还是梦想都同时出现在你的诗歌中。我一直发现你用诗歌来面对“未知”世界的努力与探询。甚至,与你年龄不太相应的是你用诗歌过早地处理了“死亡”的黑暗主题。
蒋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不论是过去或是将来,要做的不外乎是,等待时间无止息地流转过程中那个永恒的瞬间以及光的到来。即使在我们的记忆里,城邦的建立是文明的起始。
其实人类和自然之间失去的维系,才是属于全人类来自远古,最古老最初始共同的孤独。这个孤独即是文明的萌芽。它既属于诗歌,也属于诗人的世界。“不久成千上万的马匹 /将来到草原 /而我们却一次也不会知道(《夜晚用哀求挖了一个洞》)。是的,我们不会知道,一次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手握密码的永远是那个离开的人。“出门或进门 /都铺满了密码 /只有你 /我的姥姥 /你能打开”,“带着密码出门 /惊扰和催生的 /还有埋下的 /都是这一世的秘密”(《带着密码出门》)。一些事情的到来、降临,都是未可知的。扎进心里,如同刺扎进不可名状的物体,生长,盘绕,落地,或开花或结果,以不可预想的方式到来又离去。第一次发表诗歌是 2008年的冬天,我的姥爷去世了。谢挺叔到殡仪馆来时,他拿了两本刚刚出来的《山花》。我跪在姥爷的灵柩前,流着泪认真读了我的诗,那是我第一次读我的诗给他听。我笃信那夜姥爷静静地听了我的诵读。那年我 14岁。那一年,死亡的气息无处不在,像空气一样布满每一个角落。每天清晨,我都会在镜面上写下:很庆幸我今天还活着。在雾气缭绕中注视自己,以此来慰藉活着的偶然与侥幸。2008年,从那个可怕的 5月到12月,我的奶奶走了,接着是我的姥爷,再到2009年 4月,我的姥姥也走了。那是个多么漫长的黑暗的时间黑暗的记忆。我的愧疚、绝望与他们的死亡,构成同一个黑暗的幻象。在我的世界里,毁灭成了瞬间的事。他们的离去,给我的生命记忆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窟窿。一个我试图不断修补的窟窿,正在消耗成时间的窟窿。
霍俊明:似乎,女性天然地与植物和自然发生著奇妙的化合作用,尤其是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更是如此。这似乎又回到了我们谈话的开始部分。
蒋在:给予事物向上生长的空间,用等待完成所有的时间,以及一切物象的关联。我曾经一度对生于北美洲的一种草本植物——捕蝇草,感到莫名的兴趣。有人将它形容为女神维纳斯的睫毛,它卷曲柔美。我更喜欢将它称之为万物之神宙斯的手掌。生死刑场,一些生物逃不过命运。捕蝇草的“手掌”里面有六根刺,相互对应的排列在手掌两边,当任何昆虫触碰到它的时候,会促发它的闭合,在这样精准的位置上所发生的一切成为了必然。误入其中的昆虫大多都难逃一死。换一句话说,那一棵刺的位置是永恒不变的,在时间匀速规律的更替中,所有的生命体仿佛已经找到了,并步入时间的高速运转中,在逐渐成形的规律里,将空间凝固成永恒的法则。但在锋利背后,还隐藏着一种韧性,囊括着美和柔弱。花开一季。他们的花茎越过宙斯的手掌,内外明澈,净无瑕秽,恣意开放。准许所有的昆虫的前来。所有的事物都到达了:“在花团簇拥的苦寒地面 /伸出一枝来”(《我取下无指手套》)。捕蝇草靠近世界的形态,对于我们来说,那宙斯的手掌,手心里是人类历史,而手背外面的世界,含有的花朵,是人类的情感。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我们对陌生、遥远的事物感知的能力,有一种人类基本共通的感情在里面,这就是人类的智慧组成。除此之外,就是世界与自然靠近生命本体的速度,而我们可以做的唯有等待。
这是诗意的,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我们在时间里无休止地等待,那个切合时间的速度切合世界切合诗人的速度的到来。光照给予我们洞悉事物的同时也令万物显现和隐藏。它点燃一切,燃烧一切,之后一切终将重回初始的状态。
霍俊明: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希望诗歌带给你的欢乐要多于苦痛。
蒋在:谢谢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