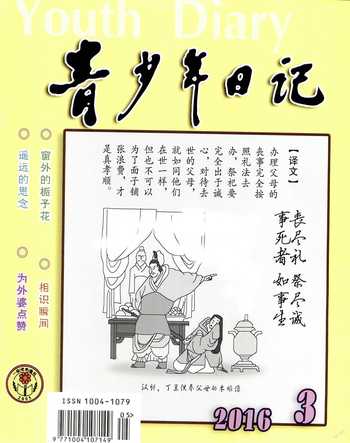不俗之客
王兢以
1月29日 晴
不知从何时起,学校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生命体。
时常会看到它欢脱地奔来跑去的样子。起初是吃惊,这不期而至的生命是何时出现的?其次是习惯,今天又见到那个欢快的生命了。现在是每天渴望见到它,希望看它于是从它身边经过或者是看着它穿过每个人的身边。它时常会找一地儿温顺地躺下晒太阳,悠悠然的样子却带着一种憨憨的味道,它仿佛并不惧人,当然我们也不总躲着它,一切仿佛那样自然,好像它本身就是我们学校的一部分。
初来学校时,它伤痕累累,瘸着一条腿,可依旧整天拖着那条残腿满校园乱逛。学生之间开始流传着种种关于它如何受伤的流言,甚至会渐渐演变成都市怪谈,无论是否真实,可当时每次看见它身上的伤痕,我似乎觉得那却在向我们证明着一切对它们这些流浪群体的不重视和残忍。有同学或老师心生怜悯,时常会俯下身子摸摸它的头,它也不躲,就顺势趴下来,眼睛眯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而当你停止手中的动作时,它会用它的眼睛看着你,眼眸清澈,似初生的婴儿,颤动着它的长睫毛,犹如一把小扇子,加上它的伤,更觉得楚楚可怜了。如此温顺如羊的生命,怎么会有人忍心去伤害它呢?
于是,同学们和老师们不知不觉自发开始了一个互不知道的接力。女同学们超乎年龄的母爱泛滥,去小超市买新鲜的牛奶;男同胞们一点也不在乎它的性别,当成同类地会偷渡自己在食堂打包的肉骨头给它加加餐;老师们也闲不住,某老师带头带着它去了宠物医院,治好了它的伤,给它打了疫苗。一切都仿佛宣称着,从此开始,这个生命体就是我们新中的一份子了。
现在,它做母亲了,诞下了三个新的生命。都是黑中带白,白中夹黑,这讨喜的肤色和它们的母亲简直如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小家伙们十分招人爱,不仅学生,就连老师们也纷纷赶来想要见一见那三团挤在一起的肉球。都说,像它这样的生命,一旦做了母亲,对自己初生的孩子是偏执似得照顾有加,旁人多站一会儿都不行,更别说是围观了。可它却不同,对于我们的造访它不但不会不舒服,还显得非常欢迎,没有半点遮拦。可若是校外陌生人靠近,它必狂吠不止,我也曾听见它的叫声从教学楼东面荡到西面,又从西面折回来,来来回回数次,我们的心也跟着急促的跳动起来,后来我们想,原来它那是把我们当成家人了,它已习惯在我们学校--它的家中间那些身穿红黑校服的身影,于是我们似乎就是它的亲人,所以亲朋前来祝贺它的喜悦,它欣然接受。
它和我们人类一样,做母亲的,总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它亦然。小家伙们养得十分壮硕,不过似乎有点过头了,它们既没继承母亲修长的腿,也没保持母亲那般良好的身材,短小的四肢仿佛永远无法撑起它们圆滚滚的肚子,这使它们稍走几步就会打个滚,我很喜欢观察它们走几步然后在地上打滚的样子,总是和朋友一起边看边捂嘴笑,那样子真的别提有多可爱了!
后来三只被领养走了两只,突然变成"独生子"的那唯一的小家伙就更受它的保护了。某次大概是小家伙与同学们玩着离它们的家——教学楼旁的灌木丛稍远了些,它便急匆匆的奔过来想将小家伙叼回窝里去,然而由于它的溺爱,那小家伙的体重早已超出它的预算,它根本无法将它叼回去,最后还是小家伙自己连滚带爬的躲进了灌木丛,它才安心地又在一旁躺下了。
慵懒的午后,慵懒的阳光,午后结束的铃声叫醒了我们,也打搅了它的美梦,它趴在一楼班级的前门,那儿恰巧还有些残留的温度,它以它惯用的方式伸了个懒腰,摇摇尾巴,带着惺忪的步伐换了个阳光更好的位置,蜷缩成团,鼻子紧贴着蓬松的尾巴,它的孩子也靠在它的身上安详地睡着。它大概是忘了亦或是原谅了曾经伤害过它的人,那样从容的睡在了路中央,享受无比宁静的午后。
竟开始羡慕起这条狗的时光了。
浙江省新昌中学越新文学社
指导老师:何文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