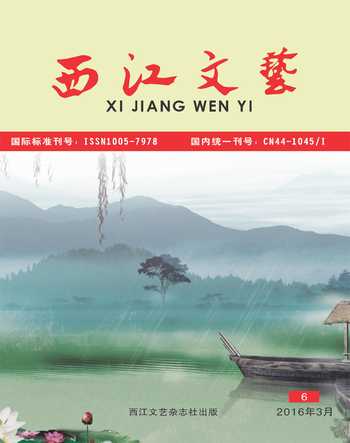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
杜庆萌
【摘要】:中国古代哲学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作者通过分析几位日本近代文化精英,如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涩泽荣一、夏目漱石、汤川秀树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吸收与改造,认为经过他们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哲學中的某些思想对日本近代的哲学、经济、文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了日本近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作者指出,探讨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育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哲学;日本;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在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文化有何积极影响呢?学术界对此探讨甚少。依据史料,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一问题,对于认识由东西文化融合而成的日本近代文化,对于扬弃中国古代哲学,探索东方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均大有裨益。本文将以几位对日本近代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日本哲学家、企业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为例,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由于属同一学科,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哲学的影响是直接而又显著的。西周、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三人的哲学思想就颇具典型意义。
西周(1829一1897)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的主要历史贡献是,将西方哲学(从哲学概论、哲学史到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而在译介的过程中,西周始终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西周6岁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2岁进藩学“养老馆”,接受严格的汉学训练,遍读《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近思录》等重要典籍,20岁左右先后入大阪的松阴塾、冈山的冈山学校学习中国古代经典。1862年至1865年西周在荷兰三年留学期间系统地钻研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学习了西方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西方的思想文化开阔了他的视野,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然而,西周在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并未抛弃以前所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知识,而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媒介,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文化,融东西两种哲学为一体。西周认为,“东土谓之儒,西洋谓之斐卤苏比(”哲学“之日语音译——引者注),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
在知识论上,西周提倡“大知”即知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反对“小知”即知识的零碎性和片面性。他说:“小知即平常的知识,在有限程度上高于凡庸者,如同某人立于稠众密群之中,看之视野不超过前后左右。”“大知与此相反,如立于一高台之上观台下稠众,对于数万人可以一目了然,视野不受前后左右所限,行动亦得当。”根据西周的《知说》篇所述,他的“大知”是以“文、数、史、地”为基本内容,以演绎和归纳为主要方法,以求得真理为最终目的。很明显,西周的知识论是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系的,但西周所述的“大知”、“小知”概念及某些思想乃是取目庄子哲学。庄子曾曰:“小知不及大知”“大知观于远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其中的联系显而易见。
西周把当时的新兴学科——心理学介绍给日本人民,其中借用了蕴涵着丰富哲学思想的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法。西周指出,“心理之分解首别三大部,智、情、意是也。”“意,是人心之主,即为心诚之君主,而智为采纳之官(又曰报告官),情为宣达之官,采纳之官司入,宣达之官司出,共居心诚,辅相心君,以开其属府于此身国”这种“智、情、意”的心理学理论虽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新知识,但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思维方法与《黄帝内经》的医学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西周认真地翻译了一批西方近代哲学范畴,他的翻译不是生硬地直译,而是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创译。如“哲学”范畴,英文原词为“philosphy”,意为“爱智”。西周先参照中国宋代哲学思想,将“philosphy”译成汉文“性理学”、“理学”、“穷理学”。随着对西方近代哲学认识的加深,西周觉以上译语均不太妥,便作了进一步改动。他说:“斐卤苏比(philosoPhy)之意如周茂树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故亦可将斐卤苏比直译希贤学。”后来他又将“斐卤苏比”译为“希哲学”,这大概是受中国《尚书·皋陶谟》中的“知人则哲,能官人”思想的启示。经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他在1874年刊行的《百一新论》中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斐卤苏比译名哲学。”这样与英文原意的“爱智”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哲学”一词是经过仔细斟酌才创译出来的,而西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素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西周在创译“理性”、“悟性”、“主观”、“客观”、“现象”、“实在”等哲学范畴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营养。这些哲学范畴今天仍在日本、中国等使用汉字的亚洲国家中频繁使用,为沟通东西哲学的交流,促进东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创建日本近代哲学的过程,中江兆民比西周更进了一步。中江兆民(1847——1901)是日本明治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的自由民权理论家。他16岁时入著名的土佐藩藩校文武馆学习汉学,专心习读《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尤其爱读《庄子》。据其周围的人说,兆民能把其中的某些章节倒背如流。随后,他还在奥官慥斋门下读过《传习录》,研习阳明学,兆民于1871年10月至1874年5月赴法国留学。归国后,他在大力介绍西方哲学文化的同时,仍拜著名汉学家冈松瓮谷为师,努力学习先秦诸子。他在建设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哲学的营养。如他对生死观问题的回答就具有鲜明的东方特点。1901年4月医生诊断兆民所患病症为喉头癌,并说只能再活一年半左右。听到这个消息,他不是悲观、消极地等待死亡,而是乐观、积极地工作。他说:“假如有事情可做,并且过得愉快,那么,这一年半岂不是足以充分利用的?啊!所谓一年半也是无,五十年,一百年也是无。也就是说,我是虚无海上一虚舟。”庄子在《大宗师篇》中说:“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庄子认为,人的生命之初是自然所赋予的,最终仍要回到大自然,因而人的生命实际上是以无为始,又以无为终。显然,兆民的上述思想是对庄子“死生存亡之一体”观点的继承和改造。兆民还说,“一个人假使七八十岁后才死,可以说是长寿。然而以后,却是永远无限的劫数。假使以七八十年去和无限作比较,那是多么短促啊!于是乎不能不把彭祖看作夭折。”可以看出,这是对《庄子·齐物论》中寿与夭观点的改造。正因为兆民能站在无神论的基础上,吸收和改造庄子生死观的思想,所以他能以顽强的意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为日本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中江兆民还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民本论”思想与卢梭的民权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东方的自由民权论。他曾写下“民为重”的汉字横幅,这与孟子的“民为贵”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天下者,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柳宗元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既非天意决定,也非圣人的意志所能左右,决定的因素是“生人之意”,即人民的意愿和物质需求,并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观点。中江兆民通过西方近代的自由民权论对孟、柳的观点作了新的阐发,指出:“民权是个至理;自由平等是个大义。违反了这些理义的人,终究不能不受到这些理义的惩罚。即使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也终究不能消灭这些理义。帝王虽说是尊贵的,只有尊重这些理义,才能因此而保持他们的尊贵。中国早已有孟柯和柳宗元看透了这个道理。这并不是欧美专有的”当时日本政治思想界中有一种论调,说“自由”、“民权”、“平等”等思想产生于西方,不适用于日本的近代化。中江兆民为了反驳上述论调,激励日本的自由民权主义者与封建主义势力和思想作斗争,所以重新诠释了孟子等人的“民为贵”思想,提出‘民权”、“自由”思想“不是欧美专有的”,使日本的“自由民权论”更具东方文化的特色更富号召力。中江兆民还用孟子的“浩然之气”观点为其自由观作了论证。他在《东洋自由新闻》的社论中,把自由分为“行为的自由”和“心思的自由”。所谓行为的自由,包括人身、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从政等方面的自由。所谓心灵的自由,“就是我精神心思绝不受其它物之束缚,充分发达而无余地。这也就是古人所谓‘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
日本近代的文学也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这里以夏目漱石(1867——1916)为例。夏目漱石被日本学界称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巨匠”。他少时喜欢汉学,曾进入以中国古代经史为主要教材的二松学舍学习。上大学英文专业时,他继续表现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浓厚兴趣,写有《老子的哲学》一文。1907年,他进入《朝日新闻》报社,成为专业作家。日本学者认为:“漱石的思想可以说是在欧洲的近代思想与东方思想的接触过程中形成的。”从漱石的创作来看,他所接触的“东方思想”除了日本思想之外,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化。
漱石的文学作品融进了不少中国古代哲学成分。他在《七草集评》之诗中写到:“洗尽尘怀忘我物,只看窗外古松郁,乾坤深夜闻无声,默坐空房如古佛。”在《失题》之诗中写到:“往来暂逍遥,出处唯随缘。”在《春兴》之诗中写到:“寸心何窈窕,缥缈忘是非,三十我欲老,韶光犹依依,逍遥随物化,悠然对芬菲。”这里的“忘我物”、“忘是非”、“逍遥”、“物化”均是庄子《齐物论》和《逍遥游》的思想。另外,他的文学作品《我是猫》、《薤露行》、《趣味的遗传》和学术著作《文学论》等多次引用庄子的文辞、典故。他在《题自画》之诗中写到:“起卧乾坤一草亭,眼中唯有回山青,闲来放鹤长松下,又上虚堂读《易经》。”在《无题》之诗中写到:“眼识东西字,心抱古今优,廿年愧昏浊,而立才回头,静坐观复剥,虚怀役刚柔。”可以看出,漱石读过《周易》并接受了《周易》思想的影响。由于融进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成分,漱石的文学作品增加了思想深度和启迪意义,表现出较强的东方色彩。
以儒学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古代思想是日本近代“和魂”中的重要部分。自王仁于公元285年携《论语》入日本起,经过一千多年日本历代学者的吸收、消化,尤其是随着儒学在江户时代(1603——1867)的兴盛和普及,中国古代哲学的某些思想已深深积淀在日本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之中,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日本学者认为,“明治以后的‘和魂,则将过去的‘汉才亦包括在内,形成一广泛圈的概念。”在这具有复杂成分的近代“和魂”体系中,与属于宗教思想的神道、佛教和崇拜古典、信奉神话的“国学”相比,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有其特有的长处,即它一方面是注重现实、关心社会、“积极入世”之学,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内容上涉及自然观、方法论、伦理观、社会观等领域,因而它对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影响颇大,成了日本近代文化的东方理论来源。
本文所列舉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态度并非简单地套用,而是基于日本近代化的社会实践,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们在吸收与改造中国古代哲学以运用于日本近代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进行文化建设,如何使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姝.伊藤仁斋“仁学”思想研究[D].武汉大学2014
[2] 易礼军.日本西周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研究[D].延边大学2013
[3] 陈锦彬.从日本儒学管窥日本文化特质[J].林区教学.2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