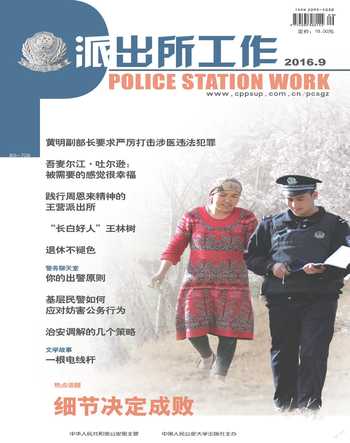那年我是片儿警
任继兵
1976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石景山分局古城派出所担任外勤民警,那时又叫片儿警,一干就是六年,既平凡又幸福,既光荣又快乐。那时,片儿里的老大妈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任儿”。与她们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亲亲热热,你你我我,警民关系十分融洽。我下片儿到谁家坐一坐、聊一聊都要喝杯茶,你不喝,老大妈们就不高兴,真像走門儿串亲戚,工作做了,警民关系也搞好了。“与群众打成一片,做群众的贴心人”,这是一个片儿警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安机关好传统的具体体现。记得1979年,我办过一个案子,那种民警与群众鱼水深情的感人画面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979年的秋天,我当片儿警的第三年。老爷子搬家,所领导放我两天假,忙活了一天,第二天上午睡了个懒觉,11点多到了派出所。车还没停稳,满脸胡渣的常所长便老远冲我吆喝起来:“我说任儿啊,回头抽空下去一趟,你片儿里出了档案子。”“什么时候?”我问道。“今天上午。片儿里的老太太们紧忙活,上个月发的一起案子刚破,这可是第二起了,人家指不定怎么着急呢!”常所有些急眼。我没等他把话说完,忙推着自行车冲出了院门。
发案的居民区离派出所有三站多地。这里原来大部分是农村生产队,工人和居民不多,那几年附近的大厂子变着法地占地,大部分农民转了工人,农民户口也跟着转成了居民。出租房屋在这儿并不违法,一些外地人和本市两地分居的职工或新近结婚的小两口由于没有固定住房,都能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合理出租或租用。房东金大爷和3个儿子都有工作,金大妈守着个大院子料理家务。大儿媳是外地人没有北京户口,在家替别人织毛活儿什么的。
院门没锁,我推着自行车进了大院。金大妈耳朵好使,打开北屋的房门便操着挺熟的哑嗓冲我打招呼。“任儿,来了,这两天忙什么去了,老没瞧见你。”“没忙什么,这不老爷子刚搬家嘛。”我支上车,边说着,边随金大妈进了屋。“家搬好了?”金大妈边说边关切地顺手递过来沏好的茶。“还没利索呢,听着您的大嗓门,这不赶快瞧您来了嘛。”“这孩子,总捡你大妈爱听的说,可你不知道,大妈都快急疯了。”
我正要掏笔记本,却想起出门着急,笔记本忘在黑提包里了。金大妈拉开抽屉,把一只红杆圆珠笔和几张信纸递给我。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是甜的。“大妈您以后沏茶别再放糖了。我,我不大喜欢喝甜的。”“蒙大妈不是,大小伙子喝点甜茶水也犯忌?”
我按照办案的程序,仔细询问了金大妈和她的儿媳妇。
上午,金大妈在前院自己的屋里缝被子,听见“咣当”一声响,出去不见人影,只发现过道上有一辆自行车和大儿子骑的“28”车差不多。她没在意。回屋后听见后院有快步走路的声音,后来又听见推车的声响。顺着玻璃看见一个穿深色衣服的小伙子骑自行车出了院门。她记得当时屋里的挂钟响了10下。
金大妈的儿媳是上午9点20多从家里出去买菜的,当时才买不久的上海牌手表放在闹钟的盒子上面,走时没有锁门。10点半买菜回来,发现手表不见了,急忙告诉了婆婆。她哭着找了20多分钟,仍不见手表的踪影,只好到派出所报案。
我反复琢磨着,金大妈听见过道有人支自行车,和那个穿深色衣服的小伙会不会是一个人?盗窃手表的人会不会就是他?他在过道支起自行车干什么?是车子坏了修车?还是……我跟金大妈说了几句,让她儿媳也到前院去。我将一枚5分的硬币放在闹钟的盒子上面。
我从院外骑自行车,院门开着,直接骑到后院。见两个房门锁着,最里面的门没有上锁。我推开门,没有人,又将门关上。然后骑车离去。到了过道停住,将自行车支起。这一段可以叫现场演绎吧,“文章也许就在这儿。”我边琢磨着边蹲下身子,停车的地方看不出有修过车的痕迹比如漏下的油或来回挪动的足迹等。我起身快步走到最里面的屋子,从屋里拿走5分钱的硬币。骑上车出了院门。
重新回到金大妈的屋子。“干什么呢?”大妈不解地问。“您听到刚才支自行车和我到后院走路的声音了吗?”我提醒着。“嗯,听见了,挺像先前的那个声音,只是那人走路好像比你快。”随后,从金大妈儿媳的嘴里还了解到前些日子搬走的那户和那对夫妻的情况。
唯一的线索就在那个穿深色衣服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身上。经过调查,证实他和已经搬走的那户租房的人在一个单位。半年前曾因为在汽车上扒窃,被公安机关拘留。金大妈家发案时他没上班,据说他骑的是一辆“28”男车。
在另一个派出所管片儿民警的协助下,我见到了他。他的年龄比我大,却叫我大哥,谈了一会儿,他就坐不住了,让我给他一次机会。他说:当时本来是去找人,不知道人家已经搬家,看门锁着就去最里面的那户,只见房门没锁又没有人,就走了。可到了过道,猛然想起闹钟上的那块手表,白白留在那儿太“可惜”了,想着,他支起了车子又快步返回拿走了手表。
案子破了,有一天金大妈拿着一包糖、一盒礼花牌香烟带着儿媳到派出所要感谢我。我实在不好推掉只好先收下。送走了金大妈,把东西交给了所长。几天后,我下管界,给金大妈家一个新的房客上临时户口,其间,金大妈绷着脸半天不和我说话。后来我才知道,所长已经亲自将那包糖和烟退还给金大妈。我几乎已不抽烟,这时不得不将那盒礼花烟打开抽出一支,“大妈,火呢?” “在这儿。”此时,金大妈的嘴角才似乎有些松弛,她麻利地把那包糖打开,用黑黄的双手剥开一块酒心巧克力糖递给我。我把糖接过来送到嘴里,又吸了一口香烟,深情地凝视着面前的这张面孔,感受着一个普通民警仅仅为群众办了一件应该办的事而得到的那份深切、真挚和信任的报答……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一直忘不掉,总想讲给年轻的民警听,让他们听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听我们公安机关的好传统,也就是听党的优良传统。今天,无论社会发展多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多大,公安工作的任务多繁重,我们都不能把公安机关的好传统丢掉,不能把党的优良传统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