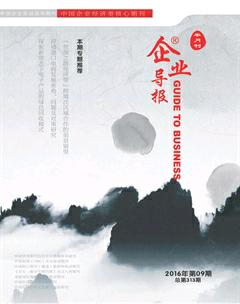当前我国农村生活面向及其治理探究
杨小华++余冲++刘净媛++唐小毛++游麒林

摘 要:本文以齐云山村和花车村两个不同生活面向的典型村落的田野调查为中心,在村落中的新房建设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出村民返乡频率的比较来分析村民生活基础和生存价值的取向差异,从而判别村落的不同生活面向,并以此探究农村治理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农村居民;生活面向;农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贺雪峰认为生活面向是指村民建立自己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时的面向[1],而这种个体的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上升到一个集体层面便是学界所热议的共同体和集体意识。在传统社会,尤其在农村地区,在稳定和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的面向具有高度的内向性,有着稳定而明确的共同体及集体意识。改革开放之后,由打工潮和升学热为两大引擎的牵引,农村居民流动不断加快,在生活面向方面从单一稳定的内向型分离出外向型的生活面向,此类个体对共同体和集体意识趋于淡薄甚至无视。而不同面向不仅决定了个体的生活轨迹,也主宰了农村地域性的整体兴衰。
二、不同生活面向的差异表达
本文在对不同生活面向的差异化研究中选取的是江西两个不同村落在住房建设和外出村民返家频率两方面的信息进行对比来表达生活面向的差异,具体如下:
(一)住房建设。经村干部和部分村民的叙述及访员的实地走访观察,可以明确的看出两村在居民住房建设上存在较大差异。两村现存的住房项目部分调查参数如表一所示:
根据上表数据计算可知,花车村和齐云山村在村中旧住房的比例为59%:93% ,新住房的比列为40.8%:0.07%。进一步的调研发现,齐云山村已知在外购置住房的已达35户之多,另一方面齐云山村自2000年后新建的住房仅有15幢,而且其装修十分简单,建房原因主要为原有住房存在安全隐患,又无力在外购房,是不得以的经济理性人选择。综合以上几点,齐云山村的外向型生活面向即十分明了。而花车村现有住房中户均住房大于一幢,即该村存在一户人家在村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但是村中并不存在现成住房的市场交易,即使是紧张的宅基地也无市场交易,在用地调整上仅限于换地。在花车村的农户中,亦有部分经济优厚的家庭在城镇购置了商品房,但是其在村中有固定独立住房。因此,花车村的内向性明显。
“建房热”作为一个热词在学界备受关注,但是其在不同生活面向的村落中却是有“热”亦有“冷”的。农民在市场生活中会尽可能做出理性的选择,当其生活面向为外向型时,在村落中建房自然也就热不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外迁,村中已有的房屋也年久失修,在村落的整体性上,便免不了村民只顾自身的发展而漠视村庄的整体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整体的利益,最终村庄走向衰落的结局。相反,在其内向型的生活面向基调下,住房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自然不容小觑,即使面临宅基地愈来愈紧张和建房装修成本越来越高等诸多困难,也难以阻止其建房的热情。在此种村落中,不管是人心还是物质的“膨胀”都将是必然的,村民都会尽量可能在村庄之内攫取资源为增益自身利益,也必将或多或少的漠视村庄共同体的利益以及发展。因此,不管是内向性村庄还是外向性村庄,当前,都是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为自身做打算,村庄共同体的意识都相对淡漠。
(二)外出村民返乡的频率。打工潮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大背景,在这当中,调研的两个村落中的情况基本类似,即村落中的青壮年绝大部分都是外出务工来谋生,而这外出大军的回家频率却在调查的两个村落存在差异,如表二所示:
春节作为中国最受尊重的传统节日,被国人所普遍重视。村民在日期间追求团聚通常要不远万里赶回家中。经调查,花车村中的外出村民(就业或就学为主)在春节几乎全部会返回村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花车村有着“拜团年”的规矩,即不论亲疏,同一村落的农户家按年长为大的原则相互登门道贺。而在其它时段除了有婚丧嫁娶等重大事件发生,否则村民回家的情况两村普遍较少,但是除了春节之外的其它节假日,清明节村民返乡祭祖也可作为一个考察的标准。在花车村清明节返乡祭祖是一种自我身份的声明,即使那少部分在城镇有了固定住房的发达人家,这两个节日返乡的频率也非常之高。在齐云山村的走访过程中发现,近五年来村中外出农民返乡的频率却出现了下滑和不稳定的趋势。外出村民过年返乡还是主流的,其目的却多为老人在家中带着子女,返乡垫付相关的教育等费用以及扮演父母的角色。第二代农民工的乡土观念更为淡薄,村中已经有数十位80、90后的打工仔连续三四年未回家,对家人的解释是“回家太费钱、回家没什么意思”之类的“理性考虑”。在其它时段返乡的农民是极少的,偶有返乡的多为在外失意、难以立足而不得不返乡。对清明节,村民也极少返乡。在这生活面向外的基调下,村民都在各自忙着怎么跳出这个村庄,怎么甩掉脚上的泥巴,怎么扎根城市。
农民工返乡不仅是一个交通上的表象,更是一个社会学上的互动表现形式。对于内向性的村庄来说,因为家乡的绝大部分人依然愿意回到故土,返乡也就意味着加强自身与传统关系的联系,以便于自身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利用上家乡传统的资源,返乡就有了现实的意义。而对于外向性的村庄来说,因为家乡的土地已经荒芜,家乡的人也渐渐的远离故土,回去就不在有加强原来传统关系的意义,在外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能指望可以获得家乡的强有力的支持,所以,从理性上来考虑,返乡的兴趣以及频率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三、不同生活面向下的治理探究
农民作为一个市场交换中的经济人的角色,在日益密切和复杂的社会互动中,越来越理性化是一个必然和应然的趋势,固守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和集体意识已然有诸多弊病,从单一的生活面向分化出内向和外向型两个不同的生活面向是农村居民适应社会生存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同时也助力于其进一步的理性生活。内向型生活面向中,这些变化既有村落文化的复兴、亦有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既有慷慨义捐造福乡里的善举,亦有拜金主义和虚荣攀比的歪风邪气;外向型生活面向中,既有农民的人走茶凉、亦有资本盘活农业生产,既有农村传统文化的凋零、亦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理性崛起。因而对不同生活面向的出现在对农村治理决策中更多的应该将其当作一个社会属性的参照,而非当作问题本身去主观的矫正,这是真正促力农村发展决策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在农村问题的治理中,政治和市场作为左膀右臂的外在两股力量参与其中,对这两者的合理利用,必然给农村面貌以皆大欢喜的改观。
(一)政治的作用。在肯定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给予资源的支持和法制的监督,不失为明智之举。在对花车村的走访调查中,2015年年初,塘下全队代表会上,村干部阐述了政府有相关的农村发展建设资金扶持,现可以申请建设村中的道路水泥路改造,但是需要村民配套集资才够钱。在水泥路改造上,明显存在较多分歧,但是多次会议协商,各自妥协下,年底水泥路的改造工程已经竣工,兑现了水泥路到家门口的承诺,也达到了全额给付工程款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花车村这样内向型生活面向为主导的村落,建立在基本价值观上的认同是解决问题关键,村干部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在具体利益商榷上不做表态,只在分歧较大时不断重申诸如“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儿,只讲和,不讲散”的大义。政治牵头,让农民自己组织,自己耕耘,村民的价值理性必然会让问题得到理性思考和解决。
(二)市场的补充。在经济和物质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中,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当作农村治理的第一要义,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过程中,农民更好的参与市场、市场恰当的开发农村不失为一条光明正途。在吴言林和程丽丽的《市场发育、农民经济理性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提出,农民经济理性行为并不是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其经济理性是受诸多条件的影响的,农民向来被社会定义以朴素无为的形象,但是农民也是求生存的最前线成员,不得不承认,农民在参与市场过程中也很快获得了自己的经济理性。因而,市场对农村治理是一个无限的契机,在农村高度嵌入市场下,城乡才有其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有必要强调市场和资本的进入应得到监督制衡。在走访调查过程中,齐云山村的山林成为村民本地的创收核心,经历过挖光、砍光、烧光的恶性开发后,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加之林业部门的监管,形成了现在以毛竹这一再生能力极强的经济林业为核心的“轮耕”式经济开发体系,这其中,根本上是村民自身经济理性化的提升,也少不了外力监督制衡的努力。回归整个市场经济中,农民会在外出务工和本土劳工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在文学上造就了返乡体中的无奈,但是其在社会学上却是充满着农民自己的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的。
四、结语
通过对两个不同村落在住房建设和外出农民返乡的两方面情况的对比中我们得出农村个体农民在生活面向上已然形成了内向和外向两种不同类型,而村落中个体的生活面向最后也决定了村落整体的生活面向趋势。不同生活面向不是单一的村落共同体和集体意识的兴衰,而是农村居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过程中的自身价值和经济理性的整体表达。在将不同生活面向作为背景参照而非问题本身的前提下,笔者在政治力量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分析了在农村治理中的这两者应有的理性参与。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页.
[2] 卢成仁.流动中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一个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5第1期。
[3]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第43页。
[4] 毛丹.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J].社会学研究,2010第1期。
[5] 赵春晓.对农村“建房热”现象的思考———以嵊州市为个案[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第6期。
[6]林晓珊.一项关于农村青年流动人口返乡过节状况的调查——以闽中山区兴山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5期。
[7] 于建嵘.农会组织与建设新农村——基于台湾经验的政策建议[J].中国农村观察,2006第2期。
[8] 吴言林,程丽丽.市场发育、农民经济理性与农村经济发展[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