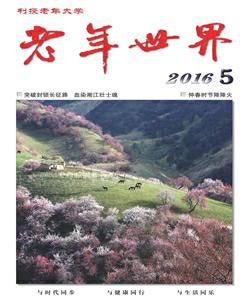老井
遥望一个个饱经风霜的古村落,便能联想到润泽这些村落的一口口老井的故事;伫立于一口口老井侧畔,同样能透视出一个个古村落的沉浮。古村落中的老井,从历史的深处摇摇晃晃地走来。
山塬的一条季节河两岸,点缀着六十多户人家,袅袅的炊烟和披头散发的老榆树勾勒出乡村的风姿,一口老井坐落在南岸沟沿上——这便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我曾问过爷爷老井的岁数,爷爷说他也问过他的爷爷,无果。难道这口井老得忘了自己的年龄?
井筒不算深,两丈有余,井壁用规整的石头砌成。趴在井口向内望,石头的缝隙处长满苔藓,冷气习习。对着里边喊一句,立即听到同声频的应和,仿佛来自地府幽灵的对答。通常,井水有一半的深度,所以无需装辘轳,绳子的一头系只小桶打水就极为方便。井口用四块大石围砌:两块长条的东西横跨,两块窄条的对头配卡在长石的间隔处,合抱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口”字。也不知当初是从哪里采来的这四块石头,长条的一块羊肝紫一块斑斓黄,窄条的也是一块羊肝紫一块斑斓黄。这四块石头,经漫长鞋底和井绳的摩挲,呈现出玻璃般的光泽,棱角极其圆滑。内测竖面上,井绳拉下深浅不一的槽痕,一道挨着一道,深的超过两根手指的厚度,使人既想看又想摸,耐人寻味——这,大概就是老井的年龄吧!
井台上有两个硕大的石槽,老乡管它们叫井槽,凿刻比较简陋。长方形的一个外部有凿痕,中间挖空,底侧开一个不足鸡蛋粗的孔洞,槽里的水弄脏的时候便可从孔洞放掉。圆形的一个外部几乎没有凿痕,能清楚地辨认出自然石头的瘤状体,只在上面掏凿了一个正方形空间,底侧也有一道漏水的孔洞。它们主要是用来饮牲口的,槽底中间都有一个光滑的椭圆形浅坑,那是水槽中水不多的时候,牛马驴骡用嘴唇嘬吮磨就的。
记忆中的早晨或黄昏,前来取水和饮畜的络绎不绝,人们一边汲水,一边唠着闲话,有问候、有赞赏、有鼓励、有调侃……爽快的说笑碰撞在木桶与井口石上,折射出乡民宽敞的胸怀。偶尔也有窃窃的私语,那是邻里的旧事或新闻在彼此心河里的流淌。
井台,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男女恋人约会的地方。他们总能瞅准无人或少人的空当儿,以洗衣或取水为由,光明正大地相见。坐在光溜溜的井口石上,眉来眼去,细语莺声,用眼神勾着对方的魂……其细节与内容,只有老井知道。
1969年农历六月,故乡一带遭受了一场千年不遇的暴雨,像捅漏了天河一样倾泻了整整一夜。山洪如同发怒的狮子,毁坏了不少建筑,也漫过井台淤积了老井。事后村民搭起架子装置了吊轮,一筐筐挖出井里的泥石,借此也淘出了井底多年的沉积物。其中有一支步枪的残骸,老人们回忆是日伪军在井上饮马时掉进去的。井台上那两个石槽不知了去向,人们在下游河道找了许久都杳无音信,成了全村人永远的牵挂。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故乡,从那以后,井水一天没一天精神。到90年代,老井底部的泉眼仿佛一位耄耋老人的泪流,少得可怜。人们昼夜守候在旁边等,有的干脆无礼貌地下到井里舀……
弥留之际的老井失却了昔日的威严,也推托了曾经的责任。乡民只好打旱井筑水窖,储存天上水开创新的生计。
在辽旷的西北大地上,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无数老井奄奄一息甚至枯竭或废弃。曾经的老井,静谧深幽,丰盈充沛,人们一弯腰即可掬一抔洗涤心灵的浪漫。世间有无数的老井,也有无数老井的故事,和故乡的老井一样深深钤印在一方儿女记忆的底版上,难以抹去。
时间是搓揉岁月的大手,人类总是在一次次挑战自然的恶劣与残暴中发展与成熟的。现代城市人压根儿就没有见过老井,自来水的普及,理所当然要淘汰老井,取代几千年来挑水的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