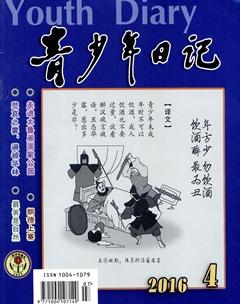压岁钱
若荷
知道“压岁钱”三个字的意思时,我已经六七岁了,刚懂得一角钱的用处和一分钱的份量,会把一块糖的钱攒起来,攒到能买一个演草本,然后拿着它到书店里去左顾右盼一番。
有一年,母亲领我去她的一位好友家,女主人是位很和蔼的阿姨,因为是新年,阿姨就给我五角钱当压岁钱,母亲好像觉得她也应该给,就又每人给了我们几毛钱,算是补的压岁钱,从此延续了下来。有了压岁钱,我就不用向母亲要那几角钱买杂用,而是把压岁钱存起来,细水长流地用来买纸笔。
通常这时除夕已过,初一早晨刚刚来临,窗外阳光明媚,家里家外的气氛又一派祥和,全家人早早起床,大人小孩换上新装,看着面带微笑的父母,一种美好的预示出现了,这就是马上就有一份压岁钱,仿佛那些钱,从母亲那亲切的笑容里走出,即将钻进每个孩子的挎包。从最初的五角,到后来十块八块不等。
那时候,我家住在公社机关大院里,爷爷奶奶在外地,家里的长辈只有父母亲,所以拜年的方式简单些。我曾见过农村家庭的孩子拜年的情景。有一次去同学家拜年,见她家堂屋里安了张八仙桌,桌面和桌子周围已扫除一新,椅子上还搭了两块带背的坐垫,等老人们在太师椅上坐好,一家人在地上站齐全,拜年的仪式开始了。
事先教好的吉祥话说完,一个个头叩过去,老人们才从怀里掏出备好的压岁钱,根据孩子年龄的大小,有的三毛,有的两毛,收到压岁钱的孩子高兴地在房间里跳跃。等家里拜完年,还要到前后左右的邻居家,到本家同族亲戚家拜年,家里又有些积蓄的人家,还要给本枝近亲的晚辈压岁钱,所以大年初一的孩子,都愿意逢人磕头,特别是见了长辈们。不仅压岁钱,几块糖,一本散发墨香的小人书,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孩子们的最爱。我小时候的压岁钱就是这么得来的。
压岁钱,是每个孩子都向往的事,时间离年还很远,压岁钱就成了大人与孩子交谈的话题。父母们在这时往往要约法三章,比如要求孩子们好好配合大人做家务,年底学习成绩要考好等等。故而年假前的半个月,孩子们的表现都不错。不过大人说时是一脸的严肃,说过之后就忘了,大年初一的压岁钱还是一分不少,平等对待,不分厚薄。只是热爱劳动的孩子值得表扬,考不好的孩子得用劳动去弥补,这样的教育,不乏父母的智慧。
就是由于生活窘困,拿不出压岁钱的家庭,父母也不会让孩子失望,他们总会想法子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一份童年快乐的记忆。比如我的同学三妮家,父母就从不给压岁钱,只给孩子买上一串“花喜团”,五分钱一串,用一根棍挑着,挂在每个人的床头上,“花喜团”——它的寓意就十分深远。
“花喜团”是用炒好的糯米做成的,用炒热的糖黏在一起捏成团,捏成燕子状,染上红花绿叶,画上燕子的翅膀,点上燕子的眼睛,团子和燕子间隔穿成串,悬在高处,又能吃,又好玩。汪曾祺曾在《炒米和焦屑》中写过这物件,他说他们家乡称这种吃食叫“炒米糖”,加热加糖后发黏,一块块切成长方形。也有搓成圆球的,叫“欢喜团”。“欢”和“花”的音相近,或许是方言口音的误差。
据说,古时有一种妖叫作“祟”,每年大年三十就偷着跑出来摸孩子,被“祟”摸过的孩子会生病,厉害的甚至能把人变成傻子。大人们就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放在孩子的枕边,等“祟”再来时,这些铜钱就会迸发出一道闪亮的光把“祟”吓跑,后来就演化成了压岁钱。至清代,又带上了去邪祈福的成分,《燕京岁时记·压岁钱》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
小时候盼过年,除压岁钱作为一年到尾的奖励,父母还给我们买小人书,买女孩子喜欢的头花,像纱一样的布,染成五颜六色,经过剪裁加工出来的绢花。进了腊月门,集市上卖绢花的到处是。有人把一块布挂在沿集的墙上,再把各种绢花插在布上,就像一张彩色的挂毯,五颜六色,春意盎然,煞是好看。
那时的年集上有年画,纸花,绢花,有年糕,有糖葫芦,有烟花爆竹,唯一没有看见有人卖鲜花,一切鲜活的东西,都用手工艺品替代了。
一声声祝福,一杯杯佳酿,一幅幅春联,构成了年的主旋律,组成中国人红火而又热闹的节日。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一路成长,不知撒下多少阳光欢笑,而如今的孩子们,尽管收到的压岁钱百元千元,但是与我们的童年相比,似乎并不比那时更加欣喜。早上醒来,在那熟悉的桌角上,一摞厚厚的红包中,新岁的祝福依然殷切,毫无二致,倒是多了些虚荣和攀比。
无论你多么平庸,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有多少财富,大家在新年里都会彼此祝愿,对生活寄予美好的祈愿,愿长辈们健康长寿,孩子们平平安安,做工作的顺顺利利,无论失落还是悲伤,都让生活从新开始,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年之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