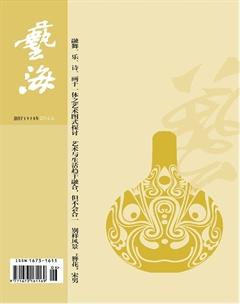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谈《红楼梦》文本的动态性
薛莹
〔摘要〕《红楼梦》发展的历史,即是读者对文本接受、阅读与反应的过程,是一场审美经验的历程。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不断的赋予和重塑着红楼文本的生命力。在红学日益成为显学的历史条件下,回归文本,从文本出发解读红楼显得非常重要。
〔关键词〕文本接受美学动态性
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曾经说过“最伟大的诗人不是创作得最多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这句话用来形容曹雪芹最恰当不过的了,终其一生,“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谁解其中味呢?概莫不过是后世这些品、评红楼的粉丝们的追捧。换句话说,是红楼的接受者,通过读者对红楼的接受、反应、阅读,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赋予和重塑红楼文本的生命力上功不可没。正是在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审美感知和审美经验,使《红楼梦》成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活力、经久不衰的显示出其强大艺术生命力的文本。
姚斯在1972年《审美经验一辩》中说,“根据接受美学理论,艺术作品的本质建立在其历史性上,即建立在它与大众不断对话所产生的效果上;艺术学与社会的关系只能在解释学的问答逻辑的辩证关系中加以把握;艺术史唯独涉及传统和理解接受间的视野变化”。此美学原理应用在《红楼梦》,一方面肯定了接受者在红楼文本发展中的作用显著,一方面也昭示了红楼文本的动态性。小说作为一种时间艺术,本身就具有随着阅读而展开画面、丰富画面的动态性。而红楼文本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超越一般小说的发展的共性规律,展示了它动态发展的特殊性。
一、刻意留白
顾名思义,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是中国画的一种布局与智慧。画如果过满过实,在构图上就失去了灵动与飘逸,显得死气沉沉;而有了留白,便给予观赏者以遐想和发挥的空间。我们观齐白石的虾,才能感受到水的清澈与灵动;赏徐悲鸿的马,才能体味到风的速度。最难忘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一幅画中,一只叶舟,一渔翁垂钓,整幅画中没有一丝水,而让人感到烟波浩渺,满幅皆水。予人以想象之余地。如此以无胜有的留白艺术,正所谓“此处无物胜有物”。文学上的留白便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文学意象所传达的经验,多半是表象的相互暗示、错综交织,具有不可限定性,意义含混,内容丰富。巧妙地运用“留白”这一艺术技巧,可以给读者留下丰富的解读空间。芹溪先生无疑是灵活运用留白艺术的大家,意义空白没有使红楼梦失色,反而使文本更显玄妙。红楼梦的叙事中有多处断层和空白,甚至是疑点。比如秦可卿何以会第五回就死去?死因为何?宝钗进京待选秀女,后事如何?第57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薛姨妈答应向老祖宗提宝黛亲事,却没有后文;贾政为何喜欢赵姨娘?贾琏何以会被称为琏二爷?《红楼梦》中的空白远远不止这些,而这些空白也为众读者所津津乐道与解读揣测。作者把疑问留给了读者,在文本和接受者之间形成了审美主客体互动的关系。作者同时也将答案交给了读者,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读者的解答都是合理的,都是依据特定的审美经验而获得的。留白所带来的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角度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是红楼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红楼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解读史,它是显示了红楼文本的动态性。在王国维那里,《红楼梦》是一部解脱的书,宣扬解脱之道;而索引派认为《红楼梦》是具有极强政治性的映射小说;认为《红楼梦》是自传小说的也大有人在。
《红楼梦》是动态文本,同时也是抒情性、意向性的诗性的文本,仿佛置身流连忘返的园林之中,“如过小桥,如循曲径,流连间不觉风光已殊。但一回首,刚才的一山一水犹在望中,始知作家笔质精工,落墨甚远”。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的园林艺术“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合而为一,在这里形容《红楼梦》文本的动态性,非常形象。
二、文本的对话性
文本的对话性,主要体现在《红楼梦》话题的多重性上。你可以认为《红楼梦》是关于争取思想自主与爱情自由的言情小说;也可以认为它是写家族兴衰荣辱的社会小说;还可以认为它是为群芳立传的传记小说,等等。作为开放结构的小说,《红楼梦》写爱情,不是单一的,它不仅写宝黛的纯情、悲情;还有贾芸与小红,藕官与芳官等缺憾性的爱情;家族命运的兴衰,群芳的去留?宝玉的执于情还是绝于情?美与丑?善与恶?宝钗是美的还是丑的,是善的还是恶?王熙凤的手段与目的是冲突的还是和谐的?这里没有道德宣判,却提供了道德影响。对话性还体现在红楼梦的叙事方式上,作者以一个鲜活的话语主体身份出现,其语言重心、色彩都侧重于展示主体的自我感受,而不是力求使它退隐到客观现象深处,消融较大的语境中。《红楼梦》采用作者助言,这源于作者不加掩饰的自我抒情角色,这个角色可以幻化为其他形态,但是其“作者原型”还是比较明显。《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以作者自云的方式开篇,接着以说书人的立场讲述,使读者仿佛身临现场,与作者一起见证一场家族兴衰的历史,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场繁华即逝的梦境。在此过程中,读者的参与性非常强,《红楼梦》留给读者的问题太多,要理解这些问题,关键还是要以文本为依托,深入理解文本的过程,就是与文本对话的过程。
《红楼梦》的文本是对话性的,通过与文本的对话,读者深化着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的认识。这种对话是开放性的,不是结论性的。文本的对话性,体现着文本的互动与律动性。
三、心理接受的动态性
还是引用姚斯的观点。他认为,一部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这充分说明读者的阅读接受在完整和丰富作品文本上的重要性。所以作为文本组成部分的接受者,心理接受的动态性也要视为文本的动态性。
《红楼梦》以神话开篇,故事情节贯穿于仙界与凡界,前世与今生,阅读者需跟随作者一起上天入地,穿越古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在有情与无情之间挣扎;礼教与诗社之间取舍;在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间恸哭;这些对立性因素构成一个似动结构,造成艺术接受心理明显的动态性。
王国维曾言“览过《红楼梦》之后,念其珠围翠绕者,钝根也;览过《红楼梦》之后,念其色即是空者,解脱者也”。这句话把红楼梦的阅读者一分为二,也可以视为对红楼阅读感受的境界说。一开始阅读红楼,大部分读者会被红楼梦的美人、美景、美食、美好的情感以及叹为观止的园林艺术所吸引,以至于和作者一起沉醉其中,及至“呼啦啦大厦倾”时,才如梦初醒,然而梦醒远远没有梦中令人愉悦。就我本人而言,览过红楼数遍,依然对49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念念不忘,其诗情与雪景,梅香与群芳荟萃时的团圆和谐之美,使此回成为120回中最光彩夺目的一章。依王国维此言,沉迷于红楼温柔乡的,不知多少人会成为“钝根”。而且阅读红楼梦,往往不可避免的走上道德评判的路子,钗黛孰优孰劣?王熙凤是好人坏人?秦可卿人品如何?随着阅读和阅历的增长,依专业所长,从美学角度解读红楼是水到渠成的。虽未必成为领略“色即是空”的解脱者,对红楼的认识却在不断地深化。在关照文本的基础上,跳出文本,再沉迷于红楼温柔乡的同时,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此来讲,读者的心理接受是不断成长变化的。
艺术在超越生活的欲求上关照人生,对《红楼梦》的解读要在尊重文本客观性的基础上,从更高更契合文本层面上来欣赏,避免顾此失彼的道德评判。这也是读者心理接受的正常发展轨迹。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代表,四大名著之首,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自成书的400年来,一直炙手可热,由于版本居多,欣赏角度和立场的不同,分别派生出文学批评派、索隐派、自传派等数派。由研究此书的思想文化、作者原意等,而形成红学。红学发展的历史,是读者对文本接受、阅读与反应的过程,是一场审美经验的历程。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不断的赋予和重塑着红楼文本的生命力。在红学日益成为显学的历史条件下,回归文本,从文本出发解读《红楼梦》显得非常重要。接受美学为我们从文本出发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法论指导。在尊重文本客观性的基础上,从更高更契合文本层面上来欣赏。(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红楼梦校注》曹雪芹、高鹗原著,其庸等校注。1984年4月出版
[2]《红楼梦美学阐释》孙伟科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3]《红楼梦评论》王国维著
[4]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