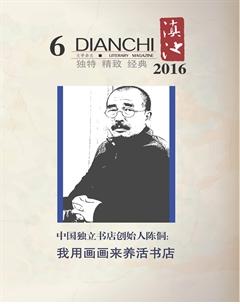仿佛来自另一个尘世
霍俊明
“你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尘世”。这是我近期以来阅读杜绿绿诗歌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或者如诗人自己所说“恰如今日的彼岸”。甚至这个声音一直在身畔内心萦绕——它切近而遥远,真实而虚幻,来自现世又通向了另一个为未可知的尘世——“你认出我的面目了吗? /我自然说不清你的样子,/你的声音 /‘仿佛是来自另一个尘世。”(《我们谈话吧》)
杜绿绿的诗歌写作时间并不算长,到现在也就是十年的光景,而且期间还有过数次中断。在此可以说,杜绿绿的诗歌写作才刚刚开始。她通过《近似》《冒险岛》《她没遇见棕色的马》三部诗集不断在完成诗歌中的“自我”。杜绿绿算是女性写作中安静的一脉。这种写作最大的优势是能尽最大可能地面向诗人自我和个体精神生活。实际上这对于诗歌自身而言已经足够了,因为对于吊诡的当代女性诗歌写作而言,曾一度担当了更多的社会学、身体学、精神症候和文化学的意义,而恰恰是丧失了女性诗歌美学自身的建构。
说句无关痛痒的话。安徽是盛产诗人的地方,可是优异的女性诗人在这个空间却成了稀有之物。这可能也不是问题,因为自来女性写作都不是整个诗歌生态的主体。那是十年前的一个雨夜,山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正和一群人在山中赶路,在雨中搭建帐篷。也许就是从这个湿漉漉的时刻开始,杜绿绿的诗歌曾一度在自己设置的精神性的小镇、山地、树林、路上、岸边、湖水、暴雨中不断湿漉漉的折返。这些地形构成了属于杜绿绿的精神性的空间,而围绕四周的往往是沉沉的暗夜。就如她早期诗歌中不断出现的“小镇”一样,这既是日常的又是陌生的。生活本身是这样的,“我哪里都没有去 /我只是不分昼夜地躺在这张暗红色的大床上”;而梦想却是这样的,“晨光照在我的骑手服上。/我们比闪电更快,/冲过松林,向更远的地方去了。”停滞与冲动该如何通过语言来平衡?由此,关键是诗人该如何找到那条并不存在的进入到诗意完美未知境地的小径?静默如谜的未知亦如神的呼吸。这是徒劳,但是也不得不一次次寻找。这既是一种寻找,是自我精神暂时安放之所,也是一次次的精神出离——“前面的路已隐入更深的草丛”“这条小路,荒草抹去它的方向。”甚至可以说,诗歌在偶然间作为精神生活对位性产物的出现恰好弥合和补充了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白日梦般的愿景。在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在现实场景和虚幻的戏剧性氛围中,杜绿绿不自觉地将自己设定或想象成了有时让人捉摸不定的女性主体性形象。有时候这一形象就站在室内或厨房的一角,有时候又像哆啦 A梦一样吹着硕大的气球往天上飘——“我多想闭上所有的眼睛,继续做个孩子”。杜绿绿有一首诗《热气球女士之死》与此精神向度是同构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她又敢于戳破那个热气球一样的幻梦。她可以和儿子大碗做游戏、出游,也可以在实有和想象性的大海、山林之中寻找那丝微而隐匿的光线。杜绿绿在广州的住宅与常年葱郁的大山尽在咫尺,相互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和呼吸。每一个窗口望出去都是群山——“我熟悉这些景色 /胜过了解自己的身体。//我望着它们 /度过每一日”。但是,住所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不是简单的物理距离,而是心理距离。这更明显地通过诗歌等方式确认。深夜或清晨诗人能够听到山鸟啁啾,这是侧耳倾听,也是对自我灵魂潮汐的观照——“可我现在成了臃肿的妇人,/屋后的山坡也难以爬上。/我只能在夜里偶尔想起那些鸟儿 /它们应该洁白,/像雪,像干净的眼睛。”“应该”一词显现出多么滞重难行的一面!(《鸟鸣》)这使我想起沃伦的那首诗人尽知的句子:“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有的人已谢世 /而我站在远方,那么静,我终于肯定 /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在此,诗歌既是向内挖掘,又是向外敞开;既是日常所感,又是精神生活使然。由此,诗人必须平衡好日常(平行或向下)与精神维度(别处或向上)之间的平衡。正如沃伦那句诗,多么自然日常,多么平静无奇,可是却一次次敲响或撞击着人世的我们,“头上的天空和木桶里的天空一样静”。“平静生活”的背后是什么?日常生活了无新意的复制与“写昨日”的偶尔重临之间是什么关系?台风会突然改变日常的秩序,而诗歌亦然。人世,山林,诗歌,厨房,自我,梦幻,现实就是以这样不可厘清的方式糅杂或叠加在一起。更为不同的是,杜绿绿甚至能够同时将厨房的烟火气和精神远方的虚幻放置在诗歌中。它们彼此咬合、摩擦、龃龉、纠结。也就是说,诗人在诗歌中处于什么一个观察和言说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由此具体到杜绿绿的诗,她更像是站在阳台上的诗人。这是三位一体。她身处于日常甚至杂乱的诗意了无(也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诗意)的居室之内,她曾借住或暂居于此——“房子狭小,堆满老旧的家具 /单人床落满灰尘 /我睡在厨房的地板上”。她又可以站在阳台附身观看尘世中发生的灰蒙蒙的日常浮世绘。与此同时,她还可以踮起脚尖眺望城市之外的精神“山林”与梦游一样的“远方”——“我们 /同在阳台上看路的去向”。这三个视角和三个位置同时融合进一个人的诗歌中,它们所一起叠加或交错的精神景观也必将是复杂难解的——“这些,/粗糙的手啊 /像要将我带离这儿。//可我还喜欢这个家,在清晨点火盆 /在炭里燃烧烟草 /用干瘪的嘴吸上几口”。而“住在失语的房子里”该如何重新发声?“我拘谨有礼地活在我们的房子里。/如果,这房子是我们的。”在杜绿绿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一个“冒险岛”。她嗓子里冒出来的声音是“我要去外面 /哪怕有一天会枯死”,“但愿明天 /能从这轮椅上逃出去”。无形的轮椅。多么可怕!这是一个爱丽丝!你看到杜绿绿诗歌中反复现身的那只兔子了吗?
杜绿绿的诗歌印证了一种“声音的诗学”。这是一种气息,实际上更接近于精神的呼吸。杜绿绿传递给我们的诗歌声音既像实实在在的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自语、对话和自我追问,又像是来自遥不可及虚无难触的另一个空间。或者说仿佛来自于另一个尘世——这个声音与我们有关,又有所不同。这种切近和遥远、现实和彼岸的拉扯刚好是杜绿绿诗歌声音的一个标志。杜绿绿是一个在诗歌世界中不断与自我较劲儿的人。她诗歌中那么多的人称指代,我,你,我们,甚至他,在更多的时候都是指向了诗人的不同层面和域界的“精神自我”,“白天,/我做着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杜绿绿在她的诗歌写作中设置了那么多独语的“自我”以及主体与不同人称指代关系之间的对话和交谈的动因。这与其说那是一种交谈,还不如说是不同镜像之间的自我盘诘。这是一种打量、存疑和诘问的诗歌。杜绿绿的诗歌和内心一直有一个率真的小女孩不时从语句和日常空间中冒出头来,转几个圈,做几个短暂的梦然后又再次回到精神成人的日常状态之中——“跳上汽车那一刻,她意识到此刻 /又是在梦中。但是吃了,/她不能从汽车上跳下来,汽车快得像幻觉 /玻璃窗上的人 /苍白如纸。她不能否认这个人正在背离自己。//她抚摸‘她,她知道 /这个女人从来都不是谁,不是那个 /梦境之外的人。”(《另一个梦露的奇遇记》)她不停坠入迷梦又不断从其中起身回顾。“她们”从来都是同一个人,但也可能从来都不是。她不停地在梦幻与现实之间折返,与不同界面和临界点的另一些“她”相遇。有时是已知已在的熟稔,有时候又是未可预料的陌生。这是主体的“她”对“自我”的打量、查勘和探询与疑问,“她总在我后面,许多年来 /我在不少地方看到过她 /一声不吭穿着黑衣服,有时 /居然和我是同样的款式。”“我的眼睛里什么都有,只是没有我。”诗歌对于杜绿绿而言,既来自于日常的生活状态,更重要的则是来自于一个人特殊的精神生活。也就是我们要每天无诗意的活着,又需要精神生活来作为支撑。尤其是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更是如此。那一首首在生命自然状态或者某些情势刺激激发下的诗歌,更像是一次次精神成长和寻找的过程,是一次次的精神出走、游离,暂时抽身、转身和出离的过程。比如这方面的代表作《她没遇见棕色的马》。在日久弥深中期待那匹棕色的林中出现的马最终只能是虚妄。这是一首无望的诗,也必将是错乱的白日梦幻连接不起来的惨烈碎片。起句“女人老了”本应该给我们诸多温暖的慰藉和怀想,可是接下来全诗呈现给我们的却恰恰相反。一路陡转直下。那匹诗行中现身的马应该承载着如此多的精神寄托和女性幻梦,但是这都是虚妄。因为,仍然没有那匹棕马、没有远方、没有明天、没有精神的安栖之所。诗中反复出现的“如果”“像是”加重了这种分裂性和虚妄无着的想象。她只能接受夜色,她的叫声就是最强烈也是最虚弱的自我镜像。讽喻之诗也必将来临。“女人老了”“但是”“谁都以为她要走了,她也这么打算”“如果”等不断强化了这一虚妄的过程。而这一虚妄的过程在杜绿绿这里是通过冷静和平淡的语气得以完成。这却又再次以张力强化了这一虚妄。这是一个“梦生梦”的“梦游者”和“远行人”,“离开所有人,走进行李深处”“她没有再去想那刻,她带上了那本书 /她走遍了这座山的所有坡底,/什么理由也没有”。这同时又是胶着和面对实有、日常和当下的蜗居者、偶尔的失眠者、年轻的母亲、主妇和瑜伽练习者。与此同时,也是一次次的精神出走之后回来途中的自我劝慰与宽怀。杜绿绿有一首诗叫《寻人启事》。这首诗是其精神自我的代表性作品。类似于“杜小羊”的自我寻找实际上更像是女性精神的寓言,如此真实又超拔于真实。从而就显得更加真实,因为这是由现实真实提升为想象力和词语的美学真实。显然,后者更重要,也往往很容易被圆满的完成。这是一次次的自我的重新发现,也是一次次向上一个瞬间“旧我”的打量与告别。杜绿绿一直瞪大着眼睛,试图把暗影里那个未知的“我”和已经成为过往的“她”拉拽出来,让三者同时站在微微的灯光下,同时现身,彼此抵牾,互相查验。在杜绿绿这里,不仅不同的人称指代指向了不同的我,而且不同代际的女性家族形象也不断在其诗行叠加成特殊的精神谱系,比如外婆、祖母等——“我来自很远的地方。/我母亲 /与祖母的房子建在黄沙里。/她们从来不洗澡”。这是不同时间序列里的“她”。“她”既是同一个,又不断在转喻中完成精神自我的分身术——“少女们,早晨!你们朝着不同的方向 /在窗外抚摸这一时刻”(《暗流》),“她又要生产了,生下另一个自己”(《梦生梦》)。但是,好天气和好时光能够有多少呢?——“我们喝呀喝,喝呀喝,好时光就回来了”。
杜绿绿的诗歌腔调往往是自语、独白、对话、自忖、出离甚至是分裂盘诘的,日常性的自我与精神性的“她”之间形成了戏剧性的冲突。这是一个略显胶着的矛盾共生体,温顺而不羁,眷顾而决绝,自信而犹疑,直觉而冷静。杜绿绿的声调往往是不动声色的,不冷不热的——“沉静的病人”、“寂静的恐惧”。即使处理死亡的抒写,她也能平静地站在寒冷雪地的深处向你慢慢讲述,“你死了。/我说不上难过,总有一些人死得突然。/比如我们的一个远房兄弟,他二十岁就吊死在父亲 /死去的堂屋里。/他的父亲,/也是这样死在梁上。”(《十一月》)但是,在平缓的语流下突然出现甚至炸裂的火中取栗、抱冰行走的决绝、阵痛的句子却令人寒噤满怀。比如,“这个早晨 /我把剪刀裹进 /坐在你身边 /露出和你相同的表情 /你并未察觉”(《镜子里的人》)。很多女性诗人大抵都属于安静时的写作,但是这种“安静”又很容易成为一种四平八稳甚至是日常“流感”式的平庸。而杜绿绿的诗歌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和印证了“异质性”的声音。这是一种张力,也是一种悖论性的容留。很多女性诗人往往在凸显自我和精神性的同时形成精神洁癖的症候。也就是往往她们的诗歌更具有自我的排他性,甚至很多女性诗人通过诗歌语言将自己扮演成种种角色,或干净圣洁,或自白的歇斯底里与寻衅。而杜绿绿的诗歌往往能够在日常和精神话语中出现“破”的一面,也就是这种诗歌话语不属于惯常意义上我们所听到的女性诗歌的“声音”,但是这一特殊的音调更多带有诗学意义上的难度和个性,比如“半明半暗的清晨,真他妈冷 /林子里烧着火”(《迷失者》)。“真他妈冷”“快乐得像个小妓女”“我他妈也飞累了”“与远处埋在裤裆里的大个儿”“像你最瞧不上的老娘们儿”“谈论厕所里的笑话,像两个纯洁的好人”“我写下一行恶毒污秽的句子”“我们可以一块 /对着无尽的阴沉说脏话 /喝酒,抽烟。/——去他妈的吧,这该死的雪地”“我们来相会吧,/菩萨。/不要再露出微微的笑容”“让你犹豫舔着我的肚脐”“用模糊的性器解释他们的梦”等“不洁之语”都可以入诗,入女性之诗,入杜绿绿之诗。这就是杜绿绿诗歌写作中的自嘲、反讽、小小的燥热和“不安分”之处。也就是说杜绿绿的诗歌自然、真实、原生而又具有一定的疏离和超拔性,没有一般女性诗歌话语的自我清洗与精神洁癖。那些干冷简硬的诗句中经常有刺儿、有寒噤、有倦怠、有尘土,有很多女性不敢言说的部分——“灌木低矮,你们俩蹲下去 /说些严肃的话。/小便清亮,顺着马蹄草的茎叶 /向低处流去。/要经过妈妈的菜地/才能到屋东的池塘”。是的,她勇于说出。
诗歌是为了铭记。这句烂俗的话对于女性写作而言却还往往凑效。就杜绿绿而言,她的诗歌中曾一度出现得最多的句子是“去年的时候”,“像是多年以前”,“她曾坐在春天的台阶上讲述过去”,“童年的境遇”,“好像爱丽丝旧地重游”,“当我老了,谁来爱我”,“那是几年前”,“许多年来”,“我们相识多年”,“我们停留在年轻时候的暗青里”,“此刻我怀念着逝去的时光”,“反看那荒芜的旧日之地”。在“生活多年来从不会改变”的日常情境之下,这是一种“后退式”祈愿式的精神诉说与追挽。可是这种向度的诗歌很容易成为自我眷顾式的水仙。换言之这样的诗歌精神打开度往往不够宽阔。而杜绿绿能够在这类诗歌中做到过去时态和当下甚至未来之间的共时性呈现。这个很重要,也很有难度。也就是说她诗歌中的“声音”“腔调”“时态”既是个人的,又有一定的普世性。这必然是回溯之诗,是直接面向时间的生命体验以及冥想性自我的精神性寄托。与回溯和后退的诗歌姿态相对应,杜绿绿还不乏面向时间、自我和未可知的明天的预叙能力。这个往往是女性诗人很难完成的,比如“这个老妇死在秋天”。
杜绿绿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各种高矮疏密的树林(比如《鸦雀无声》《她没有遇见棕色的马》《失踪者》《冒险岛》等等)。这些浓密或稀疏的树林对应着她的内心世界,“眼下 /我带着震惊、湿透的衣裳 /与刺破肉体的勇气 /坐在无人涉足的林荫深处”“他们踏着满地的荆棘向林子深处走去”“她在树下睡觉,她在树上睡觉 /除了这件事,她再也不干别的了”。杜绿绿曾坦言自己喜欢高大、干净、挺拔的树木。这一切在诗歌心理学上象征着什么呢——“却从未走出幻觉密集的荆棘林”。比如,她诗歌文本中出现的松柏(落叶松)、棕榈、榕树、桉树、杨树、苦楝树、杉树、桉树……甚至有时候杜绿绿在诗歌中把自己的位置放在“树梢”上,“我坐在枝头 /身后都是雾气”,“我在树上不曾挪动,还是有风”。有时候欢乐是在“高入天际的树冠上”,有时暮晚或黑夜中的树林又代表了并不轻松的未为可知的精神对照。这既是精神的眺望和凝视,也可以随时顺着树干来到踏实地面。H城,桂城和 S城,这些日常性的空间更多只是作为杜绿绿诗歌的一个一闪而过的背景和陪衬。而当下更多的诗人却正沉浸于这些城市化空间的日常抒情与道德伦理。反过来看,女性诗歌很容易占据分守其一,而不能同时完成。分守其一的诗歌很容易导致日常生活的平庸或陷入无限自我精神膨胀的天鹅绒监狱之中。这两个向度实际上是同一个狭窄的精神症候的结果,其对于诗歌写作自身而言是有害的。实际上这也正是自我精神与外物之间对位、呼应和精神交感的过程。这个特殊的“树林”离人世、生活和现实只有一步之遥。可诗人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一步。不远,不近,刚好处于日常和自我精神最适中的位置上。这样的诗歌就注定不是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或者说杜绿绿的诗歌不具有这种暴烈的、迷恋的、偏执的女性精神症候。她的诗歌就是一种呼吸,一种声响,刚好处于离我们切近又有着一段距离的位置。
有时候自我冥想或铭记成了诗歌戏剧性的一部分。杜绿绿是一个优秀的讲述者,女性写作绕不开的一个部分就是“自我戏剧化”。这是“另一个梦露的奇遇记”。这种诗歌中的戏剧化在杜绿绿这里既指向了过去时态又指向了遥不可知的未来时态,比如《谁来爱我》《好时光里的兔子》《另一个梦露的奇遇记》等。而人尤其是女性作为短暂和瞬间的时间过客该如何面对未知与前路?这必然是时间的无望的自我讽喻之诗——“这里葬着她的少年、青年和暮年,/可惜它们都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她想,她是这个女人的先知,是‘她的将来,/有可能存在的任何人。她唯一不可能 /是‘她。”杜绿绿那些通过一丝细节展现的时间力量更能打动我们,“我的家具上到处是黑色压痕”、“它是个工艺品,有日久年深的污垢”。这让我想到梵高笔下的脏破翻卷的农鞋。
女性诗人中不乏通过词语和想象,来完成通灵能力的人。而杜绿绿的诗歌中不时有瞬间完成的闪电天启一样的直觉丰赡天籁的句子令人惊奇,比如“她转而也安静了 /引溪水擦洗墓园”,“她拖着浸满水的自己与猫”,“乳房是个老母亲 /衰落在高高隆起的腹部”,“她快乐地踢着皮箱 /——一个巨大得能装进去 /一个人的皮箱。”用溪水擦洗墓园,该是怎样的一番人世日常而又不同寻常的景象呢?这些句子是不可复制的,包括她自己也不能再次复制。杜绿绿的诗歌语言干净而节制,正如她所倾心的那些高大、干净、挺拔的植物。当然,她也并不缺乏女性自身的任性和小脾气。有时她也用树叶和枝条来修饰和掩盖,但是最终那些挺拔的躯干成了她诗歌独有的质地。其白描和即景以及设置场景的能力很突出,甚至不乏戏剧性和叙事性的冲动,
简洁有力,有时又是晴朗和阴郁甚至寒冷并置,犹如北欧无尽雪地之下容易患上的忧郁症。
近期杜绿绿的少数诗歌中,其直觉生成性和语言的湿润质感正在为一种“深度”的干涩和知性复杂性所削减。最为直观的变化可以从诗歌的体式上看出来,近期的诗集《她没遇见棕色的马》明显每一行诗歌的长度以及文本的整体长度都变大了。这表示了什么呢?甚至有几首诗的“叙说”被“说明”所代替。我不知道这种变化对于一个诗人“风格”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是一种“成熟”和所谓的“完整”,那么一个诗人应该反思的恰恰是“成熟”“完整”的代价是什么?而历史上伟大的诗歌往往是“有残缺的伟大”。而对于一直自然而然写作的杜绿绿而言,也许,我的这个疑问对她来说够不成必要的谈论。
2014年 10月的海南。一群青年诗人围坐,身后是茫茫的大海。那时已近暮晚,突然海上有烟花闪现。在我指给身边正在吸烟的杜绿绿看的时候,烟花一瞬就消失了。我想到杜绿绿的诗,“远处有烟花升到半空又很快落下,/黑暗与光华交替得过快”“远处,灯光像是永不可触及的过去”。短暂的灿烂,长久的倦怠。大海代表了某种未知,也与日常生活之间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大海是一部常读常新的古老卷宗,关乎时间,指涉灵魂的秘密——“请让火车带我去大海,从这里,/碾过今日的重复,铁轨中有下沉的秘密。”日常之心需要那些来自诗歌的火光,随之而来的仍然有小小的芒刺——“她走了,我也决定去北方看病 /胸口的刺生的越发大了”。杜绿绿年纪轻轻,却在诗歌世界中不停地吸着纸烟。这在精神向度上是慰藉、是自我取暖、是惬意,还是不安与胶着?“我想和你说话。/你哆嗦手指,不停地打火”“旧家具在房子里,她在弹簧沙发里。/绿色地毯上,只有 /她手里的烟还活着。”在湿漉漉的午夜中所喷卷出来的烟雾,那偶尔闪烁的红点,它们离这个世界很近,同时又很遥远。也许你等了一生,密林中仍然没有那匹枣红马出现。但是,一个不曾更改的声音则是——你仿佛来自另一个尘世。
本栏责任编辑 胡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