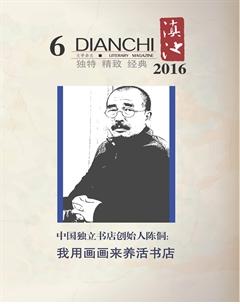山中夜雨或室内丛林
杜绿绿 霍俊明
霍俊明:杜绿绿你好!微信越来越方便了,那我们就通过微信聊聊你的诗歌吧!
杜绿绿:好的。
霍俊明:好羡慕你啊!每天不用上班,最忙的时候也就是你练瑜伽的时候。时间都是自己的。你的日常生活是陪儿子上学、弹钢琴,自己练瑜伽,偶尔徒步进山。说个最老套的话题,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情境下写诗的呢?或者说你是为什么与诗歌发生了关联,而不是其他。
杜绿绿:2004年夏天无意识中认识了一些安徽的诗人们,陈先发、余怒、黄玲君、曹五木等,认识他们后觉得好奇怪啊,如今还有那么多人写诗。我和我的闺蜜时不时会偷偷嘲笑一下诗人。
霍俊明:曹五木是河北人,后来离开了《诗歌月刊》。
杜绿绿:有一天傍晚,我和闺蜜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从郊外回城。在车上又谈到了最近认识的诗人们。我看着天上的月亮,觉得很好笑嘛,就随口说了几个句子,并且问我的朋友们,这叫不叫诗啊!他们起哄,说,叫啊叫啊。我回家把这些句子写了下来,发给当时《诗歌月刊》的编辑牛慧祥看,他说这是诗。然后,就发表在下一期的《诗歌月刊》上了。我就是这样开始写诗的。
霍俊明:你对当下的女性诗歌是否有自己的观感和判断?
杜绿绿:我对当下女性诗歌没什么深刻的观感。读的不多。再说了,诗就是诗,为什么非要分男性女性的来谈。好土气。
霍俊明:好像很多女性诗人都很反感在谈论中强调诗歌与性别的关系。你也不例外。我谈论诗歌从来既是个体的解读又同时是作为一种现象的延伸与分析。如果完全不涉及到性别似乎也不太可能。
杜绿绿:你的文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要因为别人的喜好而做变动。那是你的文章,要保持你的风格和个性。
霍俊明:是的,我喜欢听别人对诗歌和生活的看法。但是我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我对批评自身的坚持。不管最终做到什么程度,我愿意把自己的诗歌批评看作是另一种呼吸。这个,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上帝诸神也不能。
杜绿绿:是的!
霍俊明:那么说说狮子座女生吧!
杜绿绿:其实我是个很呆板的人,有时看着或许会有些热情奔放。那全是狮子座的不设防造成的。是的,我是个狮子,把大部分心思暴露给别人看,留下来的一小部分是不可告人的自尊与秘密。嗨,你也会忧伤么,看上去不大像。许多人这么对我说。难道我长得如此娃哈哈么,还是太虚伪,把每一分不爽都给藏起来。我需要跟人解释,我此刻真的很难过,而他们多数以为这个是撒娇,是不想好好过日子的浮躁行为。可事实上,我的心真的要碎了。
霍俊明:那么,诗歌与你的日常生活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杜绿绿:诗歌和我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有关联的,它从精神层面完善了我自己,对我人格的改善与完善是有帮助的。
霍俊明:诗歌对你的精神和人格起到这么大的帮助呀?诗歌在你这里起到了典型的教育和教化功能啊!
杜绿绿:我是这样觉得的。而且,因为我现在不工作,所以我目前认识的人,大部分都是写诗的,或者相关的文化艺术方面的人。
霍俊明:写了十年,你当下的写作有没有进入瓶颈期,或者说还是处于调整的爆发期?
杜绿绿:从写下第一首诗到现在虽然已经有十年了,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久。写作实践远远不能算是完整的十年,期间中断了那么多。头一年就是写了一首,停了一个月,和诗人们聚聚,又振奋了,回家接着写。我只是顺其自然,那时,我对诗歌写作没有任何的概念和目的。这样持续了至少一年后,才有了写作的意识。然后2008年元旦到 2011年秋天,这三年基本中断了写作。
三四年才写了五六首诗,完全失去写作感觉和冲动了。更多是因为我当时怀孕生孩子,什么事也做不了。
霍俊明:我在你诗里能够读出你的个人生活,比如写于 2008年的诗《鸟鸣》等能够看到当时你怀孕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杜绿绿:我那时也有焦虑,我停了这么久,可能再也不会写了,当时这么想。然而 2011年的下半年开始,我突然进入了写作爆发期。这在我的第二本诗集《冒险岛》里可以看出来。这本诗集时间跨度大约是六七年,其中一半都是在2011年写的。
霍俊明:2011年是你的诗歌年。女性写作就是有时候不稳定,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突然无缘无故地开始写,然后莫名其妙地中断,过了些年又再次热烈地与诗神相遇。
杜绿绿:所以我觉得 2011年是我写诗进入一个新的写作阶段的开始。2012年我却又写得极其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2013年到2014年,却又写得挺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写作是对 2011年的延续、完善以及发展。所以,这样说的话我觉得目前谈不上写作的瓶颈期,这不刚开始吗?
霍俊明:中国女性诗人几乎很少有终生写作的,那么你自己有何打算?还是一切顺其自然?万一再也写不出诗了,你的精神支撑是什么?
杜绿绿:我并没有给自己作任何预设,是终生写作,还是写写停停?目前来看,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并且对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现在很喜欢写诗,这个很重要。我不想放弃我
喜欢的事情。万一哪天不写诗我的精神支撑是什么?这个问题又是一个预设。作预设不好。我从来没想过我的精神支撑是什么,写诗也不是我的支撑,写诗是我喜欢的事。或者,这样说来,我们的精神支撑应该是善意与爱。而这些,我不能否认诗歌能完善它们。
霍俊明:你有没有注意到多年前的一段时间,你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山林、夜雨和黑夜?甚至它们成了你那一段时间最为突出的诗歌背景呢?我已经统计过了。
杜绿绿:是吗?可能是我住在山边的缘故。我的窗外就是群山,从楼梯口到山边大约就五十米吧。我突然发现每个窗户望出去都能够看到山呢!这可能也是日常的描述吧!
霍俊明:山上有寺庙、道观或者古迹吗?
杜绿绿:好像没有。白云山是广州市内的山,哪有这些……
霍俊明:另外,你有很多特别短的诗,每行短,整体也短,可是短诗的难度好大啊!你怎么看自己的这些特别短小的诗?
杜绿绿:不同时期的不同吧!我喜欢短诗。但我早期的短诗,更多是因为技术的不成熟而感情的充沛造成的吧,写不长。如今的短诗自然是反过来了,情绪的波动越是激烈,技术上处理得当,可以在极其有限的字数里给它更大的空间。相比这种写作技巧的成熟,早期的一些短诗虽然简单,但更显得真挚与意外的格局。
霍俊明:是的。就情感和技巧的关系而言,就诗歌的感染性和可辨识度而言,你的《冒险岛》和 2014年出版的《她没遇见棕色的马》两本诗集,我更喜欢《冒险岛》。其原因可能是《冒险岛》写作时间跨度大,能够容纳和凸显不同写作时期你的特点和变化,能够容纳更多的不同的声部。
杜绿绿:啊,这样啊!可我觉得《她没遇见棕色的马》这本诗集,我应该写作更成熟更完整了!我自己这么看。
霍俊明:可能是吧!但是有一句话,你得到的同时,也必将失去。
杜绿绿:可能吧!
霍俊明:这两天家里养了水仙。每次看到它的茎块以及绿绿的叶子我就会想到大蒜。可能有时候水仙和大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啊!水仙与大蒜的合体应该是诗人形象的结合体,既离不开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又有精神生活的水岸。
杜绿绿:我不喜欢水仙,也不喜欢花花草草,我喜欢高大、挺拔、干净的树木。可是每年台风来的时候,山上的乔木林都弯倒了。
霍俊明:怪不得你的诗歌里有大量的树木场景和意象。
杜绿绿:这些树木与我的生活和写作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霍俊明:我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做的梦是无色的、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杜绿绿:我的梦是彩色的,不过并不是特别鲜艳的吧,但是有颜色。我不喜欢做梦,这影响睡眠,而且我在梦里都会有点伤心。
霍俊明:我的梦是彩色的,而且绚烂之极,很多场景都奇异极了,甚至有时候自己在梦中提醒自己不要醒来了,梦太迷人了。这几天微信都在刷姚贝娜和余秀华。姚贝娜太可惜了,才 30多岁就走了。还好,她的歌声还在,她捐献的眼角膜也成功移植了。这算不算有些八卦啊!
杜绿绿:我不认识姚贝娜,也没有听过她唱歌,我实在不知道她。如果不是被刷屏,这个名字我没有一点儿印象。得病的人太多了,我实在不能为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难过。我舅舅贲门癌,我堂叔叔上吊死的,我表姐的儿子小时因为发烧成了傻子,20岁的时候还走丢了,我爷爷是胃癌死的,我的朋友得了乳腺癌。我认识太多不幸的人了。我思维不敏捷,不关心社会,对科学更是一无所知,也不爱瞧这些。娱乐精神也很缺乏,对八卦的爱好浮于表面,我所知道的惊天秘密无非是意想不到的人搞了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人。而这些,我也可以算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霍俊明:从生活到诗歌我们谈的也不少了。其他的话还是留待下次吧!
杜绿绿:是的。谢谢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