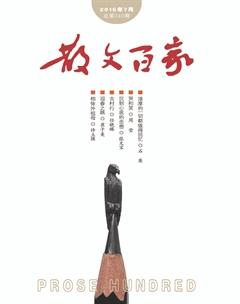益夏叔公
吴安钦
一到夏天,我便想起我的亲人益夏叔公。
益夏叔公是我祖父的堂弟,我父亲的堂叔。我常常听他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我和你爷爷虽然是堂的兄弟,但是,却像一只筷子捱断的两截。
这话说得对。我祖父没有亲兄弟,他也没有亲兄弟,对他们这一辈人而言,一个祖父下的孙子俩,就算是亲兄弟了。
我很小的时候,弄不明白,既然他们俩是一只筷子捱断的两截,那么,为何他们俩,一人在山乡一人在渔村,生活两地?依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随大人去他生活的山乡走亲,他带我们几个人去山上看祖宗的坟墓。祖宗的坟墓是在离他们居住的山村非常偏远的一座山上。我记得,翻两座山,越过好几条岭,又爬了几处山坡,才在一处山坡下的一堆坟茔中找到叔公所指的那个祖宗墓园。墓园小,简陋,但墓顶是水泥抹的,已变成黑色。墓前,有一堆重叠杂乱的石头。叔公说,这堆石的作用是遮挡远方一个什么穴位对墓地的威胁。墓地的四周没有一棵树,只有几株高过人头的不知名的草木,稀稀疏疏的,因为这几根草,反而凸显墓地的荒凉与突兀。伫足墓穴前,遥遥望去,视线里没有一处山村,更见不到乡村的炊烟。在我的感觉里,祖宗是被抛弃荒野的。继而,让我更不理解的是,那个年代,埋葬祖宗时,先人们为何,又是如何,将祖宗的棺椁抬到如此荒凉之处?
叔公也说不出道理来。当年,益夏叔公带领我们去看祖墓,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祖宗的墓园改一改或者修一修,但是,二三十年过去,依旧没有行动。
祖宗的墓地因过于偏僻,我只是跟随益夏叔公去过一次。后来,没人组织也没人提起,从此再没拜谒。
益夏叔公个子不高,甚至有些偏矮,但他不仅是他家庭的顶梁柱,还是家族里的一个头。在他生活的那个山村,住着族亲几十户两百多号人。但是,在这个村落中,仍算是很小的家族。也可说成是这个村里的一个小部落。小部落因为人少力弱,总是担心被大家族的人欺凌欺负,因此要特别地讲求胞团互助,以防被人欺侮。益夏叔公,他就是个家族观念非常强的长辈。家族里谁遇上什么事,他都会站出来说话出力。
就说当年我家发生的大变故。祖父在海岛渔村养殖海蛎时不慎溺亡,益夏叔公闻讯,第一时间放弃手头的忙活,从山村向海岛直奔而来。在海岛上,一直帮忙到我祖父入土为安才肯离去。翌年,我的父亲莫明其妙地病倒了,他担心,我一家人在海岛上单门独户,势单力薄,没人帮忙,更显孤单,又放下了手上的事,住在海岛上,替我家出点子拿主意。我父亲病重时,他几次和我父亲的朋友一起,抬着担架床一步一步送我父亲到他所在村的部队医院救治。父亲病危时,他就寸步不离地守在父亲身边,给父亲搓背捶肩。父亲因病而表现出的忧郁症,简直在折磨着家人。但是,益夏叔公流泪的同时,很耐心地安抚我父亲,给予他心灵最大的宽慰。最为感动的是,我父亲离世的那一夜,因为三十二岁未满而亡故,算是短寿鬼,我一大厝的人全部胆战心惊,避讳地全部关门闭户。此时,只有我的益夏叔公和几位我父亲的挚友在大厅上替我父亲守灵和料理丧事。送我父亲上山后,益夏叔公仍不放心,怕我家人尤为担心我的祖母节外生枝,又住两天后,才三步两回头离开我家家门。
那年头,祖母很感激益夏叔公,在他面前常常说些感激的客套话。益夏叔公说,我们是一只筷子捱断的两截。
我稍大一些的时候才知道,益夏叔公是个石匠。他当石匠的手艺,在我老家这一带乡村是名气最大的。一是他手艺精湛,用工细致认真;二是他多才多艺,设计、测量、打石、砌砖、雕塑、粉墙等等,粗工细活,样样皆通。政府的大小工程,谁家要盖房子,首选都是我的益夏叔公。经常出现因工程争着请他的局面。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公开招投标,大大小小与石头有关的工程,人家都是指名道姓要他。不到四十岁的他影响力非常大。五里十乡的男女老少都晓得,XX村有一个名叫益夏的师傅。后来,他的名字被人家简化通用为两个字——夏师。
夏师名气越来越大。原来,他二十三岁时,就开始收徒授艺。当年不少后生曾经以自己是夏师的徒弟为荣,也有不少的东家为自己的房屋是夏师所建而深感自豪。到三十岁时,他所带的徒弟已经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可谓桃李芬芳。有不少早已出艺的徒弟,仍然紧跟着他干活。
我老家下屿岛的这座礼堂就是由我的益夏叔公及其他的队伍所建的。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那几年,下屿岛大黄鱼发海了,大队积攒了一大笔三金,便决定投资几十万盖一座像模像样的礼堂。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工程的建设者,夏师自然是首选者。那一年,我的益夏叔公马上进岛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做勘察设计。不久,他的队伍便住上了海岛。我们一家人,特别是我,当时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叔公为无限荣耀,更为这么一座宏伟壮观的礼堂是我叔公所设计和建筑而无比骄傲。我记得,礼堂开工后,我常常一个人跑到离我家非常远的工地去看叔公施工。工地上有一大批工人。我就找我的叔公看。找到他后,我发现,他和其他工人一样,戴着墨镜埋头打石。錾子与锤子在石头上打敲得铿锵铿锵地响,还喷溅出一束束的火花,以及碎飞的石坯。他歇工时,抬起头才发现我,便催我赶紧回去。他吃住在工地上,晚饭后,还常常上我家坐一会。这座可容纳一千五百多人的两层楼礼堂,在我叔公整整努力两年后才大功告成。如今,这座大礼堂虽然历经一次大火洗劫,但是,其墙体完好无损,屋顶修葺之后,仍然以一道壮美景观和巍峨之姿矗立在海岛岸上。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的益夏叔公,以他质量第一、品位新潮、安全牢固的独特建筑风格享誉乡村三十多年,完全是实至名归,也不枉了他勤学苦练埋头苦干的一生。
益夏叔公有四男二女,其中两个儿子师承他,都各怀所技各有所长。日子过得如芝麻开花节节高。遗憾的是,那年的夏天,益夏叔公竟然突然地无疾而终,我们连看望他的机会都没有。
噩耗传来,我们一家人深怀无比悲痛之情,随祖母前往他的住地奔丧。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浩浩荡荡,仅他的徒子徒孙就有一两百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