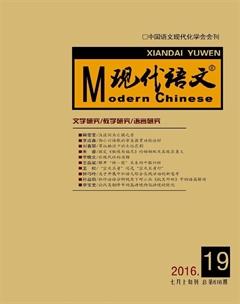吕叔湘语文教材观研究
摘 要:吕叔湘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家,对语文教材的建设有很大的贡献。吕叔湘对语文教材的研究较为全面系统,主要涉及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具体包括语文教材分编与合编的问题、编写的原则、语文教材的结构安排,等等;吕叔湘对语文教材的研究较为具体深入,主要涉及语文教材的范文、知识、练习、助读四大系统。吕叔湘的语文教材观对中国现当代的语文教材建设有着很好的启发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吕叔湘 语文教材观
回顾语文教育史,自古代语文教材诞生以来,关于语文教材的讨论与研究就从未停止过。张志公先生总结了古代语文教材的经验、问题和弊端;20世纪先后出现了以时代逆序编选的教材、按体制分类编选的教材、用现代白话编选的教材、以单元组合编选的教材、汉语文学分科教材、合编与分编型教材以及全国各地的实验教材,等等。因为语文教材自身会不断出现难以适应学生与教师的需要,难以提高教学的效率的情况,也因为时代的发展,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语文教育工作者们以其敏锐的学术目光与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活跃在历次的语文教材改革中,为语文教材的建设呕心沥血,吕叔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吕叔湘的语文教材观极具时代性又对当今的语文教改建设有所启示。
一、语文教材的重要性
好的语文教材是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关键。在谈到如何解决语文教学效率低这个问题时,吕叔湘在《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一文中提到:“教材编得怎么样?课文讲解怎么样?作文指导和批改怎么样?都有各种情况,都需要作具体的调查研究。”[1]由此可见,语文教材编写得好坏会对语文教学效率有很大的影响。语文教材的语体、选文、编排方式、组合形式、编辑意图、结构成分都将对学生的学习与教师的授课产生直接影响。
二、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
(一)多元性
语文教材编写的多元性是指语文教材可以有多种版本,除了教育部统编的一套教材外,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地方及学校的特点编制地方教材或者校本教材,甚至这三类语文教材也可以有多种版本。吕叔湘鼓励在允许的范围内多做实验,各自编写教材。“教材也可以不限于一套,除教育部统编的那一套之外,一个学校,几个学校,或者一个城市,是不是可以自己编一套试用呢?……甚至统编教材是不是也可以有两套,供大家选择?……我主张百花齐放。可能最后留下十家八家,甚至三家五家,就可以向各地学校推荐,让他们试用。”[1](P106)吕叔湘先生提出这些观点时正是文革结束不久,语文教材的建设也是百废待兴,先生紧跟语文教材改革的潮流,以发展的眼光提出了语文教材编写的多元性原则,鼓励全国各地多编写语文教材,多做实验,从中筛选优秀的语文教材再做推广。
(二)科学性
语文教材编写的科学性就是指语文教材的编写遵循着合理的序列,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点。正如吕叔湘所说:“总的说来,语文课的教材应该有一种合理的序列,但是很难做到一环扣一环,扣得那么紧。语文教学中有这种现象:往往一个内容不可能一次学好,而是要反复学,循环学,由浅入深,螺旋式上升。阅读、写作、语文知识都有这种情况。这个特点应该考虑到。”[4]语文知识有着自身的特点,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有着明显的区别,数理化等学科的知识是一环紧扣着一环,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与严格的序列性,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以继续下一个环节。而语文知识不同,语文知识的逻辑性和序列性都不是很强,语文知识中的字、词、句、段、语、修、逻、文,虽然也有着一定的序列性,但和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序列性明显不同。数理化等学科知识的序列性体现为知识点与知识点的连接与串通,比如不学加减就学乘除,学生会觉得不懂或者很难理解。而语文学科知识的序列性一般来说,体现为先学字词再学句段,或者说先学字词句再学习写作文,但并不绝对,比如我们既可以集中识字再学课文,也可以边学课文边识字,所以说,语文教材是较难做到环环紧扣,扣得那么紧的。
但语文学科知识有着螺旋式上升的显著特征,所以语文教材的编写也应该体现这个特点。所谓语文知识的螺旋式上升,是指语文的某类知识会反复在学生的学习中重复出现,学生每遇到一次都会有一次提高,有点“温故而知新”的意思。比如语文知识中一词多义的现象,最初接触这个词可能是它的最常用意思,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当初我们学习的意思已经不足以解释它在某中语言环境中意义,这时,大家会领悟到,同一个词语用在不同情境中会呈现不同的意思。于是,在相同词语的学习中我们又有了新的收获,这就是语文知识的螺旋式上升。语文教材的编写,既要考虑到语文知识的相对序列性,也要考虑语文知识的螺旋式上升性,兼顾语文知识的逻辑性和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规律性。
(三)针对性
语文教材编写的针对性是指语文教材应该针对不同的使用人群做相应的编写,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年龄阶段的使用者都必须使用同一套语文教材,应该具体分析不同群体的特点做出调整。“给中学生编课本,可以只讲一点‘当然的东西,不讲‘所以然。但是,给大学生讲课就大不一样了,不能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看待。”[2](P119)这就是说,不同年龄阶段对语文教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学生的学习阶段不同,理解力和接受力会有所区别,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学习方式与方法都不一样,这自然会影响语文教材的编写。中学生的学习内容多而广,辩证逻辑思维能力正在形成,这个阶段的学习方式多为被动接受,个人研究较少,他们的学习目标主要是掌握各门学科的知识,尽可能地涉猎更多的知识。针对这一特点,中学的语文教材就应该多为陈述性知识的呈现,而对于“所以然”,无需大谈特谈。而大学生则不同,这个阶段,学生已经有了很成熟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有了专门的研究方向,语文教材如果仅仅是“当然”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对知识的探求与理解,这时的语文教材应该有相当的篇幅留给“所以然”。那么,不同地区的群体对语文教材的要求又有什么区别呢?吕叔湘认为,农村地区的师资力量和学生学习的状况与城市还是有所差距的,所以他提倡农村地区“还是用统编教材好”。
三、语文教材的分编与合编问题
关于语文教材的分编与合编问题的讨论与实验,自20世纪40年代开明书店采用文、白分编法编成了《开明新编国民读本》以来,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先后出现了多种分编与合编的语文教材,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都有其优缺点,分分合合,如此循环,倒也呈现了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吕叔湘先生对于语文教材分与合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关于教材分和合的问题,就是阅读教材、写作教材、语文知识编成一本书、两本书还是三本书的问题……各种方案很多,但是基本上只有两派:综合派和分科派……分合问题的实质是几种教材的配合问题,说得更确切点是谁来负责分配的问题。综合派的办法是由编教材的人负责配合,结果就是编成一本,分科派的办法是让老师去负责配合,结果就是编成几本。比较起来,综合性教材难编。要在选文中找例证,并且要在读过的选文中找,要花费大量时间;设计练习也比分科教材难。如何编得丝丝入扣,技术性很强。分科教材编起来比较容易些。但在使用上,按现在一般教师的水平,似乎综合教材比较容易掌握,比较容易推广。分科教材要教师自己配合,一般教师会感到困难,不容易做好有机联系。无论哪一种教材,综合的,分科的,这么合那么合的,这么分那么分的,都要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不但要在神通广大的教师手上去考验,还要放到能力一般的教师手上去考验。我主张百花齐放。可能最后留下十家八家,甚至三家五家,就可以向各地学校推荐,让他们试用。”[2](P106)对于语文教材到底是分编好还是合编好,吕叔湘先生并没有给出绝对的答案。合编的教材编写较为困难,但是用起来较为容易,而分编的教材编写较为容易,用起来却较为困难,各有利弊。所以,吕叔湘认为大可不必在分与合的问题上纠结,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鼓励各种形式的教材编写方式,然后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使用,淘汰掉不合适的教材,最后留下编得好的教材就可以进行推广。
吕叔湘在1995年提出: “现在的教材基本上是一个模式,就是一本里既有白话,又有文言,既有供欣赏的文艺作品,又有供作文仿效的实用文字,还有文字并不精美而思想内容可取的文章。这样胡子眉毛一把抓,效果不好是在意料之中的。我以为教材可以分为三本,一本是为阅读和欣赏用的白话文读本,一本是为学习文言用的课本,一本是把作文指导和范文结合在一起的作文教材。有人要说,现在只一本语文课本,你把它分成三本,增加学生的负担。我觉得,现在是一学期一本,可以改为一年一本,这样就是把两本改成三本,增加不多。好处是每一本教材都有明确的目的,并且可以由不同的教师分开来教。 ” [4](P93)
那么,这里的主张语文教材的分编是否与上文所提主张百花齐放相矛盾呢?我认为不矛盾。因为主张语文教材的百花齐放是吕叔湘1980年11月在中学语文教材改革第二次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那时候的背景是文革结束后,语文教材亟需重新编写,相关问题还处于重新定位、重新思考的阶段,没有相关的经验与例子来验证某类观点的正确与否,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提倡各抒己见、百花齐放,多实验、多总结。而到了1995年,15年的时间足以筛选出一些优秀的、适合中国语文教育的教材,也足以淘汰部分不合适的教材。吕叔湘先生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实验,他发现语文教学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语文教材编写“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他提出把一本语文课本分为三本,根据不同目的分编,有的放矢。这种观点的转变,实质是吕叔湘语文教材观的系统化和成熟化。
四、语文教材的结构
(一)范文系统
吕叔湘认为,语文教材应该增加选文的数量,因为学生阅读能力提高的前提是大量的阅读,“教材改革必然引起教学法的改革。我总结了一些搞教改试验的老师的发言,有几点是一致的。一是加大阅读量,课内选文,有主张四十课的,有主张五十课的,还有课外阅读。这一点应该肯定下来。要提高学生阅读能力,靠薄薄的课本解决不了问题。”[2](P107)吕叔湘先生多次提到,要充实语文课本,选文应该丰富,这样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
(二)知识系统
关于语文教材的知识系统,吕叔湘重点强调了语文知识的重要性以及语文教材应该如何呈现语文知识。提及语文知识的重要性,吕叔湘说:“光逮住一个作文还不是最好的猫。还要逮文学欣赏,逮语文知识,逮百科知识,多多益善。”[2](P106)那么,语文知识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呢?“许多人对统编教材的语文知识短文不满意……怎么修改?不外乎两条路:一条是综合方向,把语文知识短文扩充改造,跟选文扣得更紧些;另一条路是分科方向,把语文知识短文拿出来,扩充成书。……恐怕还是第一个办法更适合当前情况。”[2](P111)“语文知识究竟是附在每课之后讲得好,还是写成短文穿插在若干课选文中间讲得好,我没有经验,说不好。也许两种方式都用得上。一方面保留现在这种知识短文,一方面在课文之后加点示例和仿造、改造的练习。”[4](P91)知识短文应该扩充改造,紧密结合选文。语文知识是放在后文之后讲还是穿插在课文中讲,这个不绝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三)练习系统
吕叔湘在练习系统领域研究得较为深入,阐述得也较为详尽。主要讨论了练习系统的重要性和如何具体编写练习系统。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中,吕叔湘对编写练习教材的问题做了专门总结:“会议期间好几位同志谈到对学习作文有辅助作用的单项练习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怎样编制这种练习,大有讲究。现在小学里流行一种‘解词练习,比如要小学生对‘关切‘熟悉‘高贵‘茫茫等词作出注释,这就难倒了这些孩子了。连编词典的同志都常常感觉困难的‘解词工作,怎么能叫小学生做呢?让他们试用这些词造句,比较容易,也比较有用。只要肯动脑筋,能设计出很多种好练习。语文课过去缺少公开发行的联系教材,许多学校的老师自己都在编,都在用。是不是可以选一点出来,让出版社印出来,让大家看看。现在缺乏经验的教师比较多,叫他们自己编也有困难,有现成的也不要空放着。会上有同志说他们正在编比较系统的练习集,希望快编,可以多找几个人,任务分组一下。”[5]在谈到作文教材中对“理路”的训练时,吕叔湘先生说:“有个练习,你们在教材里可以做做。50年代,我读谢老谢觉哉的一篇文章,发现有8个句子,一环套一环很严密,次序一处都不能改。我抄了下来,抄在卡片上,一句一张卡片。把次序打乱,就不好排,别的排法都不顺,只有谢老写的那种排法才顺。这样的练习可以让学生多做做,让学生排。只可能有一种答案,不可能有两种,才可以做教材。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对训练理路有好处。”[6]“编练习册不宜用‘改错这种方式,因为学生往往改了这个错而出那个错。练习可用仿写的形式。小孩子学语言本来就是从模仿开始的。”[7]
语文教材中的练习系统尤为重要,这点吕叔湘先生反复提及,并且一再建议要多编语文练习,尽快编写练习。但是具体怎么编呢?吕叔湘提出要重视逻辑思维的训练,通过排序可以训练“理路”。练习题一定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给予正面的引导。
(四)助读系统
助读系统主要是指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选文的注释、提示、图像和附录等。吕叔湘在这方面所言不多,在为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作的序中,吕叔湘说道:“编者在每一种作品前面作了简要说明,性质接近上文所说的解题目录,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作为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价值。各篇的注释主要是词汇方面的,也涉及一些语法问题。”[3](P229)助读系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帮助我们了解文章,理解题目与字词,了解文章的价值,等等。但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样,就过分夸大它的作用,从而使得助读系统占据语文教材太多篇幅。这点可以从吕叔湘对于语法图解的用途及其局限性做的阐述看出:“图解的用处是有限度的,它不能解决语法分析中的疑难问题,它更不能代替语法用例的说明。使用图解要有节制:第一,不需要它的地方不用它;第二,在小范围里用它,不在大范围里用它。所说小范围,指的是比较简单的句子以及复杂句子的某些局部。整个复杂句子,如果要用图解,就得把它简化。”[3](P188)
五、吕叔湘语文教材观对当今语文教材建设的启示
吕叔湘对于语文教材的重视,提出的多元性、科学性、针对性的语文教材编写原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对语文教材的建设都有着很大的价值。他对语文教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作业系统、助读系统的详细研究论述,给了我们反思与改革语文教材提供了具体的示例,也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尤其是吕叔湘先生在语文教材编写问题上体现出的包容并蓄、兼取百家之长的胸怀,那种考虑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念,与当下新课改对于语文教材建设的要求不谋而合。
注释:
[1]吕叔湘:《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第7-11页。
[2]吕叔湘:《吕叔湘论语文教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
[3]吕叔湘:《语文近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4]王晨:《重读吕叔湘 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5]吕叔湘:《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中学语文,1979年, 第4期。
[6]朱泳燚:《吕叔湘先生谈“理路”及“理路”教材的编写》,课程·教材·教法,1989年,第12期。
[7]吕叔湘:《吕叔湘先生谈语法训练》,中学语文教学,1991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吕叔湘.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8(2):7-11.
[2]吕叔湘.吕叔湘论语文教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230.
[3]吕叔湘.语文近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229.
[4]王晨.重读吕叔湘 走进新课标[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84.
[5]吕叔湘.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几点意见[J].中学语文,1979,(4).
[6]朱泳燚.吕叔湘先生谈“理路”及“理路”教材的编写[J].课程·教材·教法,1989,(12).
[7]吕叔湘.吕叔湘先生谈语法训练[J].中学语文教学,1991,(7).
[8]方有林.语言学视角 科学化追求——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9]韩芳芳.论吕叔湘之语文教材观[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2).
[10]王芸.对吕叔湘语言教育思想的再思考[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1]阳微.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解慧明 江苏扬州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