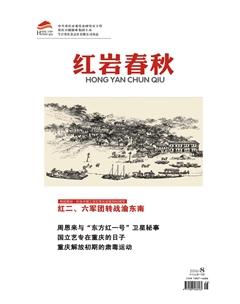“浮游”炸弹在敌机群中开花
唐学锋
“浮游”炸弹是指一种装有定时信管的、由一方在预定空域高空投下带有降落伞的炸弹,悬浮在空中,利用各弹所设定的不同引爆时间,形成一个既深又宽的爆炸空域,从而对进入该空域的敌机群形成杀伤力。这是一种对付庞大机群的空中战法,最早由意大利空军提出,但在空战史上却少见在实战中运用。
1940年8月11日,中国空军在重庆大空战过程中,首次对来犯的日机使用了这种新战法。
力量对比悬殊的空战
1940年5月,侵华日军以重庆、成都为主要目标,发动代号为“101号”的航空进攻作战。其参与作战的部队有陆军第三飞行集团所属的飞行第60战队、独立飞行第16中队、飞行第44战队第1中队、独立飞行第10中队,共计重型轰炸机54架、战斗机12架、侦察机15架;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鹿屋航空队中攻机24架、高雄航空队中攻机24架;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12航空队舰载战斗机42架、舰载轰炸机12架、舰载攻击机12架;第13航空队中攻机42架、侦察机4架;第14航空队舰载战斗机12架;第15航空队中攻机42架、侦察机2架。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共投入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共297架。
中国方面,防御重庆的空军部队主力仍为中国空军第4大队,以及临时从成都方面抽调过来的第3、5大队部分中队。与1939年驻防重庆的空军力量相比,由于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撤离,防御力量大大减弱,其可战斗的飞机仅有40架左右。
中国空军使用的主战飞机为苏制E-15、E-16战斗机,以及美制霍克Ⅲ战斗机。除了改进吸氧装备,使飞机作战的有效高度从5500米提升到7000米以外,中国的飞机在装备上没有更多的改进和提升。而日军使用的飞机与1939年相比,均有了较大的改进,如陆军使用的“三菱97式重型轰炸机”,在1940年已由原来的Ⅰ型升级为Ⅱ型。与Ⅰ型相比较,Ⅱ型的载重量已由7492公斤(总重)增加至7916公斤(总重);发动机由两台950马力的中岛“Ha-5”改为两台1500马力的三菱“Ha-101”;最大速度由432公里/小时,增加至478公里/小时;实用升限由8600米上升到10000米;其自卫武器在7.7毫米机枪5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门13毫米的机关炮。另外,日本海军使用的“三菱96式陆上攻击机”在载重量、飞行速度、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有提升。同时,日本海军还投入装备有2至4门20毫米机关炮、自卫火力更强的“三菱一式陆上攻击机”。
1940年,日军一改1939年空袭重庆的战术,主要采取以大编队方式进入重庆上空进行轰炸。在1940年,日军一次性出动飞机达到上百架的就有16次,而在1939年,一次性超过50架的也仅有2次。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想要突破上百架日机上数百挺机枪和机炮形成的高密度火网,其成功的几率很小。
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全部依靠对外购买,不能自己生产,损失一架就少一架。曾居住在重庆的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观察到这一幕,在其《中国的战歌》中写道:“我初到(重庆)时,有多达24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日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空军毫不退缩,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与顽敌展开殊死拼搏。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甚至提出一种“以机撞机”的战法。郑少愚认为,我们的E-15、E-16战斗机火力太弱,无法给日军轰炸机以致命打击,只要将日机机翼部分撞毁,日机就没有办法返回基地。而我方飞行员在机翼断裂后,可立即跳伞,还有生还的可能。
这个危险性极高的战法一经提出,许多年轻飞行员便跃跃欲试。但此战法被空军当局知道后,以保护飞行员生命安全为由,予以制止。
新战法横空出世
当时,日军进攻内地的主要航空基地设在山西的运城(陆军)和武汉(海、陆军)两地,距离内地主要城市的距离均在800公里以上。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战斗机是没有能力担任起为轰炸机护航的任务。故在较长时期(1940年8月,日军占领宜昌,并修复当地机场,作为日军空袭内地的前进机场之前——作者注),日军均采取轰炸机大机群密集编队的方式,对内地城市进行轰炸。
相比较之下,中国空军使用的E-15战斗机最大速度为364公里/小时,续航能力为510公里;E-16战斗机最大速度为440公里/小时,续航能力为800公里;霍克Ⅲ战斗机最大速度为362公里/小时,续航能力为1281公里。中国的战斗机除在爬升、转弯、俯冲等方面比日军的轰炸机灵活外,在升限、速度、火力配置、空中滞留时间等各方面都比不上日本的轰炸机。若单机对决,中国的战斗机还可以凭借其灵活性取胜。但面对日机以大编队飞行,并由上百挺机枪(炮)形成上下左右密集的火网,中国空军的飞机便很难突破。且一旦有日机受伤,日机就会变动队形,将负伤的日机护卫在编队的中央。故要击落一架在大编队中飞行的日本轰炸机,在当时的空战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多次的重庆空战中,中国空军往往还未击落、击伤日机,自己早已是弹痕累累。
提及“浮游”炸弹,就必须讲到一个人——阎雷。他原名阎承志,辽宁大连人,出生于1918年,毕业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原中央航空学校)第10期。
在校期间,阎雷十分喜欢学习和钻研技术,一直在研究如何破解日军的这种密集编队。终于,在毕业之前,他完成了一套可行的空中攻击战法,以及相应的空中“浮游”炸弹制作方式。
1940年3月10日,阎雷以飞行单科成绩第一、学习总成绩第三的优异成绩从航校毕业。不久,他便以准尉见习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部所在地——重庆市郊的白市驿机场报到。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亲自指派第23中队飞行经验丰富的王广英中尉为召集人,负责联络资深队员与阎雷讨论如何更有效地实施这种空中爆击新战法。参加这一战法研讨的主要成员还有司徒福、郑松亭、洪奇伟、高又新等人。不久,一份关于这种新战法的“攻击队形、进入方式、信管延期时间以及投弹前置距离”等内容的报告呈交到郑少愚手中。
地面推演工作完成后,中国空军第4大队又进行了一次空中模拟测试。以阎雷驾驶的飞机为假想敌,另外6架E-15战斗机则进行对头攻击。实测结果相当成功。由于每架E-15战斗机只能悬挂4枚这种炸弹,其爆炸威力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纵深,故阎雷等人决定一律将延期时间统一,并将延期信管的设定秒数定在6秒,以构成较为集中的杀伤面。
执行这种新战法的任务,本身就带有一种危险性。为了安全起见,拟参加这项任务的6架战斗机,全部在机身上漆上一圈白色腰带,无论在空中或是地面,它都向友机示警——危险!勿近!
空战经过
1940年8月11日上午,日本海军派出2架陆上侦察机飞至重庆上空侦察。随后,第一联合航空队鹿屋航空队的18架中攻机和高雄航空队的18架中攻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的26架中攻机、第15航空队的25架中攻机相继从汉口基地起飞,向西飞来。
12点18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发出日机来袭的警报。同一时间,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一批霍克Ⅲ战斗机7架,在第22中队副队长范金函率领下,首先从广阳坝机场起飞,升空迎敌。12点25分至13点45分,驻守白市驿机场的22架E-15、E-16战斗机又分3批相继起飞。其中,第一批E-15战斗机6架由大队长郑少愚亲自率领,每机悬挂4枚“浮游”炸弹,执行空中爆击日机的特殊任务;第二批E-15战斗机10架,由第21中队队长陈盛馨率领,在郑少愚等投下“浮游”炸弹后,即刻向日机群发动攻击;第3批E-16战斗机6架,由第24中队副队长龚业悌率领,再次向日机群发动攻击。
13点56分,两批日机会合,飞抵北碚,正准备以87架轰炸机组成的大编队同时进入重庆市上空投弹。突然,郑少愚率领郑松亭、王广英、柳哲生、高又新、洪奇伟驾驶的E-15战斗机出现在日机群的正前方,飞行高度比日机群约高20米。在距日机群还有两三百米的距离时,我机群投下了“浮游”炸弹,并迅速拉升脱离。炸开的弹片击中日机的机翼和机尾,在炸弹爆炸形成的气浪冲击下,日机飞行摇摆不定,一下就乱了阵脚。我方跟进的战斗机编队乘机向日机群发动猛烈地攻击。
关于这次空战的结果,次日发行的《中央日报》《国民公报》《新华日报》《新蜀报》等统一转载了“中央社”的通稿:
我空军□□大队长,亲率铁鸟□□架,以总攻姿态,向敌机迎头猛扑。敌机受我机数百挺机枪之压迫,受伤累累,全部溃散,各自夺路逃命。我机乘其纷乱之际,分头搏击,当即击落敌机5架,计坠落于石柱玉皇殿2架,丰都弹子台1架,涪陵白果铺1架,利川北郊1架。其余因受伤过重,沿途蹒跚挣扎,始终不能追随敌队者,计有6架。此等伤病败卒,无法归回老巢。残敌经此教训,当深悔不应孟浪犯我行都领空也。重庆市于下午3时30分发出解除警报,我空军除勇士兰锡芳1名略受微伤外,余均安全凯旋。
当然,在战争年代,新闻报道难免会有夸大之词,但“8.11”空战击落了日机确是真实的。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8月11日)》记载,“8.11”空战,我方击落敌机2架,一架落于石柱双庆乡,另一架坠落之地点待查。事后,坠落于石柱的这架敌机被我当地军民发现。另据1940年8月21日发行的《新华日报》报道:
八月十一日,敌机偷袭行都后窜返,有敌九六式双发动机重轰炸机1架,被我英勇神鹰击伤,下午六时五十分,坠落本县(指石柱)双庆乡六塘坝地面,登时油箱爆炸,机身全部被焚,机上敌寇有四人毙命,另有四人受伤,均被捕获。十二日晨,经该乡副乡长押解县府,由县长冯腾蛟亲讯,俘虏一人,略通华文,即用笔答,四人名衫野一助(日籍)、西泽次男(日籍)、大野敏夫(朝鲜籍)、加贺良平(日籍),刻已由县府派员医治,并予优待,俘获战利品计有航空军用地图一副,机枪三挺,手枪六支,测远镜,航法机算盘各一,护身符数十张。
战后,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二章第二节“对内地的空中攻击<一百零一号作战>”)、《中国方面海军作战》(第三章昭和十五年的海军作战),以及《中攻——海军中型攻击机》(岩谷二三男著)等战史书籍中,均记载了这次空战。《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关于“8.11”空战是这样描述的:
11日(指1940年8月11日),又用八十七架飞机攻击了重庆市中区。这天,二十八架敌战斗机出来迎战,出乎意料敌机投下用降落伞维系的浮游炸弹,以此办法进行防空。日方未因这一新战术遭到损失,但特别引起了注意。其结局是空战中击落敌机三架(其中一架未证实),日方也损失了一架。
另外,根据保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的《百一号作战之概要》记载,“8.11”空战,与我空军的飞机交火的分别有第一联合航空队的17架飞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的3架飞机和第15航空队的8架飞机。被中国空军击落的飞机属于第一联合航空队,而日方记载也击落我方飞机2架(其中一架不确定)。
从中日双方的资料印证,“8.11”空战,中国空军的确击落日机1架,并击伤日机数架。中国空军也损失了战斗机1架,是由第23中队飞行员温炎驾驶的编号为2328号的E-15战斗机。该机是追击日机群至石柱境内中弹后坠机的,温炎跳伞获救。在这次激烈的空战中,我机也有8架中弹,第21中队队员蓝锡芳肩部中弹,手指负伤。
雄鹰折翅
“浮游”炸弹战法在重庆上空的出现,给重庆主城区的市民带来了几天短暂的宁静。次日,曾参加“8.11”空战,并作为运用“浮游”炸弹战法成员之一的洪奇伟又挂弹升空,准备再次寻找日机决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今天警报较早,十点多我们便到机场去,十二点四十五起飞。我们仍然照昨天一样六架装炸弹,巡逻一小时许便落地加油。一时二十分(后)第二次起飞,我们这六架一直向南飞至南川、彭水一带拦截。我所驾飞机马力太差,跟都跟不上,把机群失掉。正想回头,便发现敌机一大批约五六十架,高度比我低,即开大油门拦截。谁知敌机见我机拦截,即变转航向,我越看越小,至后不见,只好扫兴而归。至重庆市上空,发现我机群乃跟上落地。今天敌机未敢进入市区,在郊外投弹,此定系我空炸给他的威胁也。
此后数日,日机一见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即掉头转弯逃避,不敢再入市区轰炸。直至8月19日,在新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日机才重新恢复对重庆主城区的轰炸。
“8.11”空战后,航委会对参加这次空战,击落、击伤日机的有功飞行员进行了嘉奖。阎雷因发明“浮游”炸弹和空中爆击日机群战法而立功。然而,“9.13”璧山空战后,中国空军完全丧失了对重庆的制空权。阎雷于当年底被调回昆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担任驱逐机(战斗机)组飞行教官。1942年6月4日,他在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实验新型延时炸弹时,不幸因飞机挂弹脱落爆炸而殉职,年仅24岁。
阎雷所在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10期共毕业学员125人,其中有27人在抗战中牺牲或殉职。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他在1941年3月14日的成都双流空战中,遭遇日军零式战斗机攻击而阵亡。与阎雷同期的官招盛、许晓民、黄光润、杨天雄则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牺牲或殉职。他们牺牲后,被葬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