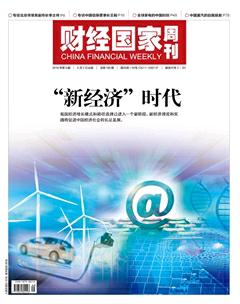“资产短缺”视角下的全球经济
周莹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降,对全球失衡以及中国角色等问题的理论研究已成潮流。在诸多前沿讨论中,一种以“资产短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应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对深度研究和观察中国与全球经济互动的分析人士而言,意味着一个新的视角和有解释力的工具。
假说来源和基本阐述
从目前公开资料看,“资产短缺”的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系卡巴莱罗教授在2006年的《资产短缺的宏观经济学》中提出,而后随着金融危机等的发生和演进又不断修正和丰富了相关内容。近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关注资产,特别是“安全资产”的短缺问题,并在其《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多次提及。在国内,南京大学范从来教授等也在相关理论研究中涉及该问题。
卡巴莱罗教授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全球存在着资本的实体经济生产能力(包括产出各类有形产品等)和创造金融资产(包括债券、股票等)的能力不匹配的情况。

“资产短缺”假说对“全球失衡”、“利率之谜”以及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等有比较强的解释力。
由此,其将世界主要经济体划分为三类: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特点是较好地将实体经济生产能力与金融资产创造能力结合在一起。其提供的优质且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吸引了全球投资者,比如美国政府债券。
二是以新兴市场和石油生产国为代表的经济体。特点是经济增速快,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缺乏足够的优质金融资产。
三是以欧洲和日本为代表的中间层经济体。特点是增长有限,提供金融资产的能力落后于一类经济体,增速落后于二类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等在资产问题上无法“自给自足”,其原因有正反两方面:相对正面的因素包括储蓄率高企、金融业的迅速发展、改革创新等带来的经济活力、居民收入增长以及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等;负面原因则包括薄弱的破产程序,长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信用风险等。正面因素带来旺盛的资产需求,而负面因素造成资产供给不足,从而带来“资产短缺”问题。
“资产短缺”视角看国际经济问题
“资产短缺”假说对“全球失衡”、“利率之谜”以及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等有比较强的解释力。
比如,新兴经济体等对美国安全资产的高涨需求,导致这些资产的名义价格上升并强化了其所谓的“安全”,这进一步带来更多外部投资需求,形成一个正向循环。要保持长期稳定增长,需要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因此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外资涌入追逐安全资产造成资本项顺差的情况下,贸易项会长期保持逆差状态,形成“全球失衡”局面。
又如解释“利率之谜”,即美联储在一段时期不断上调短期基准利率,却没有拉动长期利率跟随上升的反常现象(一般而言,由于时间越久,不确定性因素越多,所以反映风险溢价的长期利率会高于短期利率,且短期利率上调后,长期利率将跟随上涨),可以认为是新兴经济体因为资产短缺大量购买美国长期国债,抬升其价格,从而压低其利率(债券利率与价格成反比)。
再如,次贷危机的形成,也可以解释为全球资金追逐美国资产,使得该国金融机构有动力创造衍生品,将各类信用风险高的资产和相对安全的资产打包混合,再加上评级机构等推波助澜,以对接市场需求,从而形成深广的系统性风险。
除了分析解释以上一些重要经济金融现象,“资产短缺”假说还通过对资产供应端的分析,提出了在较长时期内弥补这种短缺的三个机制:一是经济体内部的资产名义价格持续上升,出现投机性的资产泡沫;二是折现利率(以实际利率为代表)将长期下滑,以增加现有资产的基础价值;三是通胀下滑甚至通缩,从而导致债券类系统风险系数更小的资产价格上升,即一种庇古效应。
若用“资产短缺”假说分析中国经济
“资产短缺”假说中涉及的一个重要资产需求方就是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体量最大。近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些类泡沫现象,比如房地产、股市、收藏热,乃至“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假说。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即一个国家只要处于资产短缺阶段,就易出现资产泡沫(第一种弥补缺口机制),投机性估值是资产供求平衡的一部分,其存在有合理性。
另外,如果监管部门试图刺破泡沫(即强行抑制第一种弥补机制发挥作用),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上述第二种、第三种机制显现甚至强化,也就是利率下行或长期通缩,或者两者皆有。
如果考虑到通缩等带来的经济代价可能更大,那么允许资产泡沫一定程度存在时又需要注意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资产短缺”假说的卡巴莱罗也有所分析,他认为泡沫集中在非资源消耗类的经济领域可能会更好,比如在金融资产,而不是工业生产部门。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引发的思考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的产能过剩是否是“资产短缺”的一个表征?其负面影响是否更大?
再者,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经济是否已经从过去的“产品短缺”进入到“资产短缺”的新阶段。在“产品短缺”时期和在“资产短缺”时期经济运行方式和规律或存在很大区别,相关的宏观调控及政策着力点似乎也应有所不同。
从更长久的解决之道上说,大力深化金融改革,发展金融市场,提供更多金融资产应该是一个主要努力方向。此外,从全球范围看,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等,是对己对人都有利的事情,应大力推进。这一方向或可以缓解全球资产需求“死磕”美国的困局,减少“资产短缺”负面效应,从而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为外交及经济政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