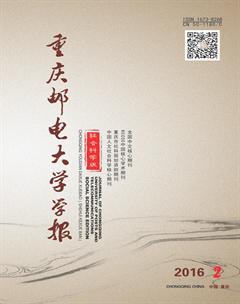白居易治水动因及机缘论考
摘要:文章续《论白居易与水利建设》一文,从天道无常、守土有责、得道多助及心怀仁爱等方面,考察分析了白居易治水的动因及机缘,发现乐天青年时期的灾荒遭际,使其对民生有了深切同情;中唐时期江淮水利的长足发展,让他在苏杭治水有势可借;当然,最可宝贵的是乐天有志治水,为此他的行动得到了各方帮助。这一切促成诗人在惨淡的中晚唐,居然倾其所能终将自己的禹功蓝图变成了现实。诗人的赤子之心、爱民情怀永远鲜活,他的水利事迹和诗文一样会永远不朽。
关键词:唐代文学;白居易研究;水利建设;动因机缘
中图分类号:TV21209;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2012407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大诗人中值得尊敬的水利专家,在风雨飘摇的中晚唐,他立志治水,“为唐水官伯”[1]卷8:429,成功做了三个水利工程,一是治理杭州西湖,二是疏通苏州山塘河,三是开得龙门八节滩。他的治水事迹及在当时的影响,笔者曾在《论白居易与水利建设》[2]159一文中进行过详细论述。本文拟从天道无常、守土有责、得道多助及心怀仁爱等方面,进一步对白居易治水的动因及机缘作考察分析,以此窥探这位诗名大于政声的前贤“唯人瘼是求”、忧念民生的心路历程与抱负。
一、天道无常,安民救灾需治水
有学者曾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等史籍,对唐代水旱灾情进行过统计:唐季289年,约有138年发生过程度不同的水灾,占总年份的48%;有114年发生过旱灾,占总年份的39%[3]。白居易所生活的年代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乐天10岁前一直生活在河南新郑。11岁开始颠沛流离,曾随父游宦徐州、衢州、襄阳;还因两河用兵,逃难越中;旅居到达苏州、杭州、浮梁、宣州;曾寄家符离,后移家洛阳;应试到长安,29岁考中进士。从建中三年(782年)到贞元十五年(799年),共计18年时间,乐天当时年轻,功名未就,活在民间,未染庙堂气息,对民间疾苦体会较深。比照各类史料可发现,在他青年时期的这18年间,除建中四年(783年)、贞元五年(789年)、贞元九年(793年)无事外,其他15个年份非涝即旱。当然,这期间除旱涝无常外,还时遇蝗灾,且兵祸不断,闹饥荒就不可免。
先看白居易兴元贞元之遭际。陈寅恪曾讲道:“考贞元元年乐天年十四,时在江南,求其所以骨肉离散之故,殆由于朱泚之乱。而兴元贞元之饥馑,则又家园残废之因。”[4]先生的推测与史实大体吻合。建中三年(782年),乐天为避两河兵乱,离开新郑到其父白季庚徐州官舍。次年十月,泾原兵变,天下大乱,再下一年即兴元元年(784年),人祸未了,天灾继起,饥荒来临,“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5]卷37:1365,“冬,大旱”[6]卷35:917,灾情波及宋亳、淄青、泽潞、河东等八节度,“蒸民饥馑”[5]卷12:347,徐州紧邻宋亳,自然在劫难逃。贞元元年(785年),灾情依旧严重,“夏,蝗尤甚”,“饿馑枕道”,“(京师)衣冠之家,多有殍殕者。旱甚,灞水将竭,井皆无水”[5]卷37:1365,加上白季庚此年有秩满移官之虞,乐天被迫逃离徐州,到南方投靠于潜、乌江的亲友(白氏有诗云“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兴元贞元之饥馑”一直持续三年时间,到贞元二年(786年)五月才让天下人看到了活命的希望。眼看有新麦可食,谁知道又现波折,“是时民久饥困,食新麦过多,死者甚众”[5]卷12:353。
再来研究白氏贞元六年(790年)遭遇的又一场灾难。贞元四年(788年)白季庚从徐州别驾迁官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乐天从亲友家移居官舍,暂时有了坚实依靠。但是好景不长,到贞元六年(790年),一是白季庚又面临秩满离职,二是此年春夏再遇天旱,史料称“春,关辅大旱,无麦苗”[6]卷35:917,“(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5]卷13:369,南方灾情更为严重,旱灾瘟疫,两害相加,死者甚众。衢州处浙东道,恰在重灾区,生死事大,乐天被迫向北逃回徐州符离。七年前自北而南,七年后从南到北,千里迢迢的逃命生涯,真是难为了少年白居易。更可怕的是,这样的苦日子根本不知道何时才到尽头!
接下来说白氏贞元十三年(797年)至十五年(799年)的遭际。贞元七年(791年)白季庚除襄州别驾。贞元八年(792年)秋,江淮、荆、襄、徐、郑等40余州发大水,九月乐天小弟金刚奴染疾夭折,草草安葬小弟后,他伴母亲从符离逃难到襄阳,从灾区到灾区,沿途所见皆为水毁之惨状《旧唐书》卷37,《志第十七·五行》第1359页记载:“八年秋,大雨,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馀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馀人。时幽州七月大雨,平地水深二丈;鄚、涿、蓟、檀、平五州,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又徐州奏:自五月二十五日雨,至七月八日方止,平地水深一丈二尺,郭邑庐里屋宇田稼皆尽,百姓皆登丘塚山原以避之。”《新唐书》卷36,《志第二十六·五行三》第932页记载:“八年秋,自江淮及荆、襄、陈、宋至于河朔州四十余,大水,害稼,溺死二万余人,漂没城郭庐舍,幽州平地水深二丈,徐、郑、涿、蓟、檀、平等州,皆深丈余。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 。贞元十年(794年)五月,白季庚襄阳任上撒手西归,留下寡母孤儿无依无靠。乐天无力运走父亲灵柩,只得就地暂时安葬,随后护送家人回符离,途中有诗云“家贫忧后事,日短念前程”。白家老少死无所葬,活人生活处境更是雪后加霜。白氏兄弟在贫苦中按礼持丧三年。贞元十三年(797年)又遇旱情,“夏四月壬戌,上(指德宗)幸兴庆宫龙堂祈雨”[5]卷13:385。贞元十四年(798年)旱情加重,民不聊生,朝廷接连开仓放粮,以救饥荒,“(六月)出太仓粟赈贷”,“(十月)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开场糶以惠民”,“(十二月)出东都含嘉仓粟七万石,开场糶以惠河南饥民”[5]卷13:388389。贞元十五年(799年)春再旱,民间饥荒依旧,朝廷被逼无奈,除放粮外也减省开支,与民共渡难关。史料称,此年二月朝廷先后“罢中和节宴会”、“罢三月群臣宴赏”,并“出太仓粟十八万石,糶于京畿诸县”[5]卷13:389390。
白家为度大饥荒,采取自救措施。先有长兄白幼文约于贞元十四年(798年)春赴任饶州浮梁主薄,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乐天随后出门找出路。他带家人到洛阳投靠亲友,然后独自南行浮梁投奔长兄,在宣州参加秋试。贞元十五年(799年)春因旱情饥荒未了,他又从浮梁负米返洛阳。其间的苦痛与辛酸有诗文可证,如散文《伤远行赋》云“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诗作一《将之饶州江浦夜泊》云“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诗作二《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又云:“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以上所叙三次跨年大旱饥荒,皆使乐天心有余悸。到元和年初(805年),他对早年的苦难依旧记忆犹新,有诗云:“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这从心理学来看,无疑会让他对民众民生深怀同情。长庆二年(822年)七月白居易除杭州刺史,闰十月穆宗有诏书云“江淮诸州旱损颇多”[5]卷16:500;三年、四年江淮相继再旱,《新唐书》云,“(三年三月)淮南、浙东西、江西、宣歙旱”[6]卷8:226,乐天作文自云“去秋愆阳,今夏少雨,实忧灾沴,重困杭人”[1]卷40:2671,“余在郡三年,仍岁逢旱”[1]卷68:3669。史料对长庆二年(822年)杭州所在区域的饥荒也有记载,“长庆二年,江淮饥”[6]卷35:899,“(十二月)淮南奏和州饥,乌江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5]卷16:501,说明当时江淮旱荒非同一般。白居易可谓临危受命,身负重托,为缓解旱情,他曾为求雨“历祷四方”[1]卷40:2673。宝历元年(825)三月,白居易除苏州刺史,秋遇旱灾,史料称“秋,荆南、淮南、浙西、江西、湖南及宣、襄、鄂等州旱”[6]卷35:917,苏州恰在浙西;乐天有诗云,“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诗史互证,灾情确实不假。他眼见百姓深陷苦难,自己早年的遭际又在民间重演,岂能坐视不理。
由此可见,白居易苏杭治水动机即在抗旱救灾安民上。长庆四年(824年)五月,他离任杭州时曾有诗云:“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诗后自注“今春增筑钱塘湖堤,贮水以防天旱。”[1]卷23:1564
二、守土江淮,随势兴水勇担当
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唐代继秦汉之后再掀水利热潮。唐代水利建设情况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系统研究。屈弓先生在冀朝鼎、邹逸麟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得出的水工程统计结果为407项[7],这样的水利建设规模确实前所未有。单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根据冀朝鼎所制《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表》[8]可知,该地区春秋至隋共建水利工程64项,另有学者统计出该地区唐代共建水利工程104项[9],也就是说,唐季近三百年之所为已远超此前的千年积累。
白居易处中晚唐时期,长庆、宝历年间先后除苏杭刺史,这个时期唐代南方水利发展较快。唐代水利发展情况,一般认为以安史之乱爆发为界,前期业已形成一个高潮,发展重点主要在关中,其次是河南、河北和河东道及西北边区;天宝之后,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发,加上气候变迁等,迫使唐王朝经济依托南移,水利关乎国运,加快发展成为必须。先来看淮南道,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该道共有12州53县,经逐项统计,唐代共建水利工程15项,中唐前4项,中唐后11项(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工程在不同时期重建或重浚,需要分别作计,这是学界通用算法)。中唐后属长庆年间兴建的有5项,主要集中在楚州淮阴郡境内,史料称“(宝应)西南四十里有徐州泾、青州泾,西南五十里有大府泾,长庆中兴白水塘屯田,发青、徐、扬州之民以凿之,大府即扬州;北四里有竹子泾,亦长庆中开”,“(淮阴)南九十五里有棠梨泾,长庆二年开”[6]卷41:1052。江南道(51州247县)也值得一说,按同样的方法统计,唐代共建水利工程76项,中唐前27项,中唐后49项。其中,杭州12项(前6后6)、越州11项(前4后7)、泉州10项(前7后3)、湖州6项(前2后4);此外,中唐前为零,中唐后有积极作为的分别是江州(4项)、饶州(4项)、歙州(3项)、洪州(3项)、宣州(3项)、福州(3项)、常州(2项)和苏州(2项)等。综合两道的情况看,唐代在江淮大地共建水利工程91项。其中,中唐前31项,中唐后60项。我们还可把关注范围缩小,定焦于浙西地区。浙江西道乾元元年(758年)初置,领升、润、宣、歙、饶、江、苏、常、杭、湖10州,此后宣、歙、饶、升、江等时而罢领、时而复领,这里为方便统计,以初置范围为准。唐代该地区共建水利工程42项。其中,中唐前13项,中唐后29项,是前期的2.23倍。由此可见,中唐以后,南方尤其是江淮水利,发展势头强劲,速度大超前期。
白居易任官的苏杭皆在浙西,又处运河沿线,是江淮的核心区域,其战略意义非同小可。“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10]卷63:677,“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10]卷555:5612,“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6]卷165:5076,“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带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国之虚盈,于是乎在”[10]卷534:5422。乐天任官两地时,深知重任在肩,“江南列郡,余杭为大”[1]卷55:3194,“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1]卷68:3672,他必须考虑水利建设以夯实发展基础,因为苏杭的赋税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用度。
由此可见,白居易苏杭治水,乃随势而为、借势发力,大的形势需要他有所担当。
三、得道多助,禹功蓝图成现实
唐代距今一千余年,限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兴水困难尤多。就人力组织而言,征发民夫群体劳作,动辄成千上万人。以大和七年(833年)河阳修防口堰为例,役工达四万之多[5]卷17下:550。水利建设对治水者的要求也甚高:一要有志治水,不避艰辛;二需熟谙水情,知晓地质;三需有较强的统筹调度、指挥协调能力。当然,最关键的是要得到朝廷支持。唐代水利建设不论水部还是地方官员,都不能想当然大兴土木。其管理机制概括来讲为“中央总举,地方自营”[11],一般须先奏请朝廷知悉,再由朝廷派人检覆,确认无误以后才会诏许动工。西湖工程是白氏亲自策划指挥完成的头个水利项目,在当时及后世都颇有影响,以下重点围绕它展开论述,探究白居易的兴水事宜在规划运筹与实施环节都受了哪些人的启发与帮助,并最终推动他的德政工程成为现实。
第一,研究认为乐天杭州兴水念头的产生,最主要受了挚友张籍的启发和指点,张籍随后全程关注西湖工程到完工。贞元十五年(799年)张籍登第,次年乐天登第,知贡举者皆为高郢。“登第早年同座主,题诗今日异州人”[12],即表明二人师属同门。长庆二年(822年)春,张籍除水部员外郎,白居易撰写制书,并专门赋诗表示祝贺,“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不久江淮闹饥荒,灾情严重,白居易于七月身负重任,翻秦岭走蓝田武关驿道赴任杭州,八月初过河南内乡县,与巡视水利与漕运[13]回长安的张籍相遇。乐天喜而赋诗云:“旅思正茫茫,相逢此道傍。晓岚林叶暗,秋露草花香。白发江城守,青衫水部郎。客亭同宿处,忽似夜归乡。”这同宿客栈的经历实在大有文章,一位是钦差水务大臣,一位是赴旱荒的刺史,水利必是当晚的重要话题。两人分手后,乐天继续南下,对兴水治水可谓踌躇满志,这与他初罢官及刚出长安部分诗篇所载的心态迥异,《初罢中书舍人》云“命薄元知济事难”,《初出城留别》云“我生本无乡”,《商山路有感》云“此生都是梦”。他在汉江边登舟改走水路时,还特地赋诗寄两省给舍云,“尚想到郡日,且称守土臣。犹须副忧寄,恤隐安疲民”。两省即门下省和中书省,此时寄诗其间友朋,已不单是抒发闲情,而是提前告白,希望守土杭州大家务必要给力。
白居易登舟汉江,并没有随水直达鄂州,而是过郢州改走漕运道,至江陵进入长江水路。过洞庭湖口时,乐天激情澎拜,豪情万丈赋诗一首,题为《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立下了他此去杭州治水安民的宣言:“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河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王拾遗1983年5月版《白居易传》认为此诗系元和十五年(820年)乐天从忠州返长安时所作[14],其1957年3月版《白居易》则认为此诗系长庆二年(822年)乐天赴任杭州途中所作[15]。先生早年之说倒是对的,晚年之修正却忽略了唐时荆襄水运线路,而且也不合理,乐天歌诗合为事而作,元和十五年(820年)他断不会无端说水利。
乐天到任杭州后,与张籍联系不断,且多有诗作往还。长庆四年(824年)夏张籍罢水部员外郎,乐天五月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由此还可以推知:白氏西湖水利,张籍自始至终给予了关照。
第二,研究认为李渤在江州修筑甘棠湖一事,给了乐天杭州兴水以规划运筹方面的启示和见习机会;此外,或许李渤与张籍一样,皆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在白氏西湖水利的朝廷审批环节提供了帮助。从第一层意义上讲,江州真是乐天的福地,元和年间被贬官,江州接纳了他;如今去杭州治水,江州甘棠湖启发了他。事情是这样的:乐天在洞庭湖口立下治水宣言后,继续放舟东下到达江州,受到好友李渤刺史热情接待。由于是故地重游,乐天特意在江州多盘桓数日,并登庐山看了昔日自己所建的草堂。在江州期间,乐天与李渤多次会面。两位刺史在水利建设上有许多共同话语,因为李渤当时正运筹兴水,史料云“(浔阳)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6]卷41:1068,李翱《江州南湖堤铭(并序)》记录此事更详实,工程地点、起止时间、规模大小、工程效应都一一指明,“长庆二年十二月,江州剌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筑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广若干尺,以通四乡之路,畜水为湖,人得其赢。正月既毕事”[10]卷637:6427。乐天的江州故地游,恰在甘棠湖开工前,李渤定是把规划运筹方面的一切都倾囊相授了。
至于白氏西湖水利的朝议审批,李渤可能也曾给力相助。李渤完成甘棠湖工程后,次年(即长庆三年)(823年)春即被召回京师,任职理匭使谏议大夫,长庆四年(824年)七月他依旧在任[16]卷55:957。理匭使专门负责处理各种请事投状文书,匭置庙堂者有曰“青匭”的,其间所投文书专门用以“告朕(指皇上)以养人及劝农之事”[16]卷55:956。白氏西湖水利文书若走该路径上达天听,李渤必然相助。
第三,研究认为白居易任职苏杭时,他的水利事务在运筹与实施环节,还得到了上司李德裕的大力相助。因为牛李党争,乐天与文饶的关系渐渐疏远,但他们也绝非死对头。他与牛僧孺、李宗闵关系甚洽,而他的挚友刘禹锡、元稹皆与李德裕相交颇深。乐天任职苏杭时,李德裕均在浙西观察使任上。“观察使以丰稔为上考”[6]卷49下:1310,乐天兴水安民救饥荒与文饶的政绩密切相关,按常理文饶不会阻碍他开展政务。乐天在苏杭两地,与文饶各唱和一次,杭州诗为《奉和李大夫题新诗二首各六韵》,苏州诗为《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 和浙西李大夫作》。这是乐天诗集仅存的两首对文饶唱和的诗,恰能证明此期间二人皆能放下恩怨一心向公,关系相对融洽。至于收入《白氏长庆集》中有争论的《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宋代苏辙、近代岑仲勉等皆已指出是伪诗。岑仲勉引苏辙语:“至其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刻覈尤甚,乐天虽陋,盖不至此也。且乐天死于会昌之初,而文饶之窜在会昌末年,此决非乐天之诗,岂乐天之徒浅陋不学者附益之耶?”[17]。苏辙的辨析有瑕疵,乐天离世在会昌六年(846年)八月,文饶当时任荆南节度使,九月为“东都留守”[18]卷248:1710,后任“太子少保”[18]卷248:1711,贬崖州司户在“大中二年(848年)九月”[19]。按照老算法,大中二年离会昌六年已三年。由此可见,《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确为居心叵测之小人托名乐天所作的伪诗。
第四,研究还认为白氏西湖水利项目送达朝廷议决时,乐天朝中的友朋,尤其是其时贵为宰相的杜元颖、牛僧孺给予的帮助很大,因为“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6]卷46:1182,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议决政事时说话分量不轻。白居易长庆四年(824年)春完成西湖治理工程,奏请朝廷批准及筹备工作当在长庆三年(823年)进行。杜元颖长庆元年(821年)二月拜相,三年十月罢相;牛僧孺三年三月拜相,宝历元年(825年)一月罢相。杜白二人贞元十六年(800年)同登进士,大和七年(833年)乐天有诗自注云,“(余)与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1]卷31:2100,循州杜相公即杜元颖,既然是同年及第,皆出主考官高郢门下,关系自然非同一般。牛白二人有师生情谊,关系更特殊。大和六年(832年)僧孺任淮南节度使,赴扬州路经洛阳拜会白居易,乐天赋诗云“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并加自注“元和初牛相公应制策登第三第,予为翰林考覆官”[1]卷31:2104。僧孺嗜石,乐天晚年为其写《太湖石记》。长庆四年(824年)西湖工程完工,乐天罢杭州,诗寄僧孺求分司,得遂所请。连私事都能相助,况白氏西湖工程乃德政也。
四、心怀仁爱,晚年犹开八节滩
白居易的思想研究向为白学重镇。一般认为,就其思想接受来源讲无非受儒道释三家之影响。但是,具体情况如何呢?不同研究视角自有不同的结论。王拾遗认为,“(乐天)壮年是儒家思想为主,佛、道思想次之;中年是儒、佛思想为主,道家思想次之;晚年是儒、道思想为主,佛家思想次之”[20]。贺秀明认为,“(乐天)始终以儒家思想为主”[21]。肖伟韬认为,“儒家思想才是其生命的底色和根本,中晚年投入释、道信仰的境域,只不过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白居易的生存哲学而已”[22]。马现诚认为,乐天思想存在儒道统一、儒释统一和释道统一,“三层内容虽各有所重,但它们有一个交叉点,就是‘有所为”[23]118。以上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共同点在于,肯定儒家才是乐天思想的根本与底色,释道融入也不改其“有所为”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生于唐季,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精熟儒家经典,受其影响是必然。当然,以儒为本的家世也有潜移默化之功。乐天祖父白鍠“年十七,明经及第”,父亲白季庚“天宝末明经出身”。这说明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动摇。至于佛道思想,在乐天那里与儒家思想是融合的,并不冲突。先看儒道之融合,马现诚阐释说,儒道产生千百年来,各自在对现实的人生态度以及治世的方略上,观点不一,争鸣不休,“但从社会观及社会理想角度看,其所追求达到的最高理想社会状态在本质上具有相互交会的契合点,如使乱世达于治,国富民殷,世俗清和,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23]116。再来看儒释之融合,马现诚引乐天自己的言论,指出他“将王道与佛道相提并论”[23]116,意即不矛盾不冲突。乐天的精彩言论,一是《三教论衡》云:“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1]卷68:3676二是《策林四·议释教》云:“(释教)大抵以禅定为根,以慈忍为本,以报应为枝,以斋戒为叶。夫然亦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1]卷65:3545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体现思想。从白居易年轻时志在兼济、拯时安民的情怀,以及除忠州刺史开始施行的善政善举来看,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确是贯通始终的,佛道也支持他“有所为”。苏轼曾著文盛赞乐天:“忠言嘉谋,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24]此段妙语涉及乐天的思想、情怀、文采和美德,因非专论,自然未涉善政善举。单从水利建设上讲,白居易治理杭州西湖,疏通苏州山塘河,是在躬身践行儒家民本、德政、仁政思想,是在身体力行“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上》),他明知水利建设复杂艰辛、劳心劳神,时间短任务重,却能“知其不可为而为”(《论语·宪问》),而且善始善终。你能说其间没有“以慈忍为本”的佛家思想和主张使民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25]的道家思想成分吗?同样,也正因为有儒道释的融合,白居易到了晚年,尚书致仕,不管政事,皈依佛门,与僧人往来、研读佛典、持斋坐禅等成为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他还坚持在现实中行菩萨善举,除了捐钱重修香山寺,还施财“开得龙门八节滩”。就会昌四年(844年)成功开凿八节滩一事,乐天自云:“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1]卷37:2550这里所谓“适”有道家的“安适”、“顺适”意味,而“功德福报”是佛家的,除了这些难道就没有其他了吗?好一个“岂独以功德福报为意哉”,这话问得真是意味深长。
对于白居易晚年“开得龙门八节滩”还有必要多说几句。笔者曾著文指出这个工程不一般,“在这一工程中我们司空见惯的官府主体没有了,白居易的行为纯粹类于今日所见的志愿者行动,是大善举大慈悲,是真正的大爱行为”[2]165。正因为不一般,所以影响大,此善举作为典故多见于后世的佛典和诗文里,甚至远播海外。这里承接拙作附记两首高丽、朝鲜时代士人的诗作为证:一是李仁老(11521220)的《崔太尉双明亭》云:“醉吟先生醉龙门,八节滩流手自凿”[26]44;二是李退溪(15011570)的《郡斋移竹》云:“樱桃杨柳搃莫污,晚岁飘然八滩曲”[26]49。
综上所述,白居易一生忧念民生,主要有天道无常需人力拯危,国用依托需随势而为,其行本善得道多助等方面的原因,成全了他化禹功梦想为现实。其中,最可珍贵的是他抱持终身的爱民情怀。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27],诗人自身尚且生活困窘,竟然能够在绝境中推己及人心念苍生,其胸襟与气魄无疑是伟大的。白居易也毫不逊色,类似诗作多达三首,一是元和年间所作《新制布裘》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二是长庆二年(822年)所作《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云:“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三是大和五年(831年)所作《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笔者在此无意将两位诗人作高下之分,因为就高尚的品德而言他们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先后,人生际遇不一,各自伸展的抱负也就有所不同。让人欣慰的是,白居易反复用象征物“大裘”取代杜甫之“广厦”,这是在做诗艺创新,此外乐天还将自己的忧念民生付诸行动,传承和发扬杜甫仁爱精神,实现前贤未竟之抱负,最终通过水利建设将抽象“大裘”变现成真正的贴身之物,并实实在在造福了民众。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朱金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谢祥林.论白居易与水利建设[J].农业考古,2014(6).
[3]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48.
[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7.
[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103.
[8]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6.
[9]陈勇.论唐代长江下游农田水利的修治及其特点[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112.
[10]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张弓.中国古代的治水与水利农业文明——评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论[J].史学理论研究,1993(4):21.
[12]张籍.张籍诗集: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56.
[13]罗联添.唐代诗文六家年谱·张籍年谱[M].台北:台湾学海出版社,1986:213.
[14]王拾遗.白居易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179180.
[15]王拾遗.白居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07.
[1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7]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483.
[18]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9]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58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281.
[20]王拾遗.白居易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96.
[21]贺秀明.刘禹锡白居易晚年老病、奉佛诗之同异[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95.
[22]肖伟韬.白居易《论语》《孟子》思想论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109.
[23]马现诚.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及与儒道佛的交融[J].学术论坛,2005(1).
[24]苏轼.苏轼文集:第11卷[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45.
[25]老子.老子译注[M].冯达甫,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74175.
[26]金卿东.高丽、朝鲜时代士人对白居易的“受容”及其意义[J].文学遗产,1995(6).
[27]杜甫.杜甫诗[M]. 傅东华,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