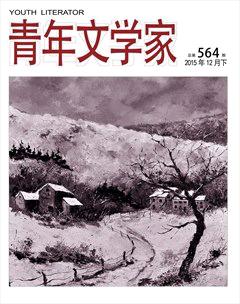人性的沉沦与救赎:试论《九三年》与《双城记》的主题
摘 要:《双城记》和《九三年》分别是狄更斯和雨果晚期的作品,两位作家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激烈残酷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对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复杂性予以剖析,刻画了朗特纳克、郭文、马内特、卡顿等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借由他们从人性的沉沦走向救赎的命运,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呐喊,表达了对至纯至真的人性的呼唤和赞美。
关键词:《九三年》;《双城记》;人性;救赎;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杜丹,女,1990年7月出生,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目前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05
《九三年》和《双城记》分别是雨果和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两部作品生动地表现了黑暗的贵族统治和受迫害的下层人民之间的尖锐冲突,揭示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根源,表达了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另一方面两部作品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大革命过程中过度的暴力和血腥,前者强调无阶级的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看做人类最高的理想;后者则以爱与温情、无私奉献为核心,提出阶级调和的主张。作家把自身对于人性的思考贯穿在人物的命运中,使笔下的人物在极端的复杂的环境下面对人性的拷问,作出艰难的选择,从人性的沉沦中走向救赎,最终回归到人道主义精神的道路上。
一
雨果和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拥有相同的基本态度。在小说中,他们都深入描写到黑暗的贵族统治和受迫害的下层人民之间尖锐的冲突,表达出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肯定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1793年是法国革命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斗争最严峻的一年。法国保王党巢穴——旺岱省爆发了大规模叛乱,这年六月建立起的雅各宾派专政采取有力措施,实施红色恐怖政权,于七月派军队镇压叛乱,《九三年》正是以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展开叙述。
作品一开始便肯定了人民革命的正义性。在一片阴森的树林里共和军正在搜索敌军,林子深处有一个奇怪的女人,她穿着单薄,袒露半边乳房,拥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傻傻地坐在树下。很快农妇被发现了,在与几个军人对话时我们知晓了她极其凄惨的经历:她的丈夫战死,因为领主需要他作战;她的父亲因为猎了一只兔子变成残废,还要感激爵爷开恩赏他一百棍子而没有判死刑;她的公公为谋生计贩私盐被绞死,只因为是国王的命令;她的祖父被关到船上做苦工,只因为是个新教徒;而这妇女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只能带着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逃难。人们同情这个女人更仇视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贵族和国王,腐朽的社会,黑暗的政权。农妇的形象折射出法国社会的黑暗现状,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贵族统治的专横无道,过于深重的苦难终将使人民奋起反抗,人民进行革命是正义的,是必然的。
与雨果所持的基本态度一致,狄更斯也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革命运动。在《双城记》里,作家以巴黎和伦敦为主要场景,着重表现了法国社会的黑暗统治和人民深重灾难的多个侧面:贵族的典型代表埃弗雷蒙德侯爵张扬跋扈,他的马车撞死无辜的小孩,他却无动于衷,扬长而去;他年轻时霸占农家妇女,为达目的逼死她全家;了解事情经过的马内特医生为伸张正义写信揭发他的罪行,不料信被侯爵截获,马内特因此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十八年;德法日夫人是当年惨死的农妇的妹妹,她将仇恨暗藏在心里,把贵族多年来的暴行一一编织记录起来,等待着复仇的机会;与德伐日太太类似的广大工人农民也都早已对贵族统治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他们每日都怀着满腔仇恨,紧咬着牙关,只等待一个爆发的时刻。山雨欲来风满楼,复仇之花已经在阶级仇恨的温床上悄然发芽,贵族的专制荒淫和人民饱受的苦难为大革命找到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二
但是雨果和狄更斯都是人道主义者,在肯定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大革命的残酷和暴力,革命的胜利不是人道主义的胜利,相反,以暴制暴带来的是新一场血雨腥风。作家把目光转向在极端的斗争环境中暴露出的人性弱点,使得笔下的人物们充满矛盾性,他们的命运轨迹正是人性中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的交战。
雨果在《九三年》中塑造了朗特纳克这个集恶与善于一身的形象。叛党领导人——亲王朗特纳克在旺岱执行秘密任务时被革命党抓获,但是他却在紧要关头放弃绝佳的逃跑机会,不顾生命危险在大火中冲回碉堡救下三个命在旦夕的孩子。雨果在小说中并没有详细描写朗特纳克之前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通过小说中人物出场时萧杀阴冷的环境描写,以及寥寥几笔革命者对这个叛党头子的深恶痛绝,读者不难在潜文本中为朗特纳克安上狠毒,冷酷等等贬义的标签。雨果将这样的人物置于生死面前,着墨于他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他做了与自己的身份和一贯作风大相径庭的决定,放弃逃生而救孩子。那一刻“魔鬼身上的上帝”[1]苏醒了,孩子的纯真唤醒了朗特纳克人性中善的力量,使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做出了舍己救人的壮举。在昏暗的地牢中,孩子纯洁的心灵净化了朗特纳克心中的恶,这一场大火仿佛烧毁了人间的罪恶,使朗特纳克浴火重生,从人性的沉沦走向被孩子救赎和自我救赎的路程。
作家接着把一个难题抛给小说的主人公即革命者郭文,应不应该杀朗特纳克?郭文在沉思:
“人们怎样办呢?”
“接受他的头颅。”
“朗特纳克侯爵要在别人的生命和他自己的生命之间做一个选择,在这个庄严的选择中,他选择了自己的死亡。”[2]
于是郭文很快对革命产生了怀疑:
“对于英雄的行为,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报酬啊!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的行为!革命居然也有这种弱点!”
“正当这个充满着成见和奴役思想的人突然转变,回到人道主义圈子里来的时候,那些为了解放和自由而战斗的人们却仍然继续内战,仍然维持流血和兄弟自相残杀的常规!”[3]
他的这番激烈的内心斗争表明:郭文是一个战士,但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觉得革命的方式不应该是野蛮的,残暴的,革命不是为了抹杀人性,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充满爱和自由的国家。最本真的人性是美与善的化身,却常常被世俗的斗争深深掩埋,往往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才得以重现。雨果就是要一次又一次在生死关头拷问人性,让人物作出选择。郭文不愿碍于革命者的身份,违背内心,处决这个舍己救人的英雄,在革命与人道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人道主义,最终放走了朗特纳克,甘心用自己的头颅换取侯爵的生命,人性的伟大在这一刻彰显。小说中的另一位革命者西穆尔登是郭文小时候的家庭教师,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为了维护革命“绝不放过,绝不宽恕”的铁纪,他选择了绝对的革命道路,却又在郭文死后悲痛万分,开枪自杀。他的矛盾和痛苦最终通过死得到了救赎。小说中反复提到“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4],在这里正确的人道主义也就是指革命不能违背天理、人性,如果为了反抗非人道的统治而使用非人道的革命手段,革命就不再具有正义性,就会沦为被人道精神讨伐的对象。“丑恶的人类法律不得不在永恒的美丽面前现出原形”[5],只有人性的美与善才是永恒的美丽,三个人物在生死面前的选择凸显出一条真理:用人性中善的一面来化解罪恶,恕字,才是人类最美好的字眼。
同样的,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也表达了赞美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 “如用相似的大锤,再次把人性砸变形,它就会扭曲成同样歪曲的形象。如再次中下肆意掠夺和压迫的种子,物从其类,也必然结出同样的恶果。”[6]受黑暗统治的人民值得同情,但是失去理性的狂暴已经扭曲了他们本来的面目,复仇太过狂热,被胜利者煽动,变成了阶级报复的偏激情绪,革命变成滥施暴力,人性被践踏。
小说中描写道那个年月,没有法律和公正可言。法官审犯人只凭一条原则:凡是和贵族沾上一点边的都要被处死。陪审席上坐着的是一群狂热分子,他们有的喝得烂醉,有的昏昏欲睡,只有听到要给犯人判死刑的时候才会亢奋起来。穷苦的缝工本该属于这场革命中获利的一方,但是却被安上搞阴谋的罪名判处死刑。达奈虽然是埃弗雷蒙德侯爵的侄子,但早就脱离家族在英国自力更生,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是一个待人友好,正直的青年,却连审问都不用就抓进监狱。 狄更斯在这里重点描写了德法日一家与马内特一家的纠葛。对于在监狱关押十八年后终获重生的马内特而言,女儿露西是他唯一的寄托,看到达奈和露西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可是“复仇女神”德法日太太一直像一团阴影笼罩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上空,她始终不肯放过达奈,定要将他致死才罢休,甚至对于无辜的露西也要赶尽杀绝。为了凸显她的丧心病狂,小说中描写了德伐日太太独特的趣味即“看杀头”:她毫无同情心,绝对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砍头的“盛宴”,总是坐在砍头的台子下面一边编织一边“欣赏”,看到杀人流血的画面无比兴奋,享受着复仇的快感,又把更恶毒的复仇诡计编织进新作中。以德伐日为代表的下层人民对贵族抱有深仇大恨,日渐丧失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同情心、爱心、悲悯之心,他们从反抗走向人性的沉沦,陷入了更深的泥沼。
三
雨果在创作《九三年》时,刚刚经历了流亡生涯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但是等待作家的是普法战争的悲惨祸端和巴黎公社成员的浴血奋斗,这给以作家直接的刺激。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雨果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认可革命,但随着革命斗争逐渐残酷激烈,他开始无法接受革命的严峻现实。雨果把人道主义看作是人类最高的信仰,“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7]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的人道主义观点是超阶级的,无论是贵族朗特纳克还是革命者郭文,西穆尔登,他们最终都超出了自身的阶级立场,归于无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圈子。小说这样描写到朗特纳克侯爵救出三个小孩时的情景:那一刻“魔鬼身上的上帝”[8]苏醒了,爵爷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他用一瞥高傲的眼光,使他面前的几个工兵让开路来”[9],虽然侯爵叫着“国王万岁”,共和军叫着“共和国万岁”,但是“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你高兴说什么废话就说什么废话,你就是善良的上帝。”[10]在雨果看来无论是叛军还是革命党,只要是作出人道主义义举的都是伟大的人,人道主义既可以征服叛军也可以征服革命党,甚至能在那一刻,使彼此忘记自身的阶级身份,共同接受人道主义的救赎。
雨果所强调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能通过乞丐泰尔马克得到充分表现。泰尔马克的形象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为他无知地放走了亲王,导致后来一系列惨剧的发生,他代表了当时法国农村的愚昧和落后,正是这些人给贵族的统治和反扑提供了契机。然而当我们回顾小说内容时,雨果描写到作为乞丐的泰尔马克救亲王是为了报答一饭之恩,并不是无知或愚蠢,一个乞丐尚且知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
乞丐和亲王接下来的对话意味深长:
“为什么救我?”
“这个人比我还穷,我有权呼吸,而他连这也没有。”
“我们现在是兄弟了,老爷,我乞讨面包,你乞讨生命。我们是两个乞丐。”[11]
在雨果眼中一个身份卑贱的人有权利站在崇高的人道主义立场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怜悯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不因他是革命军或是保王党另眼看待,仅仅是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在人道主义面前,一个乞丐和一个亲王是平等的,是兄弟。
小说还描写到乞丐送走亲王时郑重其事的一番话:
“我是在救您,但我有一个条件”,
“您来这里不是为了作恶。”[12]
乞丐救人是有原则的,这原则不是根据政治身份而划分,而是根据为恶还是为善的人道主义。当他发现村落被烧毁,对放走爵爷一事追悔莫及,也不是因为后悔放走了一个贵族叛党,而是后悔放走了一个做下恶事的人。雨果坚持认为,在人道主义面前,只有超阶级的善和恶,不因政治立场减轻或加重人的罪行。在人道主义面前,约定俗成的法律,政治立场,逻辑判断上的对与错都变得模糊不见,都是渺小的,只有人道主义精神是宇宙间最高的准则,正如乞丐对亲王所在做那样,人人都应该践行“强者对弱者,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保护和救助责任”。[13]
与雨果强调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不同,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旨归于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冷漠的金钱社会,唤醒以温情与爱为核心的人道力量;二是反对当时自私自利的社会诟病,推崇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的精神。笔者认为这与作家所处的创作环境和个人经历都有一定关系。
《双城记》创作的年代,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成为“世界工厂”。“那是英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14]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尖锐的冲突,终于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在十年间经历了三次高潮。但是,与雨果的创作动机不同,狄更斯在创作小说时,宪章运动已被镇压,他并不像雨果那样直接面对革命斗争的残酷和血腥,作家更能切身体会到的是英国人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侵染下如何唯利是图,人们自私冷漠,心肠坚硬,精于算计,就连亲情爱情都被打上金钱的烙印。另一方面作者自身家庭环境所带来的成长经历以及个人爱情经历对其创作也有一定影响:儿时,狄更斯勤奋好学,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阁楼里或树下看书,在瘦弱的身体里包裹着的是一颗有着强烈自尊,对知识充满热望的心。但是他的父亲不久后便因为欠债被关进负债人监狱,因为去鞋油厂做工可以每星期给家里挣七个便士,母亲执意要他退学去。为了七个便士母亲便抹杀了他受教育的机会,家里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愿意帮忙,甚至没有人站出来说一两句怜爱的话。对此,狄更斯的心里是怨恨的是失望的。青年时,狄更斯做过法律机构的记录员,记者等工作,接触到社会阴暗的方方面面,参与了无数离婚案件和财产案件,目睹人们为了争夺财产变得无情无义。这使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无情有一种深切体会。因此,“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缺失感一生都渗在狄更斯的骨子里”,[15]人性的自私,亲情的淡漠,社会的利己主义风气都成为他批判的对象,与之相对的,爱与温情,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则备受作家推崇。
《双城记》中马内特医生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八年,失去人身自由,整日无事可做只能面对着监狱的墙,为了保留最后一丝神智,他主动要求在牢房里做鞋,终日不停地缝鞋成了漫漫长日里唯一可干的事;由于长期无人交流,医生几乎丧失了正常说话的能力;多年来住在暗无天日的地方使原本健康的身体变得孱弱不堪。那对医生来说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埃弗雷蒙德侯爵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是为了女儿的幸福医生却能默默承受心灵的压力和痛苦,明知达奈就是仇人的侄子却依然同意他和爱女结婚,这是伟大的父爱,是童年的狄更斯渴望而不可得的感情。善良的洛里先生同情朋友的遭遇,尽心尽职责地替朋友守护唯一的女儿露西,不离不弃;当得知马内特医生获释的消息,匆忙从伦敦感到巴黎接回老友,对神志不清的病弱的马内特悉心照顾;当革命党抓住达奈,继而要对马内特和他的女儿下毒手时,又不顾危险帮助马内特一家从巴黎逃出来。这是友情的真挚和无私。卡顿对露西的爱情不求回报,为了成全女方的幸福甘愿代替情敌赴死,慷慨从容,这是为了他人为了爱而自我牺牲。像卡顿和洛里这样的人正是作家那个时代急需的人,他们身上充满人道主义的闪光,具有崇高的品格和温暖人心的力量。“狄更斯要成为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爱中的明灯。”[16]他通过塑造马内特医生,卡顿,洛里先生等形象,试图打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坚冰,在读者心中唤醒以无私奉献和爱与温情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
四
除了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侧重不同外,雨果和狄更斯在探寻社会的出路时持有不同的观点。
雨果把人道主义看做人类的最高信仰,坚信“在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17],他认为“这场斗争的战场是一个人的良心”[18],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要用一个善的灵魂才能撼动另一个灵魂,最终走向人道主义,“才能够把我们从人性的黑暗、狭隘和蒙昧中解救出来。”[19]人道主义是人类唯一正确的出路。在这个原则的支配下小说情节有多处违背现实的刻意安排,如心狠手辣的叛党头目朗特纳克可以在危机的时刻突然受到人道主义的感召发生转变,郭文为了奉行最高的人道原则可以不顾自己的政治立场放走朗特纳克。更甚至随着革命的发展,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与革命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对整场革命的正义性都产生了怀疑,深深陷入了革命和人道的矛盾之中,在小说结尾处通过郭文之死发出抗议的呼声,以人人互助互爱的人道主义王国为最高理想,对革命党丹东等三巨头组成的红色专政进行了一番指控。雨果在《九三年》中这样写道:
“我们所需要的”,马拉突然叫道:“是一个独裁者。罗伯斯庇尔,你知道我希望有一个独裁者。”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我知道,马拉,不是你就是我。”
“不是我就是你!”马拉说。
丹东在齿缝里咕噜说:“独裁,试试看!”
马拉:“……丹东,我同意你这一点;罗伯斯庇尔,这一点我向你让步。好,那么,结论是:独裁。让我们采取独裁的办法。我们三个人代表革命。我们是塞卑尔的三个头(看守地狱大门的三头怪犬)。”[20]
从作者描写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雨果意识到这场革命已经变质,当平民冲在最前面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时候,马拉,罗庇斯比尔,丹东三大巨头正坐在巴黎窗明几净的屋宇里,为建立新的专制政权开讨论会。笔者认为,在雨果看来革命发展到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革命党推翻了贵族的专制统治又建立起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实行红色恐怖主义,前后两者都不符合作家最高的人道主义信仰。激烈的对抗,使新事物不免走向偏激,以致新事物在取得胜利后,也难以走向健康的发展,而背离了它的本意,甚至使旧事物得以卷土重来。所以雨果通过郭文的口喊道“我更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共和国”[21],是奉行人道主义的王国,作家关心的是新的国家“有没有尽忠,牺牲,克己,恩恩相报和仁爱的地位呢?”[22]而不是这个国家最终是共和军的还是保王党的。一个奉行绝对的人道主义的王国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出路。只有绝对的人道主义——斩断了恨的、 超越了利害关系的神圣之爱,即使对罪人、对“凶手” 也怀有深深同情和怜悯的爱,才能拯救我们的社会。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首先狄更斯没有采取浪漫的处理方式有意夸大人道主义的作用,使所有的主人公都受到感化而精神“复活”,而是真实地再现出巴黎民众满腔的怒火和狂暴的复仇,德法日夫人从头到尾没有一丝心软,直到死亡才能阻止她继续编织复仇的网子。巴黎民众一点也没有意识到革命已面临走入歧途的危险,而是沉浸在复仇的喜悦中,恨不得杀光所有贵族,这样的描写比起雨果式的人道主义显得更为客观。其次狄更斯也没有把人道主义视为万灵的药方,借此逃避革命的残酷性,没有从一个极端(暴力革命)走向另一个极端(绝对的人道主义),而是辩证地看待了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一方面他看到了在革命过程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为了推翻旧的封建王权需要一些流血和牺牲,而不是像雨果那样陷入人道主义和革命的矛盾中,继而对革命的本质产生怀疑。《双城记》里的革命者始终坚持革命和共和国理想,没有出现郭文这样矛盾挣扎的形象。另一方面,作家反对将革命暴力扩大化。德法日夫人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对这个意志坚强,勇于反抗的女人还带着一丝欣赏,但是当她把报复的矛头指向无辜的达奈和露西时,作家对他的描写愈见冷峻。她尖刻的嘴脸,扭曲阴暗的心理,残忍的手段,逐渐暴露,最后到了招人厌的地步,连她的丈夫都不敢正视她冰冷无情的双眼。暴力是革命的手段,但不是革命的目的,当革命者像德法日夫人这样失去理智,只剩下残暴时便是反人道的,就该受到批判。正如小说中记述的罗兰夫人被砍头之前说的话:“我看到,在废弃这种报应的惩罚工具像目前这样使用以前,巴萨,莱克,德法日,那个陪审员,那个审判长,以及许多消灭旧压迫者上台的新压迫者,都将死于他的斧下。”[23]这是狄更斯为这个时代做出的预言。
在辩证地看待革命与人道的基础上,狄更斯提出改良政治的主张,把调和阶级矛盾视为社会的出路。我们可以从小说中三组对照人物形象中来看,即同为贵族的侄子达奈和叔父埃弗雷蒙德侯爵,同为革命者的德法日太太和德法日先生,以及同为犯人的卡顿和缝工。埃弗雷蒙德侯爵无恶不作,深受人民的仇恨,如果不是逃到国外,差一点就死于革命。与之相比,达奈被塑造成进步贵族的形象。他待人温和有礼,从不依仗自己的贵族特权为非作歹;他心地善良,不以家族姓氏为豪反而为耻,自己的叔父做尽了坏事,招人憎恨,作为侄子他受到良心谴责,放弃了一切地位和特权,主动脱离家族来到伦敦自力更生;他慷慨仁慈,尽力帮助平民,交代仆人不要苛责庄园里的佣人,减免税款,让他们过得舒心自在一些;他有情有义,对仆人宽厚仁爱,明知法国局势危险,但是接到仆人的求救信件,他只身犯险赶往巴黎救人。达奈的形象寄托着作者对社会统治者的期望,即反对压迫,实施有人道的统治政策,改善人民生活。德法日太太和先生都是革命者的代表,但德法日太太最终被仇恨蒙蔽了心智,丧失了人性,而德法日先生在革命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与人道主义相背离,他并不像妻子那样对砍头和流血无比狂热,在小说中他多次询问妻子报复的行动什么时候停下来,虽然没能彻底阻止德法日太太的疯狂,但对马内特医生一家自始至终流露出一丝同情和不忍,没有直接参与到德法日太太对马内特医生和露西的报复行动中。而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卡顿和一个贫苦的缝工手牵手走向刑场,“这两个本来各在一方,又大不相同的宇宙母亲的孩子,眼看着眼,你一言我一语,手拉着手,推心置腹”[24],他们相互亲吻和祝福,在生死面前,成为了亲人。作者通过这三组形象表明,如果统治者推行人道的政策,如果人人心中都存着爱和友善,阶级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天各一方的人也可以相亲相爱,人们可以放下仇恨,握手言和。
综上所述,尽管雨果式的人道主义和狄更斯式的人道主义为社会找到的出路不同,但不管是追求人间大爱大公,至善至美的境界,把希望寄托于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对社会的救赎,还是反对阶级压迫,试图调和阶级矛盾,走政治改良的道路,他们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人类的未来和人道主义精神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创作实践,表达出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悲天悯人的情怀。
注释:
[1]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郑永慧译。
[2]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郑永慧译。
[3]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郑永慧译。
[4]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5]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6]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7]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8]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9]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10]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11]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12]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13]郑永慧:《〈九三年〉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4](苏联)伊瓦肖娃:《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蔡文显 廖世建 李筱菊 译。
[15](美)埃德加·约翰逊:《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天津人民文学出版社,林筠因 石幼珊 译。
[16](美)埃德加·约翰逊:《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天津人民文学出版社,林筠因 石幼珊 译。
[17]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18]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19]陈为人:《“革命”还是“宽仁”?—重温雨果<九三年>》,《社会科学论坛》,2010/1半月刊。
[20]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21]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22]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郑永慧译。
[23]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石永礼 赵文娟 译。
[24]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石永礼 赵文娟 译。
参考文献:
[1](苏联)伊瓦肖娃:《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蔡文显 廖世建 李筱菊 译。
[2]柳鸣九:《雨果创作评论集》,鹭江出版社,1983年1月第一版。
[3]陈为人:《“革命”还是“宽仁”?—重温雨果<九三年>》,《社会科学论坛》,2010/1半月刊。
[4](美)埃德加·约翰逊:《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天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林筠因 石幼珊 译。
[5](法)安德烈·莫洛亚:《雨果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程曾厚 程干泽 译。
[6]张英伦:《雨果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