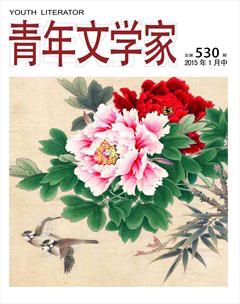论林译小说的伪翻译属性
任红伟
摘 要:本文以传统伪翻译理论为基础,结合巴萨奈特的翻译观认为伪翻译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但我们可以赋予其新的意义,以此来解除某些倾向于创作的翻译的尴尬地位。林纾的翻译就是这样一种尴尬而典型的存在,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因其不审西文,口授手追的合作翻译方法使其译本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个人创作的影子,这不免遭人诟病。本文认为,在晚清翻译草创阶段,林纾对其译本或有意无意地个人创作与改写无可厚非,与其质疑林译小说的忠实性,不如将林译本视为一种可接受的、具有伪翻译倾向的文类,关注其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意识的介入的程度,这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林译小说;伪翻译;《黑奴吁天录》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2--02
一、伪翻译的概念
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波波维奇(Anton Popovic)对虚假翻译(fictitious translation)的定义,他认为虚假翻译是指作者为了赢得广泛的读者支持, 将自己的原创作品伪装成译本出版,试图利用翻译来达到自己的文学计划。拉多(Gyorgy Rado)于1979年给予伪翻译更宽广的领域,他把过度偏离源文本的目标文本也纳入伪翻译的范畴。他认定确定一个作品是否是译作的标准是源文本与目标文本之间元素在何等程度上对应,是否可以称作伪翻译,要视其与原作的背离程度而定。吉迪恩·图里(Giden Toury)1985于将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定义为自称是翻译,却并无与之对应的源语文本(source text),没有事实上的语言转换和翻译关系的文本。图里不再把源文本事实上存在与否作为焦点来讨论,而更加关注它在实际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审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伪翻译作品历来是用来向本土文化推出一种新的文学元素的捷径。本土文化对翻译宽容的态度促使伪翻译大行其事,伪翻译虽不是翻译,却将翻译的功能利用的淋漓尽致。就其文化地位来看,伪翻译与翻译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原创与翻译之间日益模糊,翻译作为独立文类的地位也受到了质疑。巴萨奈特在《When is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中指出对翻译定义的难题(the difficulty of defining translation),“我们自认为很清楚什么是翻译。在我们看来,翻译是跨越二元分界线的一种操作行为。于是总会把自己纠缠于诸如原创性和真实性等问题,纠缠于权力和著作权、主宰和依附等问题。但我们是否确定我们了解什么是翻译了呢? 被我们称作是翻译的文本是否总是同一类文本呢?”巴氏在该文中提出了五中不同类型的翻译,这些“不是翻译的翻译”表明翻译本身定义已经日渐模糊,很难给翻译下明确的定义。林译小说虽然存在事实上语言转换关系和翻译关系,但是如果用源文本与译本比照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林译小说,就变得进退两难,可以林译小说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处于真翻译和伪翻译之间,具备翻译和创作的双重属性。
二、林纾的翻译观念
译以致用是林纾的翻译观念。与其说林纾的翻译是一场文学活动,不如说是一场经世济民的实业活动。林纾将译书作为其实业救国活动的一部分,首先,其译本有着明显的读者指向性,即有志青年和爱国人士。“至贵至宝,亲如骨肉,尊若圣贤之青年有志学生,敬顿首顿首,述吾旨趣,以告之曰:呜呼!卫国者,恃兵乎?… …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特学生人人之精实业”。林纾甘为“叫旦之鸡”,用文字儆醒同胞,尤其是有志青年和爱国人士,期望其能发展实业,强国固本以期救亡图存。其次,林纾每译一书,都要郑重其事作译序、跋尾,再三表明他的用意。在《黑奴吁天录 例言》中他希望读者不要将此书作为稗官野史,仅仅满足于猎奇心理,而是要国人以此为戒,以此为儆醒:“其中累述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而愈生其悲怀耳……则吾之书足以做儆醒之者,宁可少哉!”。
中西之同是林纾翻译的基础。林纾对中西著作在原意转换方面非常自信,如《黑奴吁天录》例言中写道:“书中歌曲六七首,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非译者凭空虚构。证以原文,识者必能辨之”。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林纾认为翻译只是在语言层面进行了变化,其本质意义不变。林纾认为中西文人脑力相似,其《例言》云:“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在林纾看来,文人的文笔文心是能成功译书的一大关键,甚至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能否译出原书的意蕴和作者的文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外语水平的问题,而是译者母语文才的高低问题。正是在这种盲目的自信下,不审西文的林纾与合作者翻译了百余部西方著作。
三、《黑奴吁天录》的伪翻译属性
林纾的翻译是在口述者的基础上的再次加工,不讲究具体字句的对应,可以说是译意不译辞。用典雅的古文传达西方现代精神,林译重在传达小说的整体意境和神韵,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受到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本土文化的影响会不自觉地在译本出体现出来,这使得其翻译日益趋向伪翻译的方向,由此可见,尽管伪翻译的概念最初只是指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伪”的程度也可取决于译者所加入的创作成份的多少。
林译古文形式迎合了当时读者的阅读心理习惯是林译小说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林纾的古文话语体系,不仅没有限制其翻译,反而极大地促进了其翻译,使其翻译的小说获得了当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林纾用典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小说,首先从文本形式上就背离了原作的创作风格。语言不仅是内容的载体,更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翻译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向另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过程,林纾译意不译辞的翻译方法虽然保留了源文本的故事情节和内容,却丢失了原文的意境和神韵。笔者以两种译本来对照分析林纾在翻译中增加和改变了什么。
“Why, the fact is, Haley, Tom is an uncommon fellow; he is certainly worth that sum anywhere,—steady, honest, capable, manages my whole farm like a clock.” “You mean honest, as niggers go,” said Haley, helping himself to a glass of brandy.
“吾遣吾奴汤姆与尔。其人绝愿悫,属以事,匪不如志。今既属君,应多予吾值。”海留曰:“天下之奴,安有精品。君言毋乃过耶!”因又引一觞。(林译)
“你的意思是说,就象一般黑人那样诚实。”赫雷说着,又自动斟上一杯白兰地。(张培均译本《黑奴吁天录》)
“你是说黑人的那种诚实吧?”海利问道,一面又斟了一杯白兰地。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
张培钧的译本标题虽沿用了林纾的翻译,然其内容则与林译截然不同,几乎是对原文做到了一字一句的直译。林译在保留故事情节情况下删去了很多带有异域文化信息的字句,汤姆的性格描述被归纳为“愿悫”(最早出自《商子》,意诚实、朴实),以“属以事,匪不如志”做总结性的陈述,丢掉了诸如“farm”、“clock”、“brandy”带有西方文化意味的词汇,甚至觉得原作不够精确,忍不住手痒,无中生有地加了一句“今既属君,应多予吾值”,以此展现讨价还价的商人形象。原文中的谢尔比是作者推崇的仁慈基督徒,在林纾笔下就多了些商人重利的铜臭味。然而对比林译和张译,林纾虽然丢掉原文的很多文化信息,其对言外之意的理解显然要高于张培均的直译。如“You mean honest, as niggers go”,从原文信息看,奴隶贩子海留(赫雷、海利)对奴隶显然是很不屑的态度,联系上下文可知,他不相信黑奴能和白人一样讲究信誉,所以用了一种嘲讽的反问语气。张译的直译未能表达出海留的原汁原味的态度,林译却是带有明显的创作成分:“天下之奴,安有精品。君言毋乃过耶”,用直白铿锵的否定句来表达海留的态度。由此可知,林译中加入了很多译者的自我理解,与原文表达方式相差甚远。相比较下,还是黄继忠的译本更能传达出著作的原汁原味,深入刻画了海留(赫雷、海利)这一奴隶贩子的丑恶嘴脸。
林纾不仅对文本形式、话语方式做了改写,在文章内容方面也加入了明显的个人创作。《Uncle Toms Cabin》是一部宗教著作,叙事者常常在讲故事之余发表个人的宗教见解和劝诫,不时插入《圣经》语录,抒发自己的宗教情怀。经过林、魏的翻译,《黑奴吁天录》的宗教精神以及伸张正义的声音不见了,对此,林纾在《例言》中解释,认为是烦琐的、无益于小说情节内容的都要删去。然而对照原作与译本,不是所有的宗教情节都被一刀切的删去了,很多黑奴在受到残酷压迫时呼天抢地痛彻心扉的情节还在,林译本对此比原作的描写还要入木三分,然而宗教对奴隶的抚慰作用却多被删去。如汤姆临终之前,凭着虔诚、忍耐和勇气最终得到了解脱,然而在林译本中则完全不提,汤姆反而是中国儒家传统观念附身,谆谆告诫儿子君子立身之道。因此林译本中压制了黑奴的宗教精神胜利,彻底塑造了黑奴吁天的不甘形象,正因如此造成了文本叙事的不平衡性,《黑奴吁天录》才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正因为译者对原著有所裁剪审查,把原著的宗教内容加以操纵而不是一刀切地砍掉,因此他们合作的成果,是一部强烈颠覆原文的翻译小说。”汤姆之死的情节可以说明,林纾的翻译是假,创作是真。
参考文献:
[1](英)Susan Bassnett. Constructing cultures [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美)Harriet Beecher Stowe.Uncle Toms Cabin[M].北京市:中央编译出版社.
[3] Harriet Beecher Stowe著,林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M].商务印书馆,1981.
[4] Harriet Beecher Stowe著,张培均译.黑奴吁天录[M].漓江出版社,1982.
[5] Harriet Beecher Stowe著,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6]朱安博.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科学出版社,2009(4)
[7]林纾:《震川集选序》.《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归震川集》[M].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三年8月.
[8]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M].北京市: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9]张佩瑶 从话语的角度重读魏易与林好合译的<黑奴吁天录>[J].中国翻译,2003(3).
[10]李宗刚.对林译小说风靡一时的再解读[J].东岳论丛,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