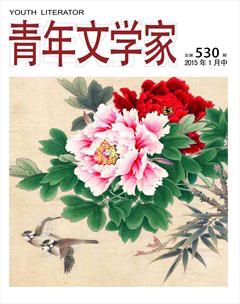妈妈?花朵?家
作者简介:郭伟,(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2-0-01
牡丹在开花,白色和粉红色。每一朵里面,像在芬芳的碗中,一群小小的甲虫在交谈,对于它们,花朵就像是家。妈妈站在牡丹花坛旁,拉过一朵花,展开它的花瓣,对牡丹的国土看了很久,那里短短的一瞬相当于整整一年。然后放开它。她所想到的大声对着孩子和他自己复述。风温柔地摇动着绿色的叶子在他们脸上投下了光的斑点。
米沃什对于与自己同时存在的其他生命和事物一直怀着深深的理解和怜爱,对于大自然的一切,更是怀着与生俱来的怜悯之心。在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过程中,诗人体验到了平静的快乐。这种融入自然的丰富体验,在他的诗歌散文中,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表达。“花”作为大地之上最能带来感官愉悦的事物,一直是米沃什诗歌吟咏的主题和惯用的意象。花园,鲜花,花朵,还有“康乃馨和郁金香”、玫瑰、忍冬花,……大量的花卉意象在诗人笔下纷至沓来,不断唤起各种让人惊异的美好情感。《世界·在牡丹花旁》也不例外,它通过一位母亲观花的细致过程,塑造了诗人“护花使者”的自我形象。
“牡丹在开花,白色和粉红色”,诗的第一句就把读者带到色彩斑斓的牡丹世界。尽管诗人在《惊异》中指出,“没被看见,没被听到/但它仍存在过。/没被琴弦和舌头表达,但它仍将存在”,肯定事物不为人类而存在的内在价值,但从人类视角来看,用感官体验世界,无疑是理解存在的最直接方式。当人们注视着牡丹花呈现“白色和粉红色”的同时,牡丹的“存在”正向他们敞开。“每一朵里面,像在芬芳的碗中,/一群小小的甲虫在交谈,/对于它们,花朵就像是家。”“甲虫”在花朵“芬芳的碗中”中“交谈”,它们或许不能像人类一样感受和理解“花”的存在,然而“花”作为“小小甲虫”的“家”或居所,天然成了甲虫世界的延伸。甲虫融入了牡丹花的世界。两者之间,没有存在意识的主体和客体,没有注视和被注视的过程,亦毋须存在的相互确证,它们在“忘我”(有本能性知觉而缺席强烈的自我意识?)与“相忘”中融为一体,在观察者的现象学还原过程中,形成了“牡丹的国土”和世界。
面对这片“牡丹的国土”,“妈妈”“站在牡丹花坛旁,/拉过一朵花,展开它的花瓣”,“看了很久”。“妈妈”温柔细致地看花的动作表达了她对这个小小的自然世界的喜爱和怜悯。在这里,“妈妈”不仅是人类生态保护者的代表,而且作为天然的女性、母性身份,她与大地或自然之间与生俱来有一种亲和关系。“妈妈看花”在“诗人·叙述者·读者”这里也形成了一幅和谐的生态图画。她“看了很久,/那里短短的一瞬相当于整整一年。”“整整一年”是用物理时间形容“心理时间”,这是在暗示,“妈妈”瞬间“看”的动作之中融入了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她可能想到什么呢?甲虫融入牡丹花的自得其乐?牡丹花“存在”的绽放?人如何与牡丹花一样的自然相处?……对于这位生态呵护者、母爱和女性的双重代表,“妈妈”唯一不会想到的就是去利用它,以奉一己之审美,否则就不会表现出“展开花瓣”“然后放开它”这样极其温柔细微的细节。“妈妈”不忍破坏主客体瞬间接近融合的美好体验(与“悠然见南山”的无我之境还是有差距的)。
美好事物是需要共同分享的。带着深沉的母爱,“妈妈”把“她所想到的/大声对着孩子和他自己复述。”她希望她的孩子和她自己能继续延续当下她与自然的这种亲和关系,珍视主客互融乃至相忘的生活体验,学会汲取牡丹花的存在启示。“风温柔地摇动着绿色的叶子/在他们脸上投下了光的斑点。”风、叶子、他们脸、光的斑点四个意象相互之间的温柔动作关系,暗示着“妈妈”和她的孩子与牡丹花的世界在刹那间营造的宁静与和谐。
诗人通过塑造“妈妈”的形象也“发现和创造”了他自己。而读者在按照诗歌真实意图阐释和建构属于自己的作品时,会越来越接近诗人所“发现和创造”的自我。我们会像诗人一样,努力融入牡丹花一样的自然和大地。这不仅是指从深度生态学的角度去落实地球伦理,呈现生态共生价值,而且退一步讲,也有利于更好地在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中实现自身的真实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