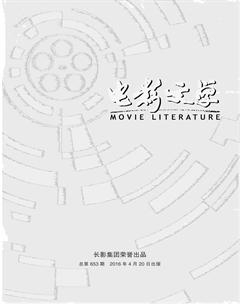结构主义视域下的《饥饿游戏》三部曲
[摘要]《饥饿游戏》三部曲尽管属于商业片范畴,但由于其中所包孕的深刻的反乌托邦内涵,一经推出便成为青少年电影中的佼佼者,在四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受到了电影批评者的关注。将这一系列纳入结构主义视域下进行观照,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堪称近年来反乌托邦电影中兼顾商业性和艺术性的杰出之作的构建方式。文章从影片的艺术风格、片中的二元对立、片中的符号三方面,以结构主义视角分析《饥饿游戏》系列电影。
[关键词]《饥饿游戏》;系列电影;结构主义
《饥饿游戏》三部曲是由狮门影业推出,根据苏珊·柯林斯同名小说改编的四部电影,分别为盖瑞·罗斯执导的《饥饿游戏》(2012)、弗朗西斯·劳伦斯执导的《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2013)、《饥饿游戏3:嘲笑鸟(上)》(2014)以及《饥饿游戏3:嘲笑鸟(下)》(2015)。电影尽管属于商业片范畴,但由于其中所包孕的深刻的反乌托邦内涵,一经推出便成为青少年电影中的佼佼者,在四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受到了电影批评者的关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在20世纪至今对电影理论产生最大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潮之一,原本属于文学批评领域的俄国的形式主义、属于语言学领域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引入电影批评在先,[1]克里斯蒂安·麦茨提出电影符号学在后,结构主义打破了传统电影理论的框架,使当代电影的批评出现了高度开放,有更多阐释余地的结构。《饥饿游戏》三部曲同样可以被纳入结构主义视域下进行观照,这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部堪称近年来反乌托邦电影中兼顾商业性和艺术性的杰出之作的构建方式。
一、《饥饿游戏》的艺术风格
在结构主义中,电影的结构决定了电影的功能,换言之,电影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如造型结构等)关系到电影能表达出怎样的意念内蕴。就反乌托邦电影这一阵营来看,投身其中的电影艺术家所热衷的艺术风格可谓千差万别,但稍加总结不难发现,其风格或偏于绚烂,在电影中制造出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奇观;或偏于阴暗,强调未来世界人性的堕落,政府或科技对人类的残害,试图唤起观众的警惕与担忧。从内涵上来说,《饥饿游戏》三部曲无疑二者兼顾,但是就形式上而言,只要与《V字仇杀队》《一九八四》等略作比较,就可以看到,作为青少年反乌托邦故事的《饥饿游戏》显然是更偏向于前者的。
《饥饿游戏》电影的诞生实际上并不属于好莱坞反乌托邦电影大潮中的组成部分,反乌托邦电影的繁盛时期在于20世纪的70年代。[2]《饥饿游戏》更应该被视作是《哈利·波特》《暮光之城》等系列电影掀起来的青少年电影潮流中的一员。青少年电影在21世纪的迅速兴旺带来的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电影消费群体的日益低龄化。这也就导致了以青少年为主角的反乌托邦电影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对极权统治的简化,其次是电影在形式上的娱乐化与游戏化。在电影中人们可以看到,出于对青少年观众的迎合,电影中的统治者的恶显得更为肤浅、直露,统治者在与以青少年为首的反叛者的对抗中也显得更为狼狈。与风格阴暗低沉的反乌托邦电影中,统治者往往对全民的意识形态、思想动态采取严格的控制,百姓甚至完全感受不到自己处于被囚禁、被压迫的状态不同,在《饥饿游戏》中,显然除了首都凯匹特的“上流社会”人们坚定地拥护这个政权之外,其他十余个区的百姓都处在敢怒不敢言,革命只差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的状态中。而《饥饿游戏》中的主题“饥饿游戏”本身就是一场华丽的大逃杀真人秀表演。毫无疑问,电影是对这一真人秀节目采取批判态度的,包括露在内的许多原本属于国家未来的青少年就在这种灭绝人性的自相残杀中丧生。并且电影还特意表现了参赛者被杀戮时发出的尖叫或哀号声,让观众感受到这个比赛的残忍。但是相比起同样是批判真人秀的《楚门的世界》《死刑犯》《狙击电话亭》等,可以看出《饥饿游戏》中的节目是最为耀眼华丽、夸张不凡的。其华丽之处不仅在于凯特尼斯的灵活身手、选手们的服装、宣传与包装方式,还有游戏主持人控制游戏的种种令人目不暇接的高科技手段等。这个比赛的目的已经不仅仅如《楚门的世界》中一样是为了获取商业回报,统治者已经将这个真人秀打造成了一个一年一度的“举国欢庆”的盛典,因此其必然要拥有华丽的包装与层出不穷的噱头,吸引着内外层结构中观众的眼球。在电影的内层叙事结构中,主人公凯特尼斯等人是用生命在娱乐着凯匹特城的统治者们,处于一种“被看”的困境中,但是在外层叙事结构上,电影院中的观众又何尝不是在为凯特尼斯死里逃生的奋斗历程娱乐着。在真人秀节目之外,对于武装反抗统治者的战争场面也拍摄得略有过家家之嫌,而缺乏了某种真实感与沉痛感。
但是,我们在承认《饥饿游戏》作为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为了制造青春、娱乐色彩,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乌托邦电影应有的严肃性和黑暗性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视觉奇观的制造依然是服务于其批判极权统治、张扬人性力量的主题的。仍以真人秀节目为例,其视觉上的夸张(除选手之外,主持人与观众的造型同样极为华丽奢靡,充满畸形趣味)实际上要达到的是一种荒诞感的营造。这个举国盛典的政治意义一是为了填补凯匹特人空虚的心灵,二则是为了震慑尚有反抗之心的其他地区人民。无处不在的闪亮装饰与五颜六色的浓妆华服,以及软科幻下的高科技尽管几乎没有让观众感受到恐怖,却让观众感受到了厌恶、排斥与荒谬。
二、《饥饿游戏》中的二元对立
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存在二元对立这一逻辑法则,在有“结构主义之父”之称的语言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展开之下,《俄狄浦斯王》等文学故事也被置于二元对立的法则之下进行观照,故事中的对立项被一一找出。这一方法后来也被吉姆·吉特西斯等人用来对电影进行分析,如西部片中的二元对立项有野蛮之于文明,西部之于东部,自由之于禁锢等。而普罗普等人则是采用格雷马斯语义矩阵,将行动元的概念代替了叙事中的角色,将角色也分为几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如主体之于客体,辅助者之于反对者等。[3]普罗普等人在叙事学上的建树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浪潮的一份遗产”。在《饥饿游戏》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其中一些采取对立形式的深层次结构。
首先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在电影中,凯特尼斯与皮塔等奋起反抗极权政府的人当然属于正义一方,而草菅人命、残暴空虚的凯匹特贵族们则是电影对邪恶的精妙诠释,本身凯匹特的统治地位就是建立在镇压起义之上的,在获得政权之后,他们并没有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如在片中凯特尼斯的父亲死于矿难,母亲精神失常,由于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凯特尼斯为了补贴家用而不得不拿起弓箭到禁林打猎;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斯诺总统等人还不厌其烦地举行杀人游戏比赛,使各区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与精神伤痛,凯特尼斯之所以参加饥饿游戏正是希望能保护自己的小妹妹不用参赛。在这样天怒人怨的政府面前,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凯特尼斯仅仅是其中一个代表。在第一部中,黑人女孩露死后,当地人民就掀起了一场很快被扑灭的起义。
其次则是敌与友的对立。在《饥饿游戏》中观众可以看到这样两对关系,一是12辖区与凯匹特,12辖区之中各辖区之间的关系;另一对则是参赛的青少年与观众,青少年之间的关系。按理来说,12辖区的人民都处于凯匹特的非人统治之下,理应团结起来,颠覆残暴的政权,然而他们却大多麻木不仁,也关心着饥饿游戏的比赛结果,仅仅是因为胜者所在的一区能够得到统治者的些许恩赐;而缩小来看,参赛者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如此,24个青少年作为“贡品”实际上是有23位注定要牺牲的,然而他们也没有互相协作,除了皮塔与凯特尼斯之外,其他人几乎都在大开杀戒。而凯特尼斯原本也以为皮塔是自己的敌人,在发现皮塔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救自己之后,两人成为盟友,最后共同与游戏主办方进行对抗,获得了双双胜出的一线生机。两人关系转变后出奇制胜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导演给12辖区推翻暴政,拒绝不合理的制度提供的唯一出路。
三、《饥饿游戏》中的符号
如前所述,电影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的影响。以至于关于电影是否可以被视作一门语言在数十年间引起了多位理论家的纷争。包括米特里、麦茨在内的电影批评家认为,电影不能被称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语言。首先,电影的表达是单向的;其次,影像可以视作对客观事物的展示,除此之外并不一定拥有与该事物对应的表意能力。但电影还不能被看作是自给自足的表意系统并不意味着电影无法拥有符号(imsigns)。[4]电影符号学中的重要人物帕索里尼认为,在电影语言中存在影像符号,它们对应的便是人类口语之中的“符素”。逻辑学家、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则改进了帕索里尼的观点,提出了电影符号系统中存在动态(相对于语言学的静态而言)的能指与所指系统,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镜头对于同一件物品的展示可以存在多种解读。在诸多电影中,可以看到导演选择了将某可见的、具体的事物作为表现对象,而观众则在心领神会中寻找到这一符号的所指,即某种不可见的、抽象的概念。这在《饥饿游戏》中也大量存在。
例如,电影中的“嘲笑鸟”意象就是一个有着十分明确所指的“反抗”符号。嘲笑鸟在电影中以多种形式反复出现,有时是凯特尼斯的胸针,有时是只出现声音,有时则是凯特尼斯穿上战服,以“嘲笑鸟”战士的造型出现。胸针是金色的,在西方,人们相信获得莱茵河黄金铸成的指环的人,必须抛弃爱情,但是可以获得杀死恶龙,还世界清平的力量。嘲笑鸟的形象被与勇往直前、不甘失败,同时又陷入皮塔与盖尔之间感情纠纷的凯特尼斯联系在一起。先是战服的设计师认为嘲笑鸟最符合凯特尼斯的形象,然后是13区的叛军们设计了一个“嘲笑鸟”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关键人物就是凯特尼斯本人。为了得到凯特尼斯,从而获取舆论上的有利地位,以科林总统为首的13区叛军暗中毁掉竞技场,带走凯特尼斯,随后便开始利用她的影响力和她对皮塔的关心让她为他们的反叛站台。
很显然,这个计划之所以叫作嘲笑鸟,正是因为凯特尼斯的嘲笑鸟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是13区煽动暴动,联合其他几个区的人奋起革命的符号。“某个社会的文化现象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系……那么作为人们内心文化观念与外界联结的各种象征,自然而然就是研究的出发点和突破口。”[5]耐人寻味的是,凯特尼斯很快发现科林总统等人实际上也与斯诺总统如出一辙,他们的理想实际上也是“一个领袖,一个声音,一种思想”,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对老百姓实施军事化管理的高压统治,和统治者一样制作各种精心排练过的、做作的宣传片。爱憎分明的凯特尼斯意识到,这样的人在上台之后无非又是一个新的斯诺暴君,人们依然要面临极权的统治。对此凯特尼斯又一次选择了不合作与反抗,嘲笑鸟的反抗精神被彰显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电影中的电视直播、赞助、总统演讲(包括总统斯诺的名字都与《尼伯龙根的指环》息息相关)等,也全都是带有政治意味的符号。
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审视《饥饿游戏》三部曲不难发现,其在风格上顾及商业回报而采取了以绚烂、夸张的视觉效果对观众进行吸引,并在其中寄托了荒诞感的手法,而在叙事上,《饥饿游戏》可以建立起一个二元对立系统进行分析,并在影像中隐藏了多种带有象征意味的符号,这一切都是为了感染观众,让观众反思人与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等关系的出路所在。可以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饥饿游戏》三部曲是属于“天上”的,其华丽与简单化的外壳有助于观众进入故事情节,但是究其根本,这个反乌托邦系列电影依然是立足于“人间”的。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度许昌学院一般科研基金项目“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文学地图研究”(立项编号:2016035);许昌学院第四届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张一兵.索绪尔与语言学结构主义[J].南京社会科学,2004(10).
[2] 曾勋.反乌托邦电影的前世今生[N].文学报,2013-11-07(024).
[3] 钱翰,黄秀端.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旅行[J].文艺理论研究,2014(02).
[4] 刘云舟.麦茨对电影叙事学研究的贡献[J].当代电影,2012(04).
[5] 储英华,何建平.象征人类学的思想渊源和基本特征[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07).
[作者简介] 郭龙娟(1982—),女,河南新乡人,硕士,郑州成功财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