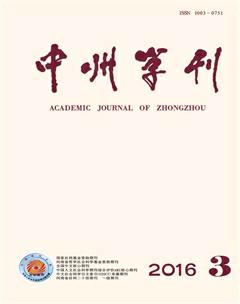北美外语片市场与张艺谋电影的竞争力*
陈 林 侠
【文艺研究】
北美外语片市场与张艺谋电影的竞争力*
陈 林 侠
摘要:张艺谋是考察当下中国电影竞争力的最佳案例之一。从张艺谋电影的北美票房数据可以看出,影响电影海外竞争力的权重元素,首先是性/欲望与权威主义密切相关的审美意识形态,几乎决定了市场的关注度;其次是突出的美学形式,能够产生异乎寻常的艺术价值与吸引力;最后是视觉奇观,能在前两者基础上增设更多的社会议题,但就自身而言,缺乏足够的市场影响。2006年之后的张艺谋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失去海外竞争力,即是私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极度萎缩,表现为文化传统与在地经验的双重缺失。为此,张艺谋创作需要从身份定位、微观力量、现代性内涵等五个方面努力。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审美意识形态;叙事形式;视觉奇观
一、张艺谋电影的北美市场及其神话的“终结”
截至2015年12月,张艺谋共执导了19部作品,其中《代号美洲豹》(1989)《有话好好说》(1996)《山楂树之恋》(2010)3部未能在北美上映,《红高粱》(1988)虽在1989年4月由New Yorker购买发行权,但在boxofficemojo网站缺少票房记录,因此,张艺谋共有15部作品进入北美市场并产生票房记录,遥遥领先于内地其他导演(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有81部中国内地电影进入北美市场,陈凯歌、冯小刚、贾樟柯仅有4部)。从票房来说,张艺谋电影也是最佳的,如五次成为内地电影在北美市场年度票房冠军,平均票房达到80多万美元。他不仅从故事生产上创造了国际电影节获奖模式,带动中国电影国际化,而且其作品牢牢占据海外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成为中国电影国际竞争力的风向标。因此,考察中国电影在北美市场的竞争力,张艺谋电影无疑是最佳的样本。我们用表1来显示张艺谋电影的北美市场状况。
截至2015年12月,北美市场发行并产生票房记录的外语片共有1780部。从表1“名次”一栏看,《三枪拍案惊奇》排名最次,但也在半数之上。张艺谋电影在北美市场的票房排名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1)3部古装大片票房非常突出,占据前百名;(2)6部文艺片超出北美外语片平均票房(105万美元),加上较接近平均票房的《一个都不能少》,这7部电影虽然从总体票房上不如古装大片,但从预算与票房的性价比考量,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3)后5部电影远低于平均票房,缺乏足够的竞争力。“时间”一栏表明:2006年成为张艺谋电影重要的转折点。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仅及《十面埋伏》票房的一半,《千里走单骑》票房仅为31万美元,成为票房倒数第二的影片。此后,他再也未能赢得北美及海外市场,如2010年的《三枪拍案惊奇》、2012年的《金陵十三钗》分别成为倒数第一、倒数第三的作品,并且无缘于戛纳、威尼斯、柏林等国际重要电影节的褒奖。2006年后的文艺片(如《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归来》等)均未获得世界级影响的重大奖项。从时间来看,1991年《菊豆》以来,张艺谋电影在北美发行非常集中;甚至出现2004年、2006年分别发行两部电影的情况。但是,《千里走单骑》后,时隔三年,才有2010年的《三枪拍案惊奇》、2012年的《金陵十三钗》以及2015年的《归来》在北美发行。张艺谋电影在北美市场的延时上映尤其是后继影片的接连失败,反映了北美乃至海外市场对之兴趣的减弱。“张艺谋神话”的终结由此真正出现。发行方面,票房与影院数量的关系密切,这取决于发行方的力量。《幸福时光》《三枪拍案惊奇》《千里走单骑》成为影院数最少的3部影片,明显与发行方SPC(Sony Picture Classics)的发行能力不符(毋庸说发行《满城尽带黄金甲》多达1234家,就是发行在国内反响平平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也能达到67家,《归来》的影院数位列第5)。这些发行数据表明,这3部影片缺乏明确定位(商业性不够,艺术性也不突出)。唯一例外的是《金陵十三钗》,仅进入30家影院,远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多部艺术电影,很难与其6亿投资的国际大制作相配。

表1 北美市场张艺谋电影的情况表
注:由于张艺谋电影在北美市场发行时间较长,为了准确反映历年发行与票房的真实状况,表1采用boxofficemojo数据库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数据,具体票房数据略有变化。但从名次的角度说,唯一变化的是,《幸福时光》超过《金陵十三钗》。“名次”内的两个数据,前者为张艺谋电影自身的排名,后者为它在北美整个外语片市场的排名。票房单位为美元。“时间”一栏指影片在北美市场的上映时间,而“时间/地点”一栏是指影片故事的发生时间/地点。“美学形式”一栏是指与内容相对的形式因素。
“时间/地点”显示,张艺谋电影的故事发生时间难以确定(仅《金陵十三钗》例外)。古代/宫廷/商业大片与民国/农村/艺术电影形成较稳固的类型;“现代”的时间元素与农村、城市、乡镇等空间元素均有配搭,相对缺乏稳定的关联。就地点来说,张艺谋电影故事发生地点确切的城市仅有上海、南京,其他均是非城市的模糊空间(即便城镇也如此,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三枪》等)。从这个角度说,张艺谋电影通过时空的抽象与压缩,凸显了一个因“模糊”而“永恒”的“乡土中国”形象。2006年之后,他力图描述现代中国,但缺乏有效的美学形式与叙事修辞。“视角”一栏能够反映基本的故事构架。我们发现,艺术电影传统的“受限视角”“微观叙事”在张艺谋电影里并不明显(仅28%),即便存在受限视角,但在叙述过程中也演变成事实上的全知视角。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虽以“颂莲”的视角开始,但镜头并不严格地以之为限,成为事实上的全知叙事;《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开端叙事视角严格控制在唐水生,但进入唐府后,受限的第一人称未能坚持下去。最典型的莫过于《英雄》《金陵十三钗》,影片开始(无名/书娟)的画外音似乎确立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然而一旦涉及复杂的叙述层次与情节内容,受限视角完全解体。这表现出张艺谋试图商业、艺术兼得的电影观。它一方面增加了故事性,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改变了第五代电影消解情节的叙事模式(如《黄土地》《盗马贼》等),也使得《英雄》等古装大片偏离了港式武侠传统,具有一定的人文气质与话题深度。但另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商业与艺术互相抵牾:为了照顾商业性,影响个体心理的深度与丰富性(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明显受到追求市场的干扰);为了艺术性,又阻碍了消费程度(如《十面埋伏》的“文艺腔”现象)。受限视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往往成为特殊的叙事形式及策略的表征。全知叙述大多缺乏突出的叙事形式。表1显示,张艺谋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艺片中集中表现出美学形式的创新,但在2001年《我的父亲母亲》之后①创新就逐渐消失。
“主题”一栏表明,张艺谋受到人道主义的影响,在传统/现代、个体/国族、民主/专制的语境中,爱情、尊严等人性价值成为推崇的绝对价值,昭示现代性的艰难。这种基于西方立场的反传统主义让张艺谋迅速走上世界影坛。新世纪以来,在传统与现代对峙中,现代人格的尊严变成东方式的传统情感。《我的父亲母亲》《十面埋伏》《三枪拍案惊奇》等,表现出与商业主义的合流,这也影响到张艺谋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在竞争力缺乏的5部作品中,《幸福时光》和《千里走单骑》属于东方传统的伦理情感(善良、父爱),《金陵十三钗》《三枪拍案惊奇》《归来》突出爱情的普世性价值。由于消费主义的釜底抽薪,这种缺乏特殊性与深度感的普世性价值颇有些陈词滥调,成为北美观众越来越不关心的话题。
二、审美意识形态:从反专制到民族主义
张艺谋早期电影借助中心/边缘、强权/弱势、男性/女性等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组建起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活情境,人物及其行动标记的自由、民主等现代性,自然欲望的人性话语成为威权主义的对立面,获得叙事与道德的双重力量。“反专制”成为张艺谋电影得到西方认同的关键。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发生强调边缘的“后现代”转向。宏大叙事的衰落导致各种(地方的、文化的、种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微观叙事(small narratives)的相互共存。②不同历史、区域、种族、性别文化构成了现代性反思的资源、维度、层次。③《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从东方文化传统,提供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反思经验:一方面,反专制的人性故事凸显了“反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另一方面,正如陈犀禾所言,“谋女郎”最主要的特点是对女性身体和情欲的发现和展示。④女性以“性背叛”的方式争取自身权利,彰显出性别意识的“性政治”功能,成为“个人即政治”的最佳注脚。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反专制”意味着“反同一”,“反传统”被替换为“反男权”。概言之,张艺谋叙述反专制、反权威这一特殊的在地经验,以女性的性感(东方异域的表象)与危险(挑战男权的女性主义),从区域与性别的角度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反思。
张艺谋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则出现民族主义的转向。女性身体与情欲的“反权威”“反专制”力量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已经消耗殆尽。海外华人学者张真甚至认为,早在1993年,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已被官方电影机构接收和肯定。⑤在《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中,女性出现“去情欲化”,近年来更为明显,如《山楂树之恋》《三枪拍案惊奇》《归来》等,反专制的身体政治早已不复存在。即便表现身体/欲望(如商业大片《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金陵十三钗》等),也不是指向驱动社会变革的心理力量,而是迅速与情感融合,成为迎合市场的消费主义。张艺谋新世纪电影依赖于民族主义,清晰地体现了主流政治意志,从上而下地整合社会经验。因此,在“中国崛起”的现实刺激下,张艺谋凸显了一种求全求大的帝国心态,悖逆于后现代文化强调微观、个体的基本精神。一个明显的表征是,权威形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官府/政府不再体现压抑、扼杀人性的负面价值,而是发生了从模糊(《十面埋伏》官府恶行的空缺)、中立(《千里走单骑》无意表现政府部门的官僚作风)到维护(《英雄》的“权威主义”的神话)的转变。进言之,这种维护权威主义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本民族文化传统及其生活方式的正面价值,而是依赖于族群本能但缺乏确切意义的民族主义。它以简单的族群概念,取代了对文化传统的理性辨识与准确表现,由上而下地强调对内的同质、对外的抗争,带有排他性、非理性、情绪化等特征。我们认为,现代民族主义在缺乏他族入侵、民族灾难等特定情境下,也就失去了社会动员的合理功能,很容易蜕变成忽视差异性经验、转移社会矛盾。在李泽厚看来,民族主义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的概念。⑥张艺谋电影从文化批判到主流政治的审美意识形态转变,在海外语境中尤其容易觉察。如裴开瑞(Chris Berry)认为,《英雄》的民族主义引发了中国大陆之外华人的反感。⑦以色列观众也看出《英雄》的帝国崇拜与权力崇拜。⑧张艺谋后期创作试图用个人/情感作为集体/政治的牺牲与献祭,弥合边缘与主流、弱势与强势之间的裂缝,积蓄起逐渐高昂的民族主义,在后现代思潮中很难赢得世界认同。
确实,新世纪以来,大凡在北美外语片市场上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及地区的电影,不仅故事经验较为丰富,传统(专制、威权/集体记忆)、现代性(普世价值/西方)与后现代(反专制、反权威/西方当下形象)错综复杂,而且,文化传统、在地经验往往成为正面价值。在多元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语境中,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在地经验,不仅是美学形式,而且已成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传统与现代,远不是先前认为的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如上所述,西方后现代“反本质”“反同一”的文化思潮,给他种资源提供了更多的表现空间。但与张艺谋新世纪电影不同,它们更强调文化政治功能,所表现出的民族国家、在地经验的正面价值,来自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是在美学形式的实践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而不是复制现有的政治观念。如《卧虎藏龙》自上映以来一直雄踞北美外语片榜首。家庭伦理及师道尊严、个体叛逆及极端自我的成长、弗洛伊德式的欲望控制与升华:不同的文化话语在“古老中国”犬牙交错。李慕白体现了儒道传统的合一(表现为克己内敛、温柔敦厚的人物性格,与道化自然、天人合一的武功气质的两者兼顾),在与现代、后现代的比照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叛逆不羁的玉娇龙反对任何社会化过程(影片充分表达了对父母的违背、对爱人的拒绝、对师父的反抗、对友情的不屑)。这种“后现代”“后个人”的特征,在李慕白的道德与情感的感召下,终于发生了回归传统、认同传统的价值翻转。墨西哥电影《非常父女档》(北美外语片市场排名第4位)的情况同样如此。开始的父亲形象具有放纵欲望的现代特征。在与女儿相濡以沫的生活中,在得知女儿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他不惜代价给女儿带来欢乐与自豪,充分流露出自然人性及其传统的伦理情感。影片透过父亲形象,不仅表现了传统对现代的优越,也显示了理性审视后现代的态度。母亲不期然的出现,令人惊讶地成为后现代社会的“酷儿”形象,并在同伴的唆使下,试图用法律但不道德的手段争夺女儿,暴露出自私的人性缺陷。也就是说,《非常父女档》显示出,在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的交锋中,前者赢得道义与情感的双重胜利。父亲/权威形象呈现越来越多的正面价值,已是一个普遍现象,意味着文化传统、在地经验在后现代视野中获得重新认识的契机。
概言之,从文化批判到民族主义,取决于张艺谋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动。从20世纪90年代国家体制的“被禁者”“受损害者”,到新世纪成为当下中国最具文化权威、标志主流价值的电影导演,他俨然成为国家层面上的“英雄”⑨。然而在西方看来,“张艺谋常常同时被赞誉和诟病为一个国家主义者,他时而粗暴地时而技巧地抓住‘中国’这个概念并将其兜售给西方”⑩。毋庸赘言,一方面,作为表征中国电影乃至国家主流价值的人物,反权威已不可能成为张艺谋持续的选择;另一方面,在新世纪电影产业全面市场化的过程中,他的国际声誉与成功案例不断吸引民间资本、境外资本,他又不得不遵循商业大片的运作逻辑,承担大投入与高回报的资本责任。这使得他深陷政治与经济夹缝难以自拔,出现了勉力调和个体与国族的《金陵十三钗》。然而,性/色情脱离了个体真实的心理欲望,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反而暴露了个体欲望/边缘舍弃自我、归依国家意志/主流的尴尬。在国内外的批评之声中,他只能回到《归来》这种阉割政治经验、重复极简主义的“怀旧”“泛情”的套路上。可以说,囿于身份与地位,张艺谋既不能充分表现人性欲望、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又很难表现残酷冷漠的专制权威,特殊的限制导致故事经验的肤浅与空洞,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感性的力量:奇观抑或美学形式

作为影像本体论的实践者,张艺谋从《红高粱》开始,就突出视觉形象与影像风格(包括早期摄影的作品《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表1中的15部电影显示,张艺谋电影中的视觉奇观可分为四类:(1)自然奇观。如出现沙漠、黄杨树、竹海、峡谷等或雄奇或险峻的自然风景;(2)制作奇观,即指导表摄、服化道等电影制作环节制造出来的视觉奇观;(3)民俗奇观,在众多电影中出现的京剧、秦腔、皮影、“二人转”等民间艺术,以及虚构的颠轿、捶脚、点灯笼等民俗;(4)身体奇观,包括女性身体的色情展现和男性身体及其武打动作。结合“时间”一栏,我们发现,张艺谋早期电影中的奇观主要属于第二和第三种,既有突出的视觉形象,也携带了复杂的情节功能与心理意义;后期电影依赖于第一和第四种,或客观环境,或影视技术,未能融入情节与人物。表1显示,视觉奇观并不能决定电影的市场表现及其艺术评价,美学形式对电影的权重影响更大。如张艺谋最缺乏竞争力的4部电影,虽有影像奇观、但都没有显著的形式,在艺术价值与市场影响上均弱于存在形式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更不能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意识形态、形式、奇观等三者兼备的电影相提并论。如《活着》位居前五,在艺术电影中仅次于《大红灯笼高高挂》,得益于敏感的政治内容及其反讽,但情节剧模式的结构缺乏足够的形式感。该片强调社会变动、政治事件的广度,但在人物深度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再如《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美学形式不够突出,与《英雄》相比,影响力与艺术创新存在明显差距。



四、对策与思路

对于陷入创造力衰竭处境的张艺谋来说,至少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
第一,准确定位身份,摆脱观念的束缚。电影作为文化消费,归根到底是内容消费、意义消费。作为国家文化重要的代表,张艺谋需要从观念上摆脱狭隘的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奇观电影)的束缚,在现实政治、经济提供了最大自由的情况下,从文化层面上实践电影的政治功能。他必须舍弃显见的民族主义,回到文化传统、立足当下经验,辩证地维护本民族国家的文化理想及其利益。具体地说,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审视文化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展示文化传统的正面价值;面对复杂的当下社会,从现实的维度丰富故事的人性经验。像《山楂树之恋》《归来》那样,降低人物的感性力量、削减心理意义、刻意回避意识形态,只能适得其反。
第二,增强电影的微观力量。张艺谋乃至整个第五代导演擅长从抽象理念到人物个体,但这种电影观念必须在强调差异、边缘的后现代语境中做出适当的调整。电影之所以成为艺术,在于专注与呈现特殊的、例外的价值,而不是再现或确证普世性价值。就思维方式来说,张艺谋应当跳出个体/自由与国族/专制的二元对立模式,摆脱从特殊到普世的叙事程式,而是应当在普世性经验的背景下,聚焦于个体的微观生存状态。当微观的个体状态、生活境遇及其心理欲望,被镜头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后,就不再是囿于个体自身,而是成为国族、集体的表征。《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早期电影的成功就是基于这种聚焦微观生存状态的叙事话语。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在文本世界中之所以成为审美意识形态,在于意义的情境化与心理化。而这特别需要微观的、差异性的生存状态爆发出足够的审美力量。
第三,丰富电影的现代内涵。在张艺谋电影中,现代性内涵表现为民主与自由意志等两种已经泛化的价值。这在时间跨度较长的创作中,很容易导致意义内涵的空洞与生硬,如性格的沉默、情感的执着已成为电影人物的固定特征。然而,更重要的是理性精神的思维方式。从意义生成的角度说,它强调内在性生成,意义在假定性语境中遭受不同理念的挑战,在克服自我缺陷的过程中,最终获得真实感。从内涵的角度说,它离不开理性思辨,在特殊的情境中出现自我审视,产生出超越性。毋庸说民族主义,即便如传统文化的仁义忠孝,在经历了辩证的理性反思后,也会具有文化的超越性。因此,现代性内涵并不着意于确切的意义,只要是多元意义的自主选择,自然会出现意义丰富的现代性特征。这是张艺谋电影最需要吸收的理性精神。
第四,突出叙事形式的创新。张艺谋电影的叙事形式较匮乏,应当从视觉奇观转移到叙事形式的创新。对于具有优异的视觉感的张艺谋来说,叙事形式的创新并不复杂。电影作为蒙太奇艺术,始终离不开元素的解构与重组。如果奇观的形式表现为视觉元素打散后静止的放大,那么,叙事形式的创新则在于叙事元素分解之后的自由组合。叙事人称、视角、语调、频率、层次、分段等众多元素,在形体、色彩、镜头、声音等电影语言中,重组存在着几何倍数的可能。在这些无数可能中,选取与特殊的故事内容最能匹配的叙事形式,势必会大大增强文本的艺术性。从现实的角度考量,这是张艺谋最需要也是最容易的突破口。
第五,增加必要的叙事修辞。文本意义的丰富需要借助必要的修辞。事实上,只要文本出现詹姆逊意义上的“国族寓言”,实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联互动,就必然包括隐喻修辞。在电影叙事中,隐喻修辞具有重要功能:一是让抽象的意识形态获得形象感,生动传达故事背后的主体观念;二是意义压缩的多义暧昧,使得文本丰富、意义增值;三是促进影像风格化,形成艺术个性。事实上,实现隐喻修辞也并不困难。当我们关注微观形态、聚焦个体生存,达到意义溢出的程度时,就会出现意义增值的隐喻。反过来,外在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只有经过隐喻修辞的凝练与压缩,形成一个以小见大、意在言外、私人与公共经验关联互动的故事,才能在具体叙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转换成具有形式感的审美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说,张艺谋要改变后期电影的单薄与空洞,就特别需要从具体细节、影像风格到思维方式的隐喻修辞。
注释

责任编辑:采薇
Foreign Language Film in North American Market and Zhang Yimou′s Competitiveness
ChenLinxia
Abstract:Zhang Yimou is one of the best cases to study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of the North American box off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re are three weighting factors influencing Zhang Yimou films′ overseas competitiveness. The first is aesthetic ideology closely related to sex/desire and authoritarian, which almost decided the market′s attention. The second is the prominent aesthetic form that can produce extraordinary artistic value and attractiveness. The third is the visual spectacle which can create more social issue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two factors, but in itself lacks adequate market impact. After 2006, Zhang Yimou films and even the whole Chinese cinema have been losing overseas competitiveness because of public experience and private experience′ withering, which showed the lack of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xperience on the ground. To this end, Zhang Yimou needs to work in five areas, such as identity, micro power, modernity connot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Zhang Yimou; aesthetic ideology; narrative form; visual spectacle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154-07
作者简介:陈林侠,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广州510275)。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北美动态数据库的中国电影国家形象及其竞争力研究(1980—2014)”(GD15CZW01)。
收稿日期:2016-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