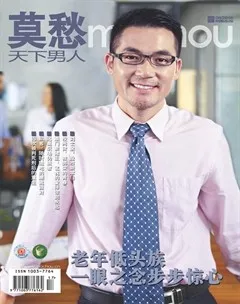“书衣大师”吕敬人
他是“中国书籍设计第一人”;他发动了一场书籍形态学的革命,在传统与现代书装业之间修砌出一道分水岭,将传统的书籍装帧推向了书籍形态价值建构的高度。
创作“最美图书”
上世纪80年代末,吕敬人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被公派去日本进修,跟随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学习。
在杉浦康平位于日本神户的工作室里,初来乍到的吕敬人从最基础的“学徒”做起。杉浦康平对细节把控是出了名的严谨,设计一本书时,必然要和作者、插图画家、出版社的编辑共同讨论文稿,从文字到图像、结构等方方面面来塑造作品。在那个电脑排版还未兴盛的年代,吕敬人一开始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老师的指点下,拿着小镊子一点一点对字体和图案做着各种拼接。
“书籍设计绝不只是简单地做个封面设计和装帧而已,它应该由表及里、由内而外,与书籍本身的内容完美契合,而且还涉及到各种领域的知识介入。”杉浦康平对图书整体设计的理念让吕敬人豁然开朗。此时,中国的书籍设计与书的文本还处于割裂状态,只谈装帧,不谈整体。这段求学经历,让吕敬人对书籍设计有了重新的认识。
回国后,上世纪90年代末,吕敬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最美图书”的创作。
接到《梅兰芳全传》设计委托之初,出版社只要做封面,整本书只有五十万字的纯文本,没有一幅图片。吕敬人将书通读了几遍,陷入了沉思。“这样简陋的装帧思路,怎么能将一位表演艺术家的视觉形象充分表现出来呢?”仅做封面肯定是不行的,经过一番思虑,吕敬人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了梅兰芳之子梅葆玖,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梅葆玖望着这个“多此一举”的书籍设计师,不禁眼前一亮。他当场答应吕敬人,可以帮他寻找父亲的照片,以充实书本内容。不久,吕敬人拿到了梅兰芳各个时期、不同层面的大量图片,巧妙地编排和设计在文本中,整本书一下子显得生动丰满了许多。
在设计书衣时,为了更好地突出梅兰芳的人物形象,吕敬人经过反复设计,最后打算为书口做可以左翻右翻的设计:左翻是梅兰芳穿戏服、女性身姿的舞台形象,右翻是穿着马褂的生活形象。他想象着,读者在轻轻地一个翻阅的瞬间,就能直观地窥见大师的一生。
编辑设计功夫花得多一些,出书时间也推迟了,但这本《梅兰芳全传》给梅兰芳“粉丝”留下深刻的印象,上市两个月就销售一空,此后多次再版。梅葆玖本人也对这本书的设计赞不绝口,这本书也最终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奖。
作为书籍设计师,吕敬人希望能在更早的阶段,比如选题确定之后,就介入到图书策划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记忆》就是他对书籍整体设计理念的一次完美演绎。设计伊始,吕敬人就十分注意和编辑进行沟通,对图书要做什么内容,希望做成什么样式,心中都有非常清晰的构想。整本书的内部编排、分割以及书的翻页阅读方式形态,都在与编著者、编辑和设计师不断商讨磨合中进行。《中国记忆》在德国莱比锡书展上一举摘下了“世界最美的书”桂冠。
做“中国味道”的设计
在与杉浦康平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吕敬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吕敬人和国内许多美术编辑一样,沉湎于西方文化。而杉浦康平却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作为中国人,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书籍设计必须扎根于本土文化之中,才能获得世界的认可。”在名师指引下,吕敬人走上了一条探索具有中国书卷味道的设计之路,并立下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位,不拟洋又尽显时代精神。”
《朱熹榜书千字文》是吕敬人的一部得意之作。在构思这一书籍的形态时,吕敬人认为朱熹的大字遒丽洒脱,以原大复制既要保持原汁原味,又要创造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形态。
为了还原书法拓片的原貌,吕敬人煞费苦心。经过反复试验,他为该书选定了当时很少应用的蒙肯纸。这种纸与宣纸质感接近,能呈现碑刻拓片的感觉。传统夹板装的书板采用了质地轻盈的桐木,上下书板连接部分使用了牛皮带,扣子则为如意造型,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在裱订珍贵书籍时,所用的材料和符号。细节上的精致处理,造就了书籍形式上的古朴与苍劲。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诸多藏家的追捧之物。
为了设计一本好书,他常常不惜工本。当然,这种看上去不惜工本做好书的设计,在执行时也会受阻。
作家冯骥才指定要由吕敬人来设计《绘图金莲传》的装帧。在对书稿内容充分研读之后,吕敬人决定为其量身定制一个古色古香的闺秀妆奁盒作为书壳。配合图书的文本内容,他还在书壳内叠放了一只从北京琉璃厂买来的小鞋、一枚专门为此书设计的印着老照片的藏书票,然后在书壳外面裹上长长的“裹脚布”。
冯骥才对这一套方案颇为满意。可没想到的是,等看到成书,吕敬人立时血压飚了上去。原来,为节约成本,书商撤走了裹脚布、小鞋,还有藏书票。盒子外包装的纸质也和吕敬人原本要求的布纹手感大相径庭。因为偷工减料而被篡改创意,吕敬人既生气又无可奈何。多年后,他感慨地说:“现在设计者的痛苦在于阻力重重。一本书的出版涉及到纸张、印刷、装订、销售一系列的环节。出版社要核算成本,在成本紧张的情况下经常会不由分说砍掉设计费。结果图书不但设计不行,整体质量也很差。中国图书设计强大要靠自己,首先要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
《灵韵天成》《蕴芳含香》和《闲情雅质》是一套介绍绿茶、乌龙茶、红茶的生活类图书。出版社请吕敬人帮忙设计,告诉他书的定位是时下流行的实用型快餐式的畅销书。按照惯例,吕敬人从头到尾细细研读了一遍后,发现作者对中国茶文化有极深的了解。这套书透出中国茶文化中的诗情画意,如果以纯商品书物的形式出版,多可惜呀!
吕敬人分别找到了作者和出版社,就文化与市场、成本与书籍价值进行了反复的探讨,最终达成了修改意见。在吕敬人的设计下,这套书完全颠覆了原先的出书思想,用优雅、淡泊的书籍设计语言和全书有节奏的叙述结构诠释主题。虽然书的价格成本比原来预设的高了些,但书的价值得到了全新的体现。
吕敬人说,最美的书,容颜无需“光彩夺目”,但一定是有个性的书。书的设计语言要有自己的艺术生命,不抄袭、不模仿、不盲从,方能很好地传递文本内容,呈现出不俗的品位。
怀有虔诚的匠心
从业四十年来,吕敬人设计的图书超过2000本。其父96岁时,以吕敬人姓名中的“敬”字写了一纸条幅“敬事以信,敬业以诚,敬学以新,敬民以亲”,要努力做到专注本职,钻研业务,探寻新知,善待他人。这是吕敬人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职业生涯和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骨子里坚持书籍设计美学的吕敬人,是个博学众长的杂家。他喜欢音乐、戏剧、电影、文学,这些趣味既源自幼时家庭环境的熏陶,也与他对书籍设计的理解痴迷密不可分。“书籍设计师应该是一个杂家,戏剧、电影、绘画、书法各领域都应该涉及,还得对统计学、逻辑学、信息学等知识有一定的掌握。然后,通过这些知识的整合,让书籍设计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讲故事的方法。”
他喜好收集各种猪形玩偶,常常自嘲“猪性难移,执迷劳碌”。工作室的桌面摆满了木鱼、猪玩偶,一颗童心不言而喻。他还爱看动画片,每做些演讲、授课的视频,总是不忘在视频里穿插各种小动画。年近古稀的吕敬人一语“道破天机”:“无论是作为书籍设计师,抑或是作为老师,都应该紧跟时代潮流。思维活跃、观念开放才能让手中的设计焕发出与时俱进的‘光芒’。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保持一颗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的童心。”
除了自己设计作品,吕敬人还看重社会责任,他开展书籍设计研究班,从早到晚讲课、示范,手把手地教给学生如何手工制作羊皮书和牛皮书,邀请国内外一流设计师为大家讲解,甚至电子书的设计课程也要讲授。在他心里,中国设计的进步,绝不仅仅是设计师的进步,也有编辑对书籍审美的理解,因此他特别愿意给编辑讲课,促进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的合作。
吕敬人的职业生涯与我国书籍设计近四十年发展的轨迹密切贴合。他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装帧到现在的中国书籍设计的变迁,从活版到照相排版、胶印、数码印刷,技术的飞跃发展影响图书设计的发展。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电子书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中,迎着这股潮流,吕敬人仍旧以手艺人的身份,怀着一颗虔诚的匠人之心,默默地做着一本本令人惊叹且触动人心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