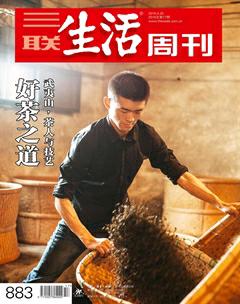古代茶事中的水与器
余闻荣
水、器之于茶事,或有比为一为茶之母,一为茶之父,细想,也有些许道理。水几于道,不仅老子这么说,孔子曾观于东流之水,从中总结出九德,或曰十一德,这么说来,水与器,有可能演绎成道器的关系了。

茶之水
水与茶的关系,明人的论述最为精当,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云:“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
许次纾《茶疏》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
张源《茶录》总结:“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曷窥其体。”
茶之水,分鉴水和候汤两个层面。鉴水是关于水的选择,候汤是烹饮之前煮水温度的掌握。
宜茶之水,首重的是一方水泡一方茶。各产茶地的泉水不在于是否著名,但用当地的泉水烹当地茶,对茶优点的发挥,绝不是外地的名泉所能比拟的。正如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所云:“夫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离其处,水功其半,然善烹洁器,全其功也。”最著名的配对要算虎跑泉与龙井茶。虎跑泉现在成为如此著名的旅游点,人流如梭,周边环境已大为变化,我估计那水也已经不复当年了。其实龙井茶和泉的交集不在虎跑,而在龙泓,龙泓是龙井的古地名,看此就知道当年是一汪泉水的名称,此事在杭州的地方志记载甚详。
烹茶用水之外,制茶用水古时也很讲究,如宋代贡茶产地的建州北苑,有专用于制茶的御井;元代贡茶产地的武夷山天游峰下的御茶园,也有专用制茶的通仙井,制茶用水可能除了当年作为贡茶的建茶,其他茶类是不用的。
几乎精于论茶的人,都精于论水。爱茶的皇帝中最有名的大概也就是前有宋徽宗,后有乾隆了。我更倾向于宋徽宗是真懂茶的,从他的《大观茶论》可以看出,此书不但对茶的采、造、点、饮,论述精妙,而且对水的论述,也有创意。因此后人甚至认为此书不可能是宋徽宗所作,因为书中对茶兴废之论,极为辩证而客观,不像风流君王之口吻。
宋徽宗谓“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我于此喜“清甘”二字。清者本已含洁,而轻者,则难以衡量。若乾隆,则取轻为水之至善,曾说玉泉山水为天下第一,理由是乾隆让人用银斗衡量玉泉山水与其他地方泉水的重量,其结果是玉泉山水最轻。
乾隆在《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载:
尝制银斗较之,京师玉泉之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亦斗重一两。济南之珍珠泉,斗重一两二厘;扬子江金山泉,斗重一两三厘,则较之玉泉重二三厘矣。至惠山、虎跑,则各重玉泉四厘,平山重六厘;清凉山、白河、虎丘及西山的碧云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则更轻于玉泉者有乎?曰:有,乃雪水也。尝收集而烹之,较玉泉斗轻三厘;雪水不可恒得,则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诚无过京师之玉泉,故定为天下第一泉。
以今之度量器观之,清代之容积为一两的斗的精密程度,要想区别出同样体积、不同地点的水的重量,显然是不可能的,且当是看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吧!
要说谁轻,可能是纯水最轻了,也就是我们物理学上说的每立方厘米一克比重的水,是一克标准重量的来源。这是纯水,不含任何杂质、自然也不含任何溶于水的矿物质。自然界到处存在的都不是纯水,其比重都大于纯水。我们所重视的矿泉水和泉水,通常都有不少的矿物质溶解在其中,而我们所谓的泉水有甘甜或咸的感觉,恰就来源于其中的矿物质的存在。所以,以轻而定泉水之高下,显然是有问题的。
乾隆此论可取者唯“凡出山下而有冽者”一句,一则说了水出于山下,二则说了一个冽字。
说水之清冽,印象最深的是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的一段:“下见小潭,水尤清冽……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用“皆若空游无所依”来写水之清,可谓极尽状物写景之妙,从此对形容水的“清冽”二字,耿耿在心了。
而明人田艺蘅《煮泉小品》论水则用“清寒甘香”四字,谓“清,朗也,静也,澄水之貌。寒,冽也,冻也,覆冰之貌。泉不难于清,而难于寒。其濑峻流驶而清,岩奥阴积而寒者,亦非佳品”。又谓“甘,美也,香,芳也。……惟甘香,故能养人。泉惟甘香,故亦能养人。然甘易而香难,未有香而不甘者也。味美者曰甘泉,气芳者曰香泉,所在间有之”。
详考古人论水名言,如“清轻甘洁”、如“清寒甘香”,又宋唐子西谓“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或苏子“活水仍须活火烹”,究之于物之理,取“清冽甘活”四字为择水之要。
清者,无色透明无杂质,为眼鉴之清,此基本要求。若于此不可得,则可舍之。嗅之于鼻,其气清爽,犹古人言气芳者,断不可有异味,此鼻鉴之清。尝之于口,味甘不杂,此口鉴之清。
冽者,凉也、寒也。手触之而凉体,口含之而醒心。大凡泉水始出于山麓石隙,多冰凉者。若温温然者,舍之亦可,为何?从卫生角度,低温则有利于抑制微生物生长繁殖,而如果我们感觉到的水是温的,大凡也有利于微生物细菌的繁殖,则此水即使清,也未必卫生,即今所言干净而不卫生,因为极可能有肉眼不可见的细菌已经有效地繁殖在其中了。或者可能水在石中缝隙本也寒冽,但出水处,或蓄水处的地理原因,如日照强烈等导致水极容易升温,此亦当谨慎取用。但凡如流动性很强的活水,也不容易为外因导致升温。
甘者,味之美也。我们通常说纯水是无色无味的,可是我们取自自然界的水都不是纯水,因为有各种矿物质溶解其中,难免导致口感的偏差,或咸(如崂山矿泉水)或涩、或苦或酸,于烹茶皆不可取,可取者,唯甘一味。甘不完全等同于甜,更不能是有含糖的甜的感觉,所以古人但云“味之美者”,一种很舒服的口感,叫回甘固然可以,称有点甜也对,总之是水内在的矿物质对口腔味蕾形成的良好的反射感觉。
活者,流动之水也,陆羽《茶经》中说的“使新泉涓涓然”、“井,取汲多者”,也都是强调水要活的。再好的水,如果淤积,不流动,就容易导致滋生各种微生物,同时,不能流动的蓄水环境,由于水不能一直冲刷同时带走不干净的物质,所以也不可能是取水的好地点,不论是泉水、井水,活水意味着是鲜水,是最少被污染的水。
活水,又以刚从石隙中渗出者为佳,就是陆羽《茶经》中说的乳泉,也被喻为石乳,确实是一等好水!《煮泉小品》认为“泉非石出者必不佳”,说的是同一道理。大凡此水,又以出于半山特别是山麓者为上。盖因山上之水,如雨水,入土壤后,又慢慢渗入岩石层,经岩石层的过滤,同时溶解了岩石内的微量金属和微量盐类,实际上形成了矿泉。而渗透的岩石越深厚,则矿物含量越丰富。当然,矿物含量多也不是一味的好,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益于人者,有无益乃至有害于人者,钙、镁是最容易被水溶解的两种矿物,但当钙、镁含量过多时,就是硬水,硬水虽也是含矿物质丰富的水,可不是什么好水,是肾结石、胆结石的祸根之一。
有不少泉水流出或涌出之处,都会形成一个坑、潭或井,越是这样的取水地点,越要注意活水的问题,只有不断溢出流动的泉水,在水质上才有卫生的前提。取水,一定要尽量取靠近泉水的源头活水,如果泉水已经在地表流出很远,沿途的污染就会增多,很难说是否有看不见的污染物融入水中,此亦取水之要点。
水之清、冽、甘、活,与清人梁章巨论武夷岩茶之清、香、甘、活,仅一字之别,唯其理或有可通者,如清字、甘字;或有不同者,如活字。概言之,清、甘、活,为茶事之首务。
陆羽精于鉴水,张又新《煎茶水记》中记载的陆羽品鉴的二十处分为二十等之水,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扬子江南零水第七。到如今,只有惠山寺的泉水第二因为一曲《二泉映月》仍然著名,虽然泉水早已干涸。而历史上更著名的两则鉴水的故事,其一就是陆羽鉴别南零水的,另一则是《警世通言》中编写的王安石和苏东坡关于中峡(瞿塘峡)水的故事。这两则故事都事涉无稽,编的人智商不高,信的人就更堪忧了。
候汤之难
“候汤”,是另一被讨论得很热闹的话题。北宋著名的茶专家蔡襄(对,就是那个仅被认为是书法家的蔡襄),在他著的《茶录》中就说“候汤最难”。
候汤最难,牵涉两个方面,一是和茶的烹饮方式有关,二是和煮水的器具有关。
候汤理论,来自于陆羽《茶经》中提出的三沸论:
“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这是《茶经》中很重要的一段候汤文字,对后世煮水烹茶影响甚大,其初沸、二沸、三沸之说,可谓深入历代文人之心,后之煎水,基本上围绕着三沸论,当然,有所发展是难免的。
到了晚唐的皮日休,又新创蟹目一说,皮日休《煎茶诗》云:“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我们谁也不能肯定诗中鱼鳞是否代指鱼目,但此后宋人笔下蟹眼鱼眼可就是成对出现,而且很明确是前后关系了,举几个宋人大腕的文字做个佐证:
苏轼《试院煎茶》诗:“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
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诗:“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
虞俦《以酥煎小龙茶因成》诗:“蟹眼已收鱼眼出,酥花翻作乳花团。”
元人王桢《农书·茶》云:“当使汤无妄沸,始则蟹眼,中则鱼目,累然如珠,终则泉涌鼓浪,此候汤之法。”则是对宋元点茶候汤的总结了。
宋人说到候汤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宋人喜欢用汤瓶煮水点茶,我们从河北宣化辽墓壁画就可以看到当时煮水的场景。汤瓶通常口小颈长,对接近沸腾的水的观察很不方便。从唐代以来,随着茶叶加工和饮茶方式的变化,煮水的茶具也随之演变,煮茶为代表的唐代以釜、铛、铫为主。点茶滥觞于唐末,盛于宋而止于明初,此时的煮水器除釜、铛、铫外,又出现了汤瓶、注子、急须等,而材质则包含了金属、陶瓷、石质等。与煮水其配合的火源,曰茶灶、曰风炉、曰燎炉。
灶通常是不可移动的,而且有烟囱,古代称为突,曲突移薪讲的就是灶的故事。但茶灶的烧水量不大,又演变成类似炉子一样可以移动的,区别是灶门大而出延,因为燃料用柴;炉门小而无延,仅用于通灰漏烬。如果说唐陆龟蒙茶事十咏中的《茶灶》是指蒸茶杀青所用的灶,那么宋梅尧臣《茶灶》诗则肯定是煮水的灶了:
山寺碧溪头,幽人绿岩畔。
夜火竹声干,春瓯茗花乱。
兹无雅趣兼,薪桂烦然爨。
同样说明问题的还有张耒的“笔床茶灶素围屏,潇洒幽斋灯火明”,幽斋中的茶灶!
其实,陆龟蒙真正的潇洒,就是《唐才子传》所云:“放扁舟挂篷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鼓棹鸣榔,太湖三万六千顷,水天一色直入空明。”这茶灶一定是煮水的。
炉在唐宋茶事中更为常用,陆羽《茶经》中风炉位列诸茶器之首。至于为何叫风炉,到了晚唐的人都已经不知道了。风炉这个名词似乎从陆羽首用,宋明时人偶用于诗文,如黄山谷诗:“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风炉之名反而在邻国日本的茶道中一直沿用着。
唐宋时期仍保存一款最有古风的无需炉灶而能煮水的器具——铛,铛和鼎是同一器物,在语音的变化中形成了两个名称,其实是同出而异名,都是上古的三足炊煮器,可立地生火。后来鼎成了庙堂之器,而铛则代表乡野之器,大凡唐宋和茶有关的诗文中所说的茶鼎,都是指茶铛,比如陆龟蒙的《茶鼎》诗:
新泉气味良,古铁形状丑。
那堪风雪夜,更值烟霞友。
曾过赪石下,又住清溪口。
且共荐皋卢,何劳倾斗酒。
《唐书·王维传》说王维“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唐才子传》载白居易“茶铛、酒杓不相离”,诗文咏茶铛的更不胜枚举,可知铛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煮水器;宋代李公麟的《山庄图》中,也仍有在山野中使用铛煮水的画面,画中的铛和闽北出土的宋代铁铛如出一模。
铛在历史过程中,根据使用需要,出现了方便出水的流,然后又加上了柄,在此基础上又继续演化出了无足铛或称折脚铛。在上海博物馆藏宋人《莲社图》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无足铛,已经和苏东坡《次韵周穜惠石铫》诗中的一种叫铫的煮水器高度相似:
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
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
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烝藓未干。
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
苏东坡用“函牛折足”和“无脚轻安”来隐喻这是无足器,结合“龙头拒火柄犹寒”一句,就是《莲社图》所绘的器形。
那么图中所绘的到底算什么呢?如果是无足铛,那么为何苏东坡诗中的铫和它如此相似呢?这就要对铫做个追源溯流的梳理工作。
铫是先秦就有的器物,它的命名,按中国古代一本专门从发音解释字义的著作《释名》的解释原则,就是铫者吊也,和铛立地吹煮的方式相反,铫是吊挂着烧,民间至今仍有吊子的俗称。吊烧的铫和立烧的铛,都很适合野外使用,尤其是无足的铫尤其方便军旅携带,成了汉代以前军旅中人人必备的装备。如果说铛可以理解成是釜(也就是俗称的锅)加三足,那么铫就是釜加提梁。而这种釜又有一个名称叫作鍪,鍪是一种深腹的釜,很像是头盔的形状,头盔也有另一个名称叫兜,兜鍪也是指头盔,而铫恰恰像个倒置的兜,或换一种叫法,铫也就是吊兜,这个词,一直被记录成刁斗或刀斗。
“刁斗”这个名称汉以后基本仅见于文人怀古的诗咏中,原因是在使用过程中,它的形制也在逐步发生分化,甚至唐宋时期的人已经无法描述刁斗是怎样的一件东西。虽然铫这个名称还在使用,原始的器形也依旧存在,但人们已经无法把铫和刁斗联系起来了。因为,就像铛在后来演变出长嘴的流一样,铫在唐代也出现流,就像刘松年《碾茶图》风炉上的那件器物。从沈括的《忘怀录》我们知道,这时期还有专用的食铫,保持原始器形的就是食铫,而茶铫出现的流,也是为了出水的方便。福建省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藏汉代铜铫和唐代铜铫,也就是刁斗,沈括记载的食铫,应该都是这种形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宋金时期的定窑瓷铫,是两宋茶铫的一个标准形制,和刘松年《碾茶图》中的铫也是一样的。
与此相类似的是“急须”,这是宋明时期江浙一带地方性的名词,北宋杭州人沈括的《忘怀录》中就记载了“急须子”,北宋黄裳在《龙凤茶寄照觉禅师》诗中自注得更明白:
有物吞食月轮尽,凤翥龙骧紫光隐。
雨前已见纤云从,雪意犹在浑沦中。
忽带天香堕吾箧,自有同干欣相逢。
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
禅翁初起宴坐间,接见陶公方解颜。
顺指长须运金碾,未白眉毛且须转。
为我对啜延高谈,亦使色味超尘凡。
破闷通灵此何取,两腋风生岂须御。
昔云木马能嘶风,今看茶龙堪行雨。
急须随着茶事的东传,也传到了日本,在日本被写作急烧,而在中国,则明代以后急须一名也基本不见使用了。在更多地区,这种器物是被称作砂铫或瓦铫,比如潮汕一带。
而这个地方性别名为急须的铫,和两宋时期点茶中最常用的一种水器——汤瓶,又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汤瓶也称茶瓶,唐代就已经出现,其作用在唐宋时期一直是茶酒合一使用的,标准器形是前嘴后鋬。这时 期还有一种前嘴侧柄的瓶,通常称为注子、注瓶,是更专业的茶具,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所藏的唐代一套石质茶具中,恰巧包括了两种专业器形。
期还有一种前嘴侧柄的瓶,通常称为注子、注瓶,是更专业的茶具,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所藏的唐代一套石质茶具中,恰巧包括了两种专业器形。
看到宋代的汤瓶实物,就不难理解为何喜欢用汤瓶煮水的蔡襄会说“候汤最难”。汤瓶这种造型,在明初点茶法退出历史舞台后,还继续保留着它的酒壶的使命,而注瓶这种造型,已经和侧柄铫子合二为一,同时兼并了无足铛的造型,这种事物发展的趋同性,是在使用功能的引导下进行的,苏东坡笔下的石铫,和无足铛合一,就不难注解了。
铛、注瓶和铫,在使用功能和名称上都遗传给了潮汕的砂铫,而紫砂壶,在明代时也是叫砂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