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不知有你
吴钧尧
有一年春节,我在淡水遇见高中同学。淡水老街是旅游热点,行人不仅如织,而且织得凌乱,情人两两成对,家族三五成群,青年学子团团围聚,每种移动都是一种织法,没想到同学左闪右闪、我与孩子东挪西移,竟碰头了。
我们只顿了一下,便认出彼此,“喊阿伯、喊阿伯”,我敦促孩子。
关于人情称谓,你向来拘谨,那一回也不例外。你怯怯地喊了声阿伯,同学约莫是没听见。你摸不着头脑,我跟你说,先喊了,我再细说原委。待与同学父女分别,我才跟你说,他是我高中最要好的同学,后来却不常往来。
孩子,当你有机会,与朋友相识于青春岁月,相伴于初老时分,那是人生的幸福,所以我常问你,可有要好的朋友或同学?当你们长大了、成家了,你们或许距离遥远,却会留在朋友的叙述里,如同童话的经典开场:“在很久很久以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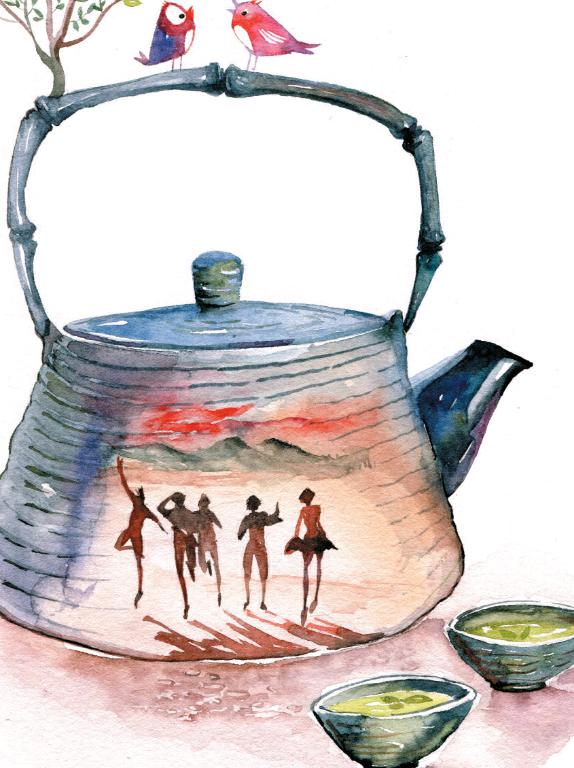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时不知道寒暑,也不知道有你,我跟林姓同学就很要好。我们一起徒步,往山里走、往溪边行,包括闻名遐迩的中部横贯公路。当时,台湾旅游风气未开,走访太鲁阁与天祥时,一如它们的地名,悠悠宁静,完全不像今天旅客如织。
流水、孤鸟,犹似人生。
同学结婚早,20岁时已生育男孩。他跟太太租住一间两室公寓,屋子虽小,毕竟门户独立,成为同学聚会场所,有人多喝几杯,或聊到兴起,索性打地铺,隔天再走。相交30年,以为友谊该无碍延续,没料到他妻子先入籍巴西,再是他跟女儿,只有他的长子,因无法适应移居生活,独留台湾。
几年前他返台,我曾带着你,与他们吃饭。后来一起在台北车站地下街,买了巴西难以购置的《武则天》《神雕侠侣》等连续剧光盘当礼物。当年这些电视剧正在热播,我当然奉上最热的礼物,给心头最热的朋友。
那一回,我们一同看望高中老师,老师不禁问,花这般代价,忍受无尽的乡愁,值不值得?同学在巴西,并非如我之前无稽设想的住庄园、养小马,而赖贩卖中国结等东方饰品维生,一年忙到头,也只能小有利润。在台湾苦,到巴西也苦,老师不解,两边都苦,何不在台湾苦?老师非常器重同学,常说他文采好,是班上的才子。妻子认识他20载,说他现在老了好多,我却觉得,他只是倦了。
同学老家就在芦洲,我的隔邻小镇。高中时,我常骑单车经三和路,转碧华寺附近小径,途经苍翠蜿蜒的农田,找他打球。我们常驻足,顾盼蝴蝶与野花漫舞,浏览野菜与水稻争路。20世纪90年代后,三重、芦洲交界剧烈变化,铺了新马路、筑了新大桥,有一次路过,想重寻往昔小路,已遍寻不着。
同学被老师问得狼狈。我心底盘算着,巴西返台得花几十个小时搭机、转机,前回见他已隔四五年,按此频率,这一生再见,不过寥寥数回了。
孩子,你可有这等相识且相伴的朋友?人生难以计算,天意自有安排,人与人能做的,只是为彼此停下,喝个茶、吃顿饭,都好。
因此,我对于淡水偶遇这事,记忆深刻。当时,你带着刚买的摔炮与仙女棒,要到广场上玩,我们携手,穿梭于如织旅客群,寻自己的路,往广场走。同学显然更早到了淡水,正往回走,哪知竟遇上了。
当我与同学四目相对,忽然同时顿了一下。我不知道同学想了些什么,但那个刹那,我脑海兜着旋转花木马,彩色的孔雀沉下去,灰暗的大象浮了上来,浮沉之间,音乐一贯地悠扬。
在顿着的瞬间,我把同学回想了一遍。从他的青春斯文,到如今肥胖灰暗,一如从孔雀到大象……但我仍一眼认出他,如同他毫不迟疑地辨识出我。
孩子啊,慢慢你会知道,人生的花木马上,起、落都是常态,但有没有一个朋友,在你沉降而下的时候,记得你的灿烂容颜呢?
道别以后,我们到广场玩摔炮与仙女棒。我看了一眼同学离去的身影,并不知道这一别,是否即是天涯。(饰 文摘自凤凰读书微信公众号,勾 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