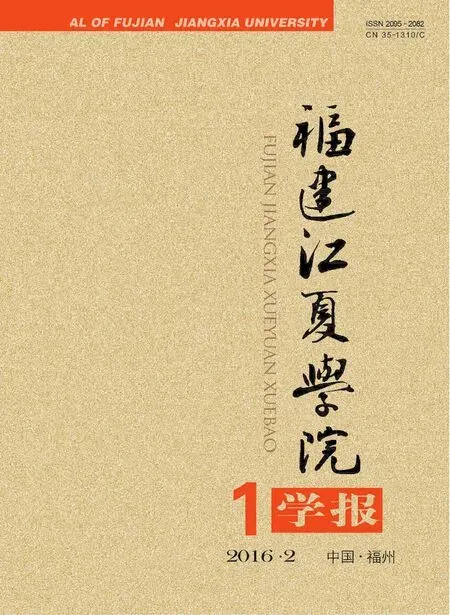论阎安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李卫国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论阎安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李卫国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摘要:阎安的诗歌充满着北方的苍茫与壮阔,在历史之虚处,他不断地挖掘和寻找,展示历史之变的同时还从中攫取了野性,形成了独特的力度写作。在当下之实处,他从旁观者的特殊角度出发,在客观中构筑现实世界之变,而诗歌中不断出现的石头则是他所找到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
关键词:阎安;诗歌;艺术特色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面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摇滚歌手崔健在歌里大声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而今我们在21世纪中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社会发展更快,个人被时代的大潮不断地往前推涌,根本来不及思考和沉淀。因此,社会变得浮躁,催生出了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在诗坛体现为诗歌创作的随意性和诗歌批评的浮泛性。一些诗人面对物欲时代的种种诱惑,盲目随心地进行着所谓的创作实验,各种主义、诗体形式频繁出现,以期夺人眼球。而部分批评家面对形形色色的诗歌乱象根本无暇深究,只是做一些浮光掠影式批评。在如此的乱象中能够坚持自我的人不多,陕北诗人阎安就是其中之一,他依然在秦岭以北贺兰山以南的中国地理版图中写作,书写着波澜壮阔的北方。
一、于虚处发力
于虚处发力,是对阎安诗歌创作的一种描述。这里所谓的“虚”,指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纯净,另外还指与现实相对的历史传统和时空的想象。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诗应回到虚的位置。在谈到当代诗歌所面临的的危机时,阎安毫不客气地说:“整个时代的大多数诗人热衷于用一种入世的心态和动机写诗,诗歌回不到虚的位置上,就是诗歌写作的诗性缺失,等同于俗物”。[1]10不可否认当下诗歌正走向多元化,相应地诗人和读者也随之出现分化,一部分诗人迎合市场化、大众化的需要而写一些通俗的诗歌,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缺乏节制,出现粗制滥造、雷同、无病呻吟之势,极大地破坏了诗歌的形象,使之失去了原有的批判性和庄重性。另一部分诗人仍坚持诗性这一根本性原则,从生活出发,不断淬炼着诗文,从而提供着更为超越性的气象,诗人阎安对此有强烈的意识并通过自身不断实践着,正如他所说的:“一个诗人及其诗歌无论从创作原理还是从境界容量上而言,是包含着天意的,不仅仅是人的那点儿事,它必然要给世界提供更高的、超越人事的综合和提炼、格局与气象”[2],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对历史和传统重新进行认识,因此就有了“虚”另一层含义。第二,不可触的历史传统。历史与当代的遥远距离,造成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只能是通过文本和想象,因此历史作为已逝的事物,是不可亲历,不可触的,是虚的。虽则如此,但历史中形成的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对当下还是有借鉴性意义的,对此诗人说道:“我相信厉害的写作者都在传统之中,是传统的产物,正是传统在他身上表现出更新性延续,才体现出他创造性写作的完整意义”。[1]9这种对历史传统回顾的实际本意在于建设,正如阎安在《秦岭颂辞》一诗中写道:“让时间历史和时代就像山上飘过的一块云朵孰轻孰重 无法掂量”,时间和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而石头相对不变,也即是说在变中总有一些不变的根本性因素,供我们在它的基础之上延续创新,依靠这个基础,个人也可以成功地切入历史,从而打开时间之门。第三,“虚”是指想象的时空,文字世界的童话或神话。如在《玩具城》一诗中,“我是梦的孩子我的梦是大力士的梦世界是我梦中轻如鸿毛的玩具城”,“我是梦的孩子我是世界的孩子我居住在我的玩具城里”,提到玩具这一意象,明显具有儿童般天真的心态,我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和探索的欲望,因此世界在诗人眼中就是一座巨大的玩具城,而我们每个人也是其中一员,世界也和我们开着玩笑。在另一首《北方北方》中诗人写道:“我的故乡在北方我要把我的童话不断地讲给北方听我要我的北方在我的童话里慢慢长大”,北方,诗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那里有着诗人的记忆,那里还有悠远时空里的神话和传说,诗人相信这些童话,虽然环境恶劣,但他的童话小屋总是努力呵护着那一盏灯和花,诗人要不断给北方讲童话,他希望他所居的北方保持那一份本真,那一份质朴、那一份厚实和那一份原始的生命创造力。在《一个湖泊突然消失之后》一诗中,诗人则是直接把逐日而死的夸父写入诗中,梦见他复活,展示了一种奇崛的画面。童话或神话的思维是最具原发力的,除此之外,诗人追求的还是一种直接和时间对话的冲动,在时间之维中深刻揭示人的存在,使诗歌超越现实,超越人性达于神性,从而形成一种自由的诗性空间。
于虚处发力的“力”指的是一种力度写作,一种阳刚之气,一种精神中的野性。李岩说“早年阎安的诗歌并不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诗歌……是一种在地层深处自焚、饱受煎熬的诗歌”,[3]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带着苍凉的北方气息和特别意象,如《大河以西》,“大河以西,所有的事物与我的亲人有关惨不忍睹”,后来西部这一地域随之被更广阔的北方代替,如《北方的书写者》《北方北方》《我的故乡在秦岭以北》等,一些意象如秦岭、大山、黄河、大地沙漠、石头等展示着鲜明的北方特色。较有野性的是《与狼签约》,“狼神呵,我们与你签约——让你的灰色和羊群的白色汇合和马群的棕红色汇合和大海、山林、天空——我们心中的蓝色汇合”。狼是不被驯服的,世道变了,狼的桀骜不驯和杀气不会变,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破坏和野性的精神,因此诗人和狼神签约,呼唤野性的复归。
二、在实处旁观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谓的“旁观”即是一种从当下紧密的生活之中抽离出来的姿态,是一种有意识地和现实拉开距离的态度,是某种意义上的隔。通过旁观者的姿态打量现实、打量自身、打量他人,打量过去,可以从更客观的视角上进行一系列的反思。阎安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参与生活以及诗歌创作的。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毫无疑问,语言及其意义的本性决定了旁观并不是一个懒汉懦夫对当下生存现场的漠视和游离,正是在语言的旁观中,世界清晰、朴素、真实,并强烈地凸显着此在时空的内在尊严和形式风格。这就是说,旁观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要刻意自居的位置”,[4]10诗人的力量是语言,他通过语言旁观世界,旁观并不是对当下的漠视,相反,抽离正是为了纠正和重新参与。随后他继续解释道:“活成一个旁观者,让语言写作品质纯粹并成为本时代关乎心灵的见证性力量,这是语言写作必须选择的开端和终端,这也是我作为写作者的全部开端和终端……旁观者是一个终极的关怀者和承担者,他以全部诞生的品质构建语言意义上的世界身体”,[4]10诗人以旁观者式的冷峻和关怀打量着现世,在语言之维中构建着世界之变。
在实处旁观,具体说来有三个层次。第一,对现实的旁观。当诗人从色彩斑斓的现实之中撤离之时,他即可回到一种客观的位置,他首先好奇的便是裹挟着自己飞奔而前的现实究竟是怎样?在现实的背面他能重新打量,重新发现,重新调整。当停下来,当回到旁观者的位置,他开始回顾,开始透过时间对变化的事物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梳理。首先是对故乡的观察,故乡是文学不变的母体,如《我的故乡在秦岭以北》写道:“天下人都知道 秦岭以北那是我的故乡 和许多人的故乡天下人都知道的是 如今那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草丛茂盛蛙鸣寂寥”,整首诗充满着一种落寞与焦虑,诗人与故乡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故乡的生活是贫穷落后的,父亲杀掉老牛后丧魂失魄,“在我的故乡牲畜的亡灵比人的灵魂更长时间地折磨着生活贫穷是一种古已有之的误会”,故乡的贫穷使诗人逃离,进入了城市,这些年,诗人的状态是“拖儿带女在外漂泊”,当诗人再回去时“那已是父亲归山的日子”,诗人在城市追逐着梦想,但猛一回头,那个曾“为此天天为我捏一把冷汗夜夜为我做一场噩梦”的父亲已不见,这是何等的沉痛。此外,诗人还发现工业文明已把自己的故乡吞噬的面目全非,在《回乡记》写道:“那座童年时候的山 如今道路纵横机声隆隆 夜晚降临后我才知道山上那棵威风凛凛的树也不在了比它更加威猛高大的钢铁井架代替它站在高处”,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机器声、钢铁井架已经打破故乡的宁静,一切已是物是人非,诗人感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悲怆之感油然而生。
第二,对自身及他人的旁观。从自己的故乡逃离后,诗人进入了充斥着种种欲望的现代都市。《中年自画像》一诗写的是诗人对自我的审视,“ 一个被大海和它虚无的湛蓝淘尽了青春的人灰溜溜地回到了秦岭以北如今已不事精耕细种的北方一肚子瓦蓝瓦蓝的海水没处吐”,这个秘密便是诗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与不自在,这种类似的的体验还表现在另一首诗《怎样变成一个城里人》中,“有很多次你必须像贼一样 晚出早归在深夜潜回故乡”,人虽在城市生活但是心仍无处安顿,在深夜总是梦回故乡。在《面具》一诗中更是疾呼“我已经不适合在这里居住这个横行霸道的城市”,痛感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每个人都虚伪地活着,不肯暴露自身真面,不以真诚示人,因此诗人忍无可忍要离开,并在大声嚷嚷中使自己显得真实。另外就是对他人的关照,他人对自己来说是一面镜子,在对他人的旁观中同样可以发现自己的影子。如《卖咖啡的外乡人》一诗中写道:“卖咖啡的外乡人卖不掉自己的咖啡像一座孤岛一样陷落在行人稀疏的路边就像他的故乡的孤岛陷落在人烟苍茫的大海远方就像他又红又黑的眉宇间偶尔闪烁着灼热的忧郁目光”,这里对异乡人的审视,不如说就是把自己代入,异乡人的情感体验就是自己的情感体验的投射,在这人际苍茫的大海,自己像孤岛一样,一种漂泊无依之态显示无疑。
第三,对过去的旁观和审视。这种关照透入历史之中,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之中已经有所涉及。诗人生活于秦岭以北贺兰山以南的地域,这里是文明的生长地,由秦至汉唐,文化一脉相承。在谈到秦文化时诗人说:“秦的历史在我看来就是生命及其历史诗性的直觉形式的必然性崛起,它为当时处于危机状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原始的生命直觉”。[1]9因此诗人通过旁观历史,进而针对当下诗坛发出回归野性的呼唤,这集中体现在《与狼签约》一诗,“与狼神签约:什么时候我们接它回来……就像接回自己流亡异乡的孩子”,“与狼神签约:我们的城市已深陷于白像死亡……我们需要另外的颜色 包括灰色你在奔跑中杀气冲冲的灰色”,狼神在这里就是秦文化、汉文化,乃至于唐文化的象征,这种文化具有原始的野性和蛮力,是滋生创造力的源头,更是诗性直觉的场域。
三、时空里的石头
提到石头这个意象,我们可以想到女娲补天的传说,足见石头的古老,因此它是最能代表时间的东西。其次想到的是《红楼梦》中被投向人间的那一颗补天剩下的石头,历经红尘是非。石头这一意象频繁地出现在诗人的诗中不能不引起人注意,单就题目说,带有石头二字的就有《祖国与石头》《山上的石头》《华山论石》《追赶石头》《整理石头》《秦岭:石头庄园的七种方式》等,另外涉及石头的《华山论石》《北山寻石记》《一个石匠》等,诗文本中出现石头的则更多,如《把黑变白的经过》中的巨石礁石,《在陌生的河流上》中的巨石,石化的骸骨,《偶然之河》中的砾石或岩石,《风一样轻的叙述从何而来》中的石块等不一而足,倘若是算上山(更大块的石头),则数量更多。诗人的一本诗集则更是直接命名为《整理石头》,那么石头究竟在诗人笔下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整理?怎么整理?
这些疑问,只能到诗中寻找答案。诗人在不同的场合,曾经不只一次的说出自己对当代诗歌的失望以及对古典传统的喜爱,这其实并非是简单的厚古薄今的心态,而是从古典传统之中看到了自己所认定的理想,看到了一种精神纯度和诗性的自由场域。那种诗性是完整的,而不是如当下的破碎和低滥,那种诗性是超越人性直达于神性的,而不是当下诗歌的物性弥漫。因此向传统的回头凝视实是诗人的一种企图,企图超越局限和束缚而直接与时间对话,从而在时间之中找出一种更深的依据参与当下,因此这种回归同样是出于建设性的目的,出于参与当下的目的,这二者并不矛盾。谈到石头,诗人说:“我出生并长久地生活在中国北方……所谓的地球上的高纬度区位,正是人类文明最早产生,并注定要经历沧桑剧变的地方……我随便拿起一块石头都能发现他们比《四书》《五经》更古老,我由此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魅力并为之倾倒”,[1]8由此看出石头所代表的正是古老的时间,石头是时间之流中不变的事物,同样也是指北方独特的地理空间。
由此再回到诗中,如《祖国与石头》一诗中写道:“应该开辟出更多的地方让石头居住让那仿佛来自于山中连接和暗示着时间另一端的石头”,这石头来自于古老的时空,它处在时间的端点,连接着当下和过去,它可以供我们忙作之余眺望时间和历史,这远比苍穹厚重的多。在另一首《山上的石头》中写道:“在山上要相遇的石头是从古代放到现在的石头让风带来又带走的石头”,诗人走在山上,不断邂逅着石头,而山本就是更大的石头,走在山上就好似踏上了那远古的时间大道,走向时空的另一端,逼问生命的存在。诗人诗中常出现的山是秦岭,《秦岭七日》《秦岭论石》《传说中的秦岭红》《秦岭颂词》等,它是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如在《我试着说一说秦岭》中,“我是北方人 秦岭就在我家的院子里我知道翻过秦岭就是南方”,作为石头的秦岭同样是时间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我知道秦岭深处的东西 主要是那些石头…… 带着可信和不可信的寻常与神秘……每一个朝代都有为秦岭而走失的人他们至今还住在山里”,历经两千年依旧,诗人说他知道的不多,只是随口提提唐代的、宋代的秦岭而已,苍茫感顿出。在描写了众多的石头后,诗人说石头需要整理,于是有了诗作《整理石头》,这是一首较长的诗,开篇写采石工人寂寞地重复着沉重的劳动,他全心全意神情专注,看着一块块石头被运出整理打磨,抹去了曾被杀伤的痕迹,石头代表着历史和时间,石头被整理打磨暗示着历史被修改,被人为的阐释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性。随后接着写道:“一个因微微有些驼背而显得低沉的人是全心全意整理石头的人一遍遍地他抚摸着那些杀伤后重又整好的石……借助磊磊巨石之端祥自己的影子神情那样专注而满足”,整理石头的人从石头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自己也像石头一样,被时间、生活、权力等所支配打磨,和最初相比已失去朴真,面目全非。最后诗人说道:“我见到过的整理石头的人我宁愿相信你也见过甚至相信 某年某月某日你曾是那个整理石头的人你就是那个整理石头的人”,意思豁然开朗,直接点明,我们其实和石头一样是被时间、历史和权力打磨的人,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整理和打磨着石头,即或多或少地参与着历史的修改,正像霍俊明说的整理石头所带有的“个人时间的灵魂史和时代见证史难度”[5]的意味,意即我们参与并构造着历史,我们经历,同时我们见证。同时,整理石头也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对日益迷失自己、迷失了方向的人类给以足够的提醒,阻止心的下沉,世界的下沉”[6]的关切和忧思。
历史无法被完全的还原,但是历史中一脉相承的东西像石头一般坚硬,虽有磨坏却仍被保留了下来,这就是传统文化中根本性的因素蛮力所在,它质朴,它有活力,它同时具有野性和扩张性。它能够给与诗性以自由驰骋而不受约束的空间,无疑这一点也正是诗人所不懈追求和强调的所在。正是通过以上不懈的探索,诗人终于找到了现实和历史的连接。
参考文献:
[1] 丰云,吴怀尧.整理石头的人——著名诗人阎安访谈录[J].诗选刊(下半月),2008,(9).
[2] 王丽一.诗歌是快要灭绝的艺术方式和精神游戏[J].延河,2015,(2):93.
[3] 李岩.有关阎安诗歌的几个片段[J].诗刊(下半月),2004,(10):41.
[4] 阎安.在我们的时代旁观[J].诗歌月刊,2007,(12).
[5] 霍俊明.在“断裂”地带写作-评阎安诗集整理石头[J].文艺报,2014,(10):1.
[6] 李晓恒.阎安:用诗歌扶提下沉的心下沉的世界[J].延安文学,2014,(8):282.
(责任编辑林曼峰)
教育教学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YAN An’s Poems
LI Wei-guo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YAN An's poetry is full of vast and magnificent vision of the Northern,In the imaginary place of history,he continues to expand into the depths of history and gains the power of the wild,he forms a unique way of writing.In the present reality,he observes the world from sidelines and objectively construct the change of the world.And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stone is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the intersection he found.
Key words:YAN An;poetry;artistic features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16)01-0100-05
收稿日期:2015-11-17
作者简介:李卫国(1991—),男,山东聊城人,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