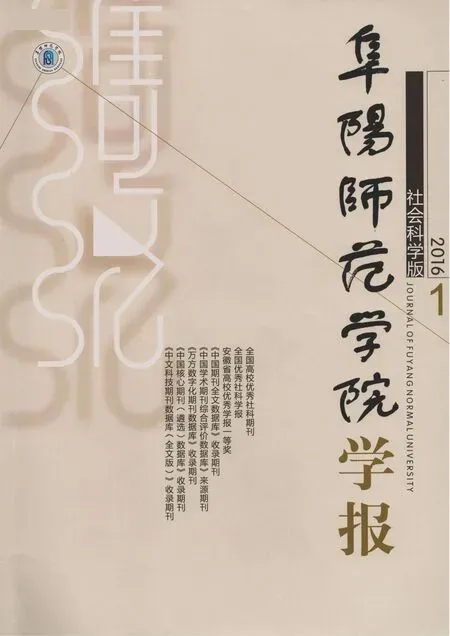社会资本与法治实践的逻辑探析
胡 钢(江西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社会资本与法治实践的逻辑探析
摘 要:社会资本通常被定位于以合作、信任和相互期待为基础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以信任、规范、网络等为核心表现形式。在厘清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挖掘社会资本与法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分析社会资本对法治实践的积极意义,并探究法治实践对构建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对法治中国背景下的法治实践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任;法治;法治实践
胡 钢
(江西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社会资本”概念由来不久,上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首次提出,随后被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诸领域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并加以研究。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争议也是一直不断,百家争鸣。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研究和分析法治实践问题的一种理论视角。然而,对社会资本与法治实践之间关系的研究,当前我国学界还鲜有学者涉足,且多着力于其中的某个方面。在“十八大”提出法治中国建设新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拟就当前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和理论争辩作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阐述社会资本与我国法治实践之间的功能和意义。
一、社会资本:以信任、规范、网络为核心表现形式
“资本”一词本源于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能够生产产品的产品”,从这个概念上来看,此即为人们通常所谓之物质资本;也在上世纪,经济学家提出一种代表着人格化的知识或技术的“人力资本”,认为它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明确将“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互动进行了阐述,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等学者也基于不同的学科理论视角和分析目的,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多样化的解读,为社会资本的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为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发展,提供了理论工具和实证工具。
布尔迪厄将社会资本表述为一种通过对“体制化的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1]。这种网络并不是自始天赋的,而是通过个人不断进行制度化的群体关系和社会联系的投资而获得的。他进一步阐述认为,个人对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将个人的、私有的特殊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具有集体公共性的合法利益[2]。
詹姆斯·科尔曼以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研究的出发点,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中的社会结构性资源,由社会结构要素组成,且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他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并且他认为,通过培育和组建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的自我治理,可以生成上述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本。科尔曼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以致他的观点让许多后续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影响都是有所裨益,而没有任何消极后果的(世界银行也因此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社会规范、组织与网络等形式的社会资本获取权力和社会资源,以利于进行社会行动的决策,或者是国家科学地制定政策),这种因概念界定上的逻辑混淆所致的错误显然需要纠正。
美国政治学家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延伸到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社会制度也被纳入到社会资本的研究范畴之中。普特南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地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情况的实证研究,对社会资本这样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然而普特南将“公民参与”水平、社团数量多少视为社会资本存量的体现,他的社会资本概念不免有混淆市民社会与“公民精神”之嫌。当然,尽管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公民精神并不等同,但二者确有重合之处,从社会资本最终产生结果的形式来看,存在于人们之间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信任”“合作”“互惠”等规范和价值,很有可能归因于“公民参与”和“市民社会”的作用,但也并非是确然发生的,社会资本并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会导致有益的结果。
从上述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来看,尽管社会资本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未在学界形成一个共识性的观点,而且其中概念界定上的共同缺陷,也是社会资本理论建构继续发展的阻碍因素。珀斯尼科斯严肃地指出了当前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不足之处:一是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尚未有一个逻辑严密的阐述,仅限于将社会网络、信任、互惠性规范等概念进行罗列式的归纳表达;二是研究者虽然竭力试图为社会问题寻找良方,但最终实际上却又并未提出任何未知的东西,以用来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1)。
福山对社会资本的表述值得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4]。这种将社会资本称之为一种“非正式规范”,而将前人所谓之“信任”“互惠”“合作”“社会网络”等被视之为社会资本本身的概念,看作是非正式规范作用的结果,对于这种结果,则有可能为正负两个方面。福山在此后的研究中还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资本积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统文化的基础,但政府通过施行积极的法律政策也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
我们这里并无意对社会资本作个定义,但结合学者们的论述,还是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还是一种“非正式规范”,长久以来,对于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通常都被学者们广泛地以信任、规范、网络等来表述,他们研究社会资本的共同取向,都是将其定位于以社会合作、相互期待和共同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进而成为可以对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危机进行功能补充的非制度化要素[5]。这就与科尔曼所述社会资本是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社会结构性资源的概念有共通之处。当然,人们为了各种利益而采取社会行动、参与到社会关系之中,创造出各种社会资本,对社会也必然发生相关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或使社会发展因此受益,增进社会信任、团结与合作,也有可能致使社会发展面临威胁。
二、社会资本与法治实践的内在契合
(一)社会资本为法治实践提供价值支撑
法律虽有其本身内在的价值和强制性,但法治及其实践离不开道德伦理秩序而存在发展,对法治秩序的遵守和践行,则需要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存在于每个守法公民心中的共同认可的道德伦理规范的约束。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揭示了当今我国道德秩序逐渐被市场经济瓦解支离的状态,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不择手段的征地拆迁,社会主体道德伦理丧失,社会个体之间、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缺乏道德信任和法律信任。另外,西方纯粹法学和法律万能论单纯依赖法律作为社会治理工具带来的恶果又让人们开始深思,仅仅依赖机械化和程序化的法律是否导致了法治的僵化,社会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和自由沟通以及信任理解因而难以实现?
以信任、规范、网络等非制度化要素为核心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形成有诸多联系。现代法治的内在价值和伦理道德都是人们生活和交往经验的总结,对法治的信仰和崇拜,对自由和平等的要求,对公平正义的伸张,甚至于道德的标准,它们都产生于人们重复不断的社会交往与行动之中,产生于社会个体之间的信任、规范、网络的关系之中。社会资本包含着充满生机的市民社会中的制度性关系,体现了多元化、破碎化时代的共享价值观,从而构成了公民美德的基础[6]。因此说,作为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创造和共同认同,社会资本为法治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广泛而有力的价值伦理支撑。
(二)社会资本可以提高法治实践的社会合心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社会发展逐渐走向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机制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由合作共存转变为竞利互争,个人主义盛行,传统道德的分崩离析使得人们之间的行为愈加私利化,社会分化、冲突、矛盾日益加剧,整个社会走入一种“囚徒困境”。人们很难再通过信任、合作的方式来获得集体的胜利和利益的共赢,反而不再相信任何有可能束缚和限制其个人私利和欲求的规范。
当然,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法治实践和社会治理中的违法行为,比如暴力执法、环境群体事件等严重侵害个人、群体权益的现象,由于其本身的不透明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人们对公权力的行使缺乏信任,缺乏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感。社会个体与国家公权力机关、与社会管理者缺乏信任、沟通,乃至于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实践还没有形成依法遵行的合心力。
因此,要克服上述困境和问题,提高法治实践乃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社会合心力,社会资本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信任、规范、社会网络、互惠、合作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比如我们国家和民族传统的家族血缘关系、邻里联系、民族纽带,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等等,当其在良好的环境里充分发挥其积极效用时,就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互惠与合作,增强社会信任,进而公民参与和网络规模都能得到扩大,这样就可以消解多元利益冲突和信任危机,促使人们通过团结协作寻求共同利益,增强社会成员以民主法治方式参与治理的理念。这对于推进法治社会的有效整合,凝聚社会主体的合心力,实现良法善治,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社会资本有利于推进法治秩序形成
2011年3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才宣告形成,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法治实践已经初步具备体系化的规则基础。没有规则就没有法治社会各个主体的各行其是,就没有法治秩序的最终形成。前文已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和社会行动中的社会结构性资源或非正式规范,它为人们所创造出来并共享的基础是人们对其普遍自觉接受和认可并达成共识,并且没有国家制定法的强行性和命令性的色彩。因此,法治社会及其实践中,社会资本的存量越大,某种程度上说明(这里只讨论那些产生积极、良性效果的社会资本),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越趋向信任、合作与互相期待,更容易达成沟通、理解乃至于利益的趋同共赢。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为法治实践建立全民以及所有社会主体对法治普遍遵守和奉行的基础。
另外,在当前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下,公共治理这一体现着现代法治民主理念和机理的治理方式,不仅能够让公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管理社会事务,又能够对自身事务高度自治。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作出了新时代的重要部署:“良好的国家治理总是与社会自治紧密结合的,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越文明,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越受重视,作用发挥得越好。”[7]社会资本所产出的信任、互惠合作、网络等内容不仅与公共治理的理念一致,还能够创造出公共治理的载体,比如各种社会组织、社区团体、民间性ADR组织等等,这些内容扩大了公民参与,培育了公民精神,人们通过组成社团等现代社会网络或者仅仅是依靠传统的家族、社区的网络,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人人都成为法治轨道上的社会治理主体,这也不自觉地促进了法治秩序的形成。
三、法治实践之于社会资本的构建
(一)我国社会资本的基本现状
当前我国社会资本的基本现状是,传统社会的习惯、惯例、风俗等非正式规范的约束与调节作用越来越有限,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意识逐渐淡薄,支撑人们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价值根基缺失。人们之间的社会行动缺乏信任基础,阻碍了网络、互惠、合作的关系生成,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比如,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关系而聚合的乡族关系网络有内外不同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基于传统的家族和乡土的观念,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述的“差序格局”,建立了因亲疏远近而形成的大小、强弱不同的乡族式的关系网络。而如今的现实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客观变化,这种乡族网络尽管数量上减少、关系强度上弱化,网络内部人们彼此关系松弛,甚至封闭化,但当面对网络外部,人们往往能够紧密联系起来,有着强大的社会行动力。这主要体现为:这种关系有助于加强关系内部的互惠联系,促进合作,共同抵御威胁、化解风险,比如农民工集体维权,比如各种地方商会组织;当然,也会有负面效果发生。在农村,各个宗族势力之间纠纷不断,农村治安环境恶化;在城市,这种关系网络容易形成犯罪团伙。
市场经济和多元利益的冲击,人们对传统道德伦理的漠视使得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因素,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其范围的半径已然缩小,信任范围内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规范以及互惠合作等都随之减少,加之传统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社会资本的存量相比西方民主法治国家明显不足。
(二)法治实践与社会资本的构建
传统的社会资本发挥积极作用有限,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现代型社会资本尚未普遍规模生成,存量不足,亟待加速整合重构。而建设法治中国的法治实践,可以在社会资本的构建中发挥促进作用。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现代民主与法治观念能够重构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互惠关系。我国法治实践中在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制保障的同时,社会中相应的法治信念和精神阙如,导致法治畸形发展,法律条文沦为一纸空文,传统社会资本中一些恶性因素出现并蔓延导致一些预期外的后果,比如裙带性质的人情关系导致贪污腐败,这种消极恶果尽管不一定是社会资本的预期目标,却使得法律制度威慑力丧失,最终无法获得法治实效。现代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理念能够让社会个体理性开放地面对社会,慎重选择自己的社会行动,以法治的方式展开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信任、社会协作与互惠关系,建立新型健康的社会资本。
第二,法治的规则和制度是整合、改良社会资本的法制基础。前文所述的社会资本给法治运行带来了预期外的“恶果”,而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强制力和惩罚性,可对违反法治运行规则的行为和现象(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犯罪、乡族势力斗争等)施以惩处,引导社会资本良性发展。社会信用依赖于法治得以培育和发展,没有形成法治化的环境和氛围,个体、组织甚至是整个国家社会就缺乏建立自身信用的积极性。反过来说,在一个缺乏社会信用或社会信用极其低下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和惩戒功能,可以促进社会信用的培育和成长[8]。
第三,法治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积累社会资本。当前我国法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对于法治秩序形成的重要作用。虽然笔者并不认为民间组织能够作为一种关系网络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本身,但将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作为法治实践的内容和重要方式未尝不可。更何况社会个体通过结成民间组织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形成互惠合作的关系网络,既是社会资本的结果,且随着人们不断在网络内外开展社会行动,有益的作用又将持续扩大,福山所谓的人们之间的 “合作习惯”将会养成,“信任基础”也将得到巩固[9],带来的就是社会资本的增多。当然,一些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乃至于国家治理中的法律地位如何实现,就要依赖于立法以及政策上的依据了。比如将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一些职能赋予专门成立的民间组织,使之享有一些行政性质的管理和处罚的权力,就需要法律专门作出规定,在此不赘。但基于法治的基础上,诸如此类组织对于积累社会资本的成效是显著的。
第四,良法善治为社会资本的生成和积累创造稳定、开放的社会结构。从微观的法治语境来看,法治实践为社会资本的生成提供稳定的法治环境。福山认为国家通过有效地提供社会公共物品(比如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公共安全利益),可以间接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人们更有理由去选择国家法律所提供的安全,而不是黑手党作为“民间财产权保护者”的保护。良好的国家法治能为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起到强制性调整和保障,在此情形下,违法犯罪现象将减少发生。因而,在一个安定有序的法治环境里,人们才更有可能进行社会交往、参加志愿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发达的民主法治环境中,公共治理作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从政府一元单向治理转变为多元互动共治,公共治理的领域和内容越来越广泛,夯实了培育和生成社会资本的土壤,通过不断扩大的公民参与社会协作,人们的社会信任会因此得到增进,互惠关系、互动交往网络和社会规范也就不断生成并加强,从而有助于体现民主法治精神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社会资本的形成。
总之,且不论社会资本究竟应作如何定义,但其对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作用。社会资本不仅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还可以带来法治所依赖的理念和信仰,促进自生自发秩序的实现,形成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自觉,正式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在此基础上得以施行并被遵守。当然,由于当前国内外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仍没有取得最大的共识,且很多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故而社会资本与法治实践二者之关系的研究,仍有待于后续的探讨。
注释:
(1)转引自马德勇.社会资本:对若干理论争议的批判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8,(05):74-81.
参考文献:
[1]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1998(03):18-21.
[2]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04):23-35.
[3]罗伯特·D·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
[4]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J].曹义,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02):36-45.
[5]马长山.社会资本、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J].环球法律评论,2004(03):263-272.
[6]弗雷德·鲍威尔.国家、福利与公民社会[J]//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陈家刚,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13.
[7]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04):5-27.
[8]王华.中国社会资本的重构[J].天津社会科学,2004(05):68-72.
[9]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341.
□经济学、管理学研究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w
HU 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Ganzhou 341000,China)
Abstract:Social capital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social a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which is based on cooperation,trust,and mutual expectations and mainly manifests in the trust,norms,and networks.Based on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this article digs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rule of law practice,analyz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rule of law practice,and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rule of law practice for establishing social capital.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trust; law practice; rule of law practice
作者简介:胡钢(1990-),男,江西鄱阳人,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2013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法制。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资本转型视域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14BSH016)。
收稿日期:2015-11-11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1-0103-04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1.020